

扫码打开虎嗅APP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看理想(ID:ikanlixiang),作者:苏七,配图:《我 11》《钢的琴》,头图来源:《最好的我们》
前段时间,13岁东北男孩“钟美美”模仿老师的视频引发了广泛的讨论。
语气和台词我就不夸了,让我觉得最绝的是:一个眼神,一个小停顿,一个转瞬即逝的微表情,小手那么一指……模仿老师接上级电话时候的一个假笑,语文老师训人的时候顿那一下衣服,拿起女学生口红时的手势,老师带病上课发不出声的时候的音色。——豆瓣网友@刘小鸭
钟美美模仿的那种凶劲,扎心伤自尊恐吓的话,变脸技能瞪眼等,其实还有诬陷欺负老实学生立威,小学老师里太常见了,心理伤害极为深刻。——知乎网友@oooo
我一个上班好多年的人了,看完愣是吓出PTSD来。——知乎匿名用户
也有评论指出了这种强烈共鸣感背后的根源。
老师拥有几乎完全不受制约的权力,可以肆无忌惮地以教育为名拿学生发泄情绪,侮辱人格,甚至暴力伤害。在学校里他们就是国王,决定学生的一切。这样教育出来的孩子会把伤害教育投射到下一代,然后觉得这都是童年回忆。自己被这样对待理所应当。——微博网友@山顶冻人1218
5月29日,钟美美删除了他在快手上所有与模仿老师有关的视频。6月3日,学校与教育局先后回应,承认与钟美美接触,但本意是对其表演天赋的肯定,希望能从正面引导孩子,多传播一些“正能量”的作品。
此后,钟美美转变风格开始模仿志愿者,但这种“正能量”的视频并没有得到大家的认可,反而再次引发了关于教育包容度和引导的讨论。
这是自我意识萌发的少年与成人社会的初次交锋,或多或少让我们想起了自己。十来岁的年纪,正是快速生长,对世界懵懂而好奇的时候。但大部分时候,我们只能按部就班听老师灌输各科知识,鲜能发表自己的见解。
在这种模式化的评判标准之下,少年的锋芒慢慢陨落黯淡,向平庸的现实妥协。东北作家双雪涛,把这种少年时期充满探索与好奇,却充耳不闻、口不能言的感觉,叫做“聋哑时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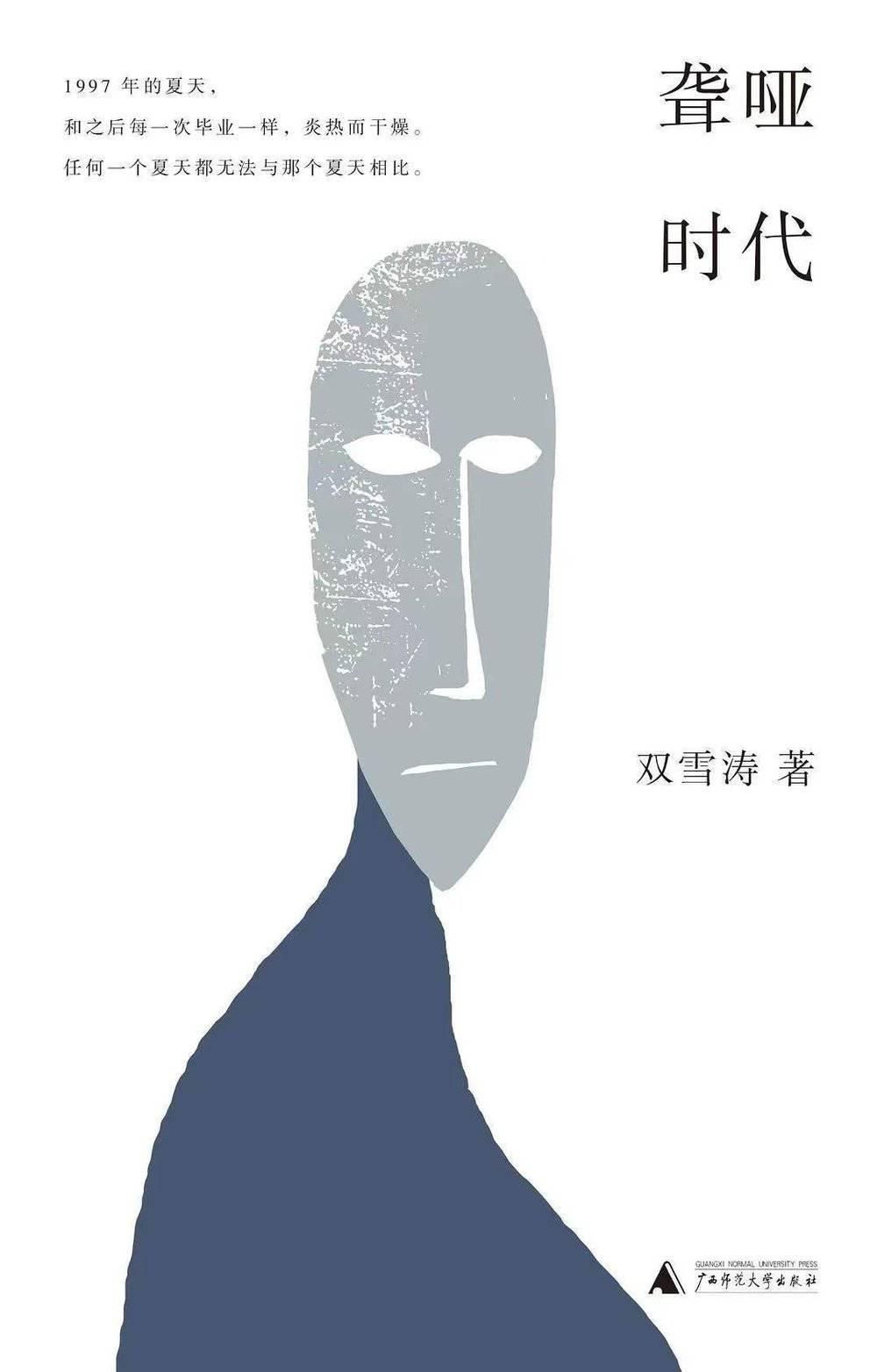
青春的本来面目
进入六月,天气一天天炎热起来。如果不是疫情的影响,这个时段网上又将迎来一大批中高考完无处释放的孩子。
夏天对于中国的孩子是特殊的,中考,高考,毕业,成年前所有重大人生转折都发生在夏天。无处可藏的炎热意味着过往的终结和新生活的开启,逼迫着对成熟毫无心理准备的我们往前走。

1978年,独生子女政策被写入宪法。1986年4月,《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颁布,九年制义务教育和考试制度随之建立完善。
80、90这代人,生来带着独生子女的标签,成长过程中又正好赶上了经济发展快速期,无论哪一代人都可以理直气壮地评价我们 “娇生惯养”、“不能吃苦”、“脆弱”、“自我”。
但凡一个80、90后流露出烦恼,肯定会有长辈搬出吃不饱肚子挖菜根的过去来忆苦思甜,说你们都是少年强说愁。一边是作为独生子女承载着整个家庭的希望,一边是不得不面对的严酷的升学竞争,但我们没有资格抱怨,没有资格不好好学习。
现实中,日益收紧的上升空间,高昂的房价,却都在一点点吞噬着年轻人做梦的空间,让人变成为一株被钉在窗台上的落灰的盘栽。
这些不被正视的压力,都被压缩在了那个四四方方飞满粉笔灰,一坐十二年的教室里。压抑和孤独,成为许多人青春的底色。

文学影视作品中描写青春的素来不少。有《山楂树之恋》中,上山下乡的40、50后们的艰苦羞涩;有冯唐笔下,烫起蓬松卷发、刚刚学会跳迪斯科的60、70后们热情奔放的青春。唯独80、90后的青春,还未被严肃全面地描绘过。
一是因为我们这代人还不够老,老到拥有重新解读自己历史的话语权。二是因为我们这代人中,还未出现手法老道到足以提炼出时代脉络的作家。
80、90后中不乏出彩的作家,但他们的创作多被当作“青春文学”,那些情绪和伤感也被当作无病呻吟,并不被主流所认可。
直到双雪涛写出了这部半自传小说,《聋哑时代》。
香香的橡皮,白色修正液,绿格子作文簿……成年以后,校园时光的记忆似乎都被镀了一层柔光的滤镜。我们缅怀青春,试图在庸碌的成人生活中靠着它们发掘出一丝甜味。
而这一次,《聋哑时代》却把糖衣一一剥离,还原出80、90后的青春残酷而压抑的本来面目。
校园是权力的缩影
不知为何,每个班级都会有一个人人都爱的早熟少女,一个总是坐在教室后门没有同桌的贫嘴同学,一个爱打小报告的老师的走狗。那个早熟少女必定早恋,老师的走狗必定串联殷勤的家长帮班主任收取补习班费用。
好像我们都被塞进了同一个脚本的沉浸式剧场,每个角色都贯穿始终地扮演着自己的人设。

《聋哑时代》的故事就以这些同学展开,科学怪人刘一达、天才少年霍家麟、古怪早熟的迷人女孩安娜,永远穿白衬衫的艾小男……面对现实,有人激烈反抗,有人陨灭、失去踪迹,更多的孩子变得沉默寡言。
而故事走向却也并不陌生,在早恋中尝试人生的女生被冠上“荡妇”的标签,为好友写大字报抱不平的贫嘴同学被勒令退学,老师的走狗最后成为银行小职员,懂事圆滑的两面派同学凭借圆滑官运通达。
少年们在家长、老师、学校构筑起的权力机制下压抑自己,将自我客体化,嵌入社会各界共谋下定好的角色模版,走向平庸,或走向自毁。

双雪涛说,“我写《聋哑时代》其实是想把学校当成社会的一个缩影,或一个典型的标本来写的,有一个面目模糊的校长,有已经被格式化了的、简单粗暴的老师,他们把学生当成手里的行货。校园绝对不是青春那么简单,它是权力的缩影。而你作为一个孩子,是这个权力关系里的弱者。”
而父母,只是这个庞大体系下被磨平棱角的市民典范,早已成为了权力机制的共谋。
小说中同学霍家麟爸爸:“两个人简直一模一样,只不过他的脸像是霍家麟的脸不小心掉在地上,被过往的行人踩了几年。”霍家麟的父母为了帮助儿子获得学校的原谅,可以在校长面前狠狠打骂儿子。
而小说中“我”的父母,则在下岗潮中仍相信着“无论如何国家总会给口饭吃”,即使最后战战兢兢推着小车走上街头卖茶叶蛋也是如此相信着。他们咬着牙东拼西凑地凑出九千块赞助费,相信只要交了这九千块,孩子就会拥有美好的未来。
当意识到梦想破灭时,父母却只能拿出皮带抽打自己的孩子,面对孩子受到公权力的不公待遇,却又装聋作哑起来。
胆怯不是贬义词
“我”作为一个普通的初中生,对抗这个权力体系的唯一方式,就是努力考了一次年级第一名。但又因为奖励的分配,第一名的名次很快就被抹去。“我”为了克服不公带来的失落和愤恨,只好说服自己,自己只是一个与一切美好事物无关且平庸无比的人。
小说中有一段描写作为主角的“我”的心境:
我没想到跳楼,吃安眠药,卧轨之类的方式,只想到用剪子剪破自己的喉咙。也许是我想在死之前,先成为一个完完全全的哑巴。其实我当时并没有意识到,只要换一个方式就可以活下来,像动物一样活着,放弃思考的权利,放弃对美妙事物的期盼,按照他们教我的方式,做一个言听计从的孩子。
——《聋哑时代》第七章《她》

其实我们大多数人,在自我意识萌发的少年时期就具备了对社会的观察力和理解力。我们的理解力从那时候起再未增长过,反而是一直在衰退。
曾不止听一个朋友述说过,他们在十几岁的青春期都曾体会到满满涨涨的情绪,和由此产生的激越的思想。但后来为了学习,或者为了完成别的什么事,主动远离了让自己情绪波动的人事。
更准确地说,是学会了对让自己情绪波动的人事视而不见。
通过关闭感官,阻断敏感,有意忽视一些无法解决的事,正如小说中的“我”,“决定做一个和别人一样的人,老师说什么,我认真听,不要去找她的破绽,不要想学这些到底有什么意义,不要有无谓的坚持,和百害而无一利的自尊。”
“我”心有不甘,痛苦地挣扎,却越来越像一个典型的言听计从的孩子。
成绩中下,其貌不扬,唯一的写作爱好在被老师痛批后便不再提笔,懦弱不敢正面与老师对抗,不敢为自己的朋友说话,不敢对喜欢的女生表白。浑浑噩噩,吊儿郎当,最后考了一个三本大学,成为一个收发传真的小职员,像极了卡夫卡小说中的人物。

台北二手书店蠹行书店,位于青田巷,门口招牌有殷海光的话,双雪涛摄于2011年
故事有一个俗套却令人温暖的结局(当然也因为出版社的要求),原本失败的“我”,最后终于写出小说并成功出版了。
这是双雪涛留给我们的小小希望:“我是一个胆怯的人。胆怯不是贬义词,是青春的一面。勇敢者有勇敢者的方式,披荆斩棘,无所畏惧,把伤疤当成勋章。胆怯者有他们的路,匍匐在黑暗中,累了歇一会,可能短可能长。最后每个人都会以自己的方式到达终点。”
一个少年的自白
尽管小说的主角们都是初中生,讲述者也是初中生,文字间却没有一丝动摇与犹豫。它举重若轻地描画成人的市侩迂腐,对准尖锐的、不该被言说的矛盾,对人性的刻画更是入木三分毫无留情,却也因此更深层地留住了人性中美好温暖的一面。
叙事风格则充满碎碎念的生活感,像聊天似的,但总能落在一个让人心中扑腾一惊的地方。
之后的很多年我一直在想为什么我一度和这个人成了不可救药的死党,也许是我们后来都成为了疯子,想必当初未疯的时候已经有些病状的前兆让我们不自觉地相互吸引,终于成为一对除了有疯病之外,毫无共同点的挚友,也可能是我们彼此需要对方在自己一无所知的领域提供一点安全感。
——《聋哑时代》第一章《刘一达》
这样敏锐和尖刻的视角,仿佛作者在初中时就已成为了大人。又或者,作者保留着初中少年的面目,直接变成了大人,带着所有敏感,不适,脆弱,无可奈何,和对光明未来的卑微希望。
《聋哑时代》是特别的,它更像是一个少年有些急切的自白。在写完这本半自传体小说后,双雪涛说:“我知道自己再也写不了这样的东西,可能我成了另一个人吧,从那时开始,我就要作为另一个人活着。”
他坦诚,一个职业作家不可能永远只写自己的生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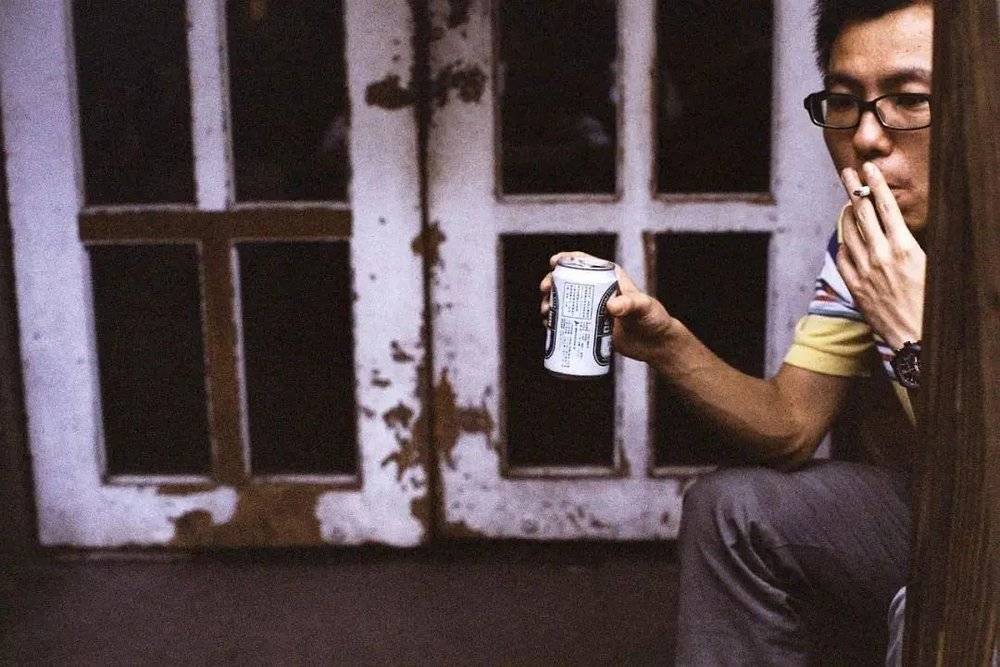
双雪涛,摄于台北,2011年
是的,这本书后,双雪涛进入了更为成熟的创作阶段,写出了《北方化为乌有》,写出了《平原上的摩西》,写出了《刺杀小说家》,小说要被搬上大荧幕,也获得了更多文学奖,被誉为80后“迟来的大师”。
双雪涛写由盛转衰的沈阳铁西区,悄无声息的改革阵痛期,工厂停产,工人下岗。颓败的厂房,困蹇的居处,混乱肮脏的街道,像艳粉街、九千班等常在双雪涛作品中出现的地名符号,都脱胎于《聋哑时代》。
但他的笔触更多对准的还是人,那些被侮辱与被损害的普通人们。酗酒、下棋、撞球、游荡、斗殴,却也在无边的坠落与虚空中,试图找回自己的神祗,以及人的尊严……

《聋哑时代》中出现过的许多鲜活的人,都更为妥帖地融入了一个个精彩绝伦、不着痕迹的故事。比如小说描写的同学霍家麟,在《我的朋友安德烈》中,永远成为了一个对抗时代的疯子。
只知道勤勤恳恳地卖茶叶蛋的父亲,表达感情的方式,就是带儿子吃下十二个冰淇淋球。这个父亲形象,也出现在了另一篇小说《大师》里。
双雪涛喜欢写人,这些一个个孤零零的人,是他小说的核心:“我得把我认为被埋没掉了,被忽略掉了,被遗忘的历史和个体写出来,当时写这个小说(《聋哑时代》)有种责任感,是替我自己发声,也是替我那些朋友、儿时的玩伴们发声。”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看理想(ID:ikanlixiang),作者:苏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