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扫码打开虎嗅APP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凤凰网读书(ID:ifengbook),作者:梁鸿,整理&编辑:巴巴罗萨、白羊,主编:魏冰心,题图来自:《一直游到海水变蓝》
阳光,浅滩,芦苇荡,一个人静静地坐在河床上,这是《一直游到海水变蓝》留给作家梁鸿的一个镜头。而这个“在河边坐下来”的瞬间,恰恰是她曾经想象过人生里最完美、最快乐的事。
十年前,梁鸿回到中国的“病灶”和“悲伤”:故乡梁庄,在这里完成了对自我的洗刷,重建了与亲邻的关系,找到了乡村的历史位置,十年后,她继续进行着另一种社会身份的追寻——为什么梁庄里的女人没有名字?吴奶奶,霞子妈,多子,她们本来是谁?她们其实是谁?
对于梁庄的一切,梁鸿依旧充满好奇、理解与共情。她讲那些沉默的乡下女人:抗婚逃走的,与强奸犯结婚的,承受多年暴力直至丈夫去世的……她们不是社会新闻里的拉姆,更不是影视剧里的樊胜美、房似锦,但她们也有具体的面孔,和不比任何人稀薄的生活。
作为知识分子和写作者,梁鸿自命为乡村“代言人”,用十年的自我袒露,换一些追问、叩问和质问。有人说今天的女性谈得够多了,真的够吗?她们身上有普世价值观,有情感共鸣,有学术概念,但在梁鸿看来,很多话“都是轻飘飘的,是不落地的”,终究,“你不能代替她过她之后的生活”。
10月13日,作家梁鸿与凤凰网读书编辑魏冰心在法国文化中心进行了一场对谈,本文即该对话和观众提问的内容实录。
1. “没资格代言,就不说话了吗?”
凤凰网读书:首先请梁老师讲讲《梁庄十年》写作的缘起,您是带着怎样的一种心情来写《梁庄十年》的?
梁鸿:当年写《中国在梁庄》时,我最大的愿望就是想通过尽可能谨慎而深入的书写,把村庄里真实的生活形态呈现出来。《中国在梁庄》花了四五个月的时间写完,当时非常开心,因为故乡本来只存在于我的心灵深处,突然间再次呈现在现实生活里,并且对精神世界产生了巨大作用。我真正看到那样一群人在生活,虽然他们之前也在生活,但其实是我被忽视的,或者是被我遗忘的,或者说我没有真正去体会过那样的生活。所以写这本书是一次重新发现自我、重新发现故乡、重新发现中国生活的过程,这是意义非凡的。

《中国在梁庄》,梁鸿 著,台海出版社 | 理想国
《中国在梁庄》后来引发了一些讨论,比如说“大国弊村”、“乡村沦陷”,但对我自己而言,好像还没有完成。因为它写的是梁庄人在家的生活,实际上没写在外的打工者,这是第二本书——《出梁庄记》的缘起。我想,只有把在外打工的梁庄人也写出来,它才是一个当代的完整的村庄。
因为当时在家调查的时候,我发现虽然打工的人常年不在家,但梁庄还会为他们而欢欣鼓舞,比如有一张汇款单寄来了,有个人回来了,整个村庄就一片沸腾,喝酒、聊天、打牌,像过节一样,所以其实他们还是这个村庄的人。2012年,我花了很大工夫,跑了一年多,采访在全国各地打工的梁庄人,最后写成了《出梁庄记》,我觉得这本书对我有更重大的意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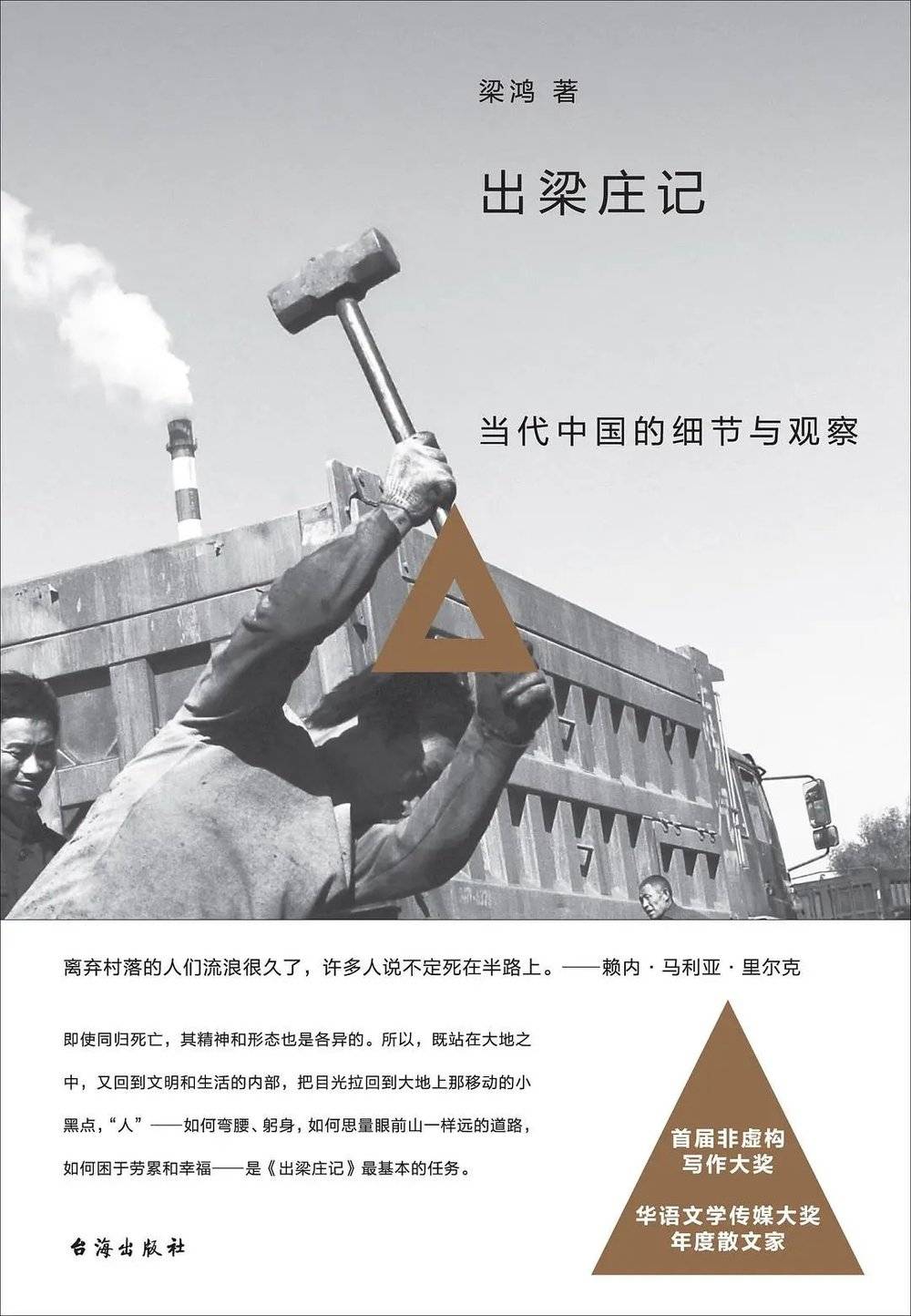
《出梁庄记》,梁鸿 著,台海出版社 | 理想国
写完这两本书,我好像已经完成了一件事,已经重新洗刷了自己一次,不管是回归学术还是重新写作,都觉得自己得到了很大的教育。但脚步是停不住的,我在这十年之间来来回回,和梁庄的人特别亲密了,有的人老了,有的人去世了,有的人出生了,梁庄像一条永远流逝但永远都在的河流一样,我希望把这种流动也写出来,所以今年出了一本《梁庄十年》,从我第一天开始准备写梁庄到现在,正好是第十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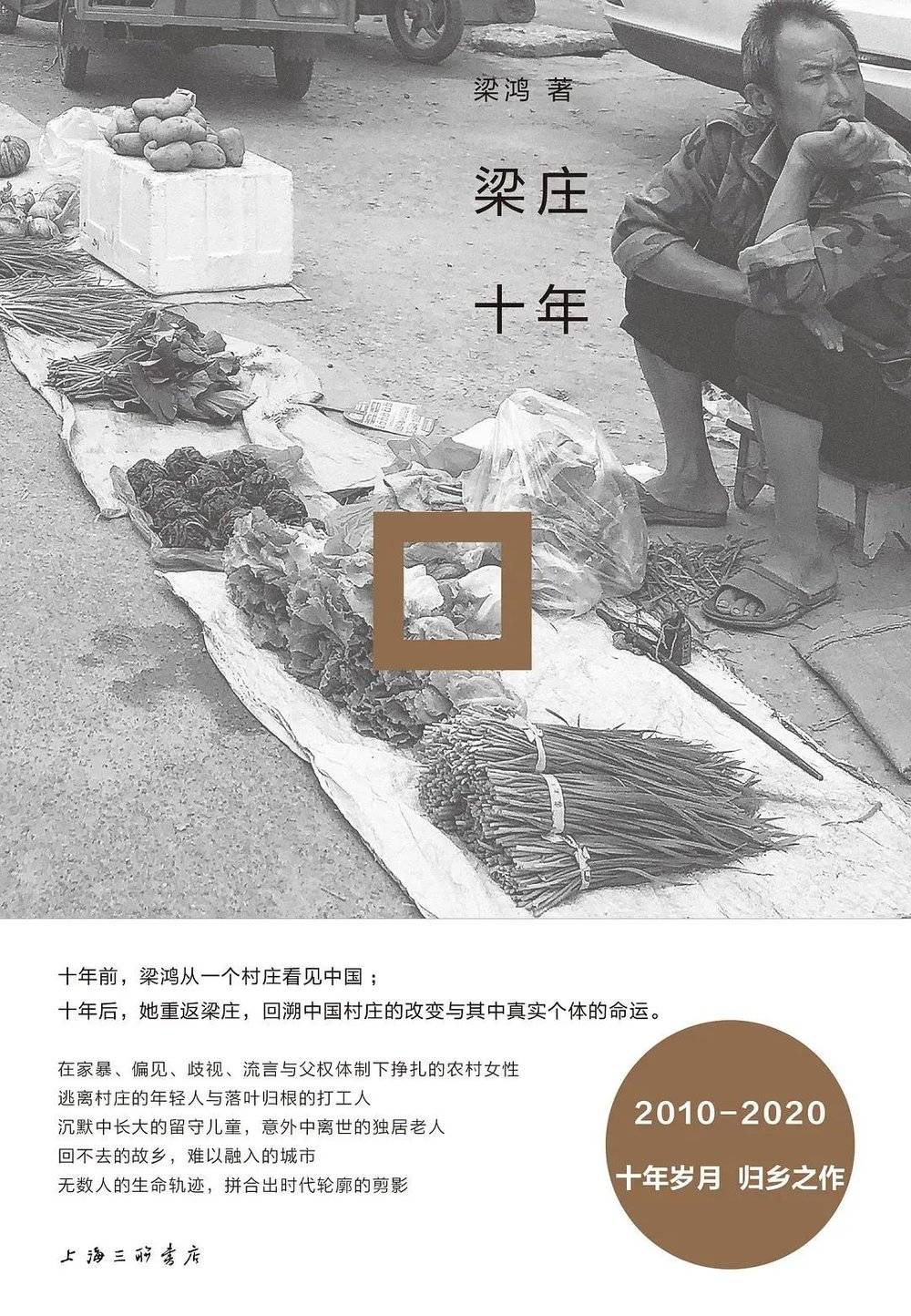
《梁庄十年》,梁鸿 著,台海出版社 | 理想国
为什么写《梁庄十年》呢?前两本可能是一个比较大的、整体的社会性书写,这本是从相对细微的、小的切口去写。我想日常化的梁庄也是非常重要的,正是人生中非常微小的东西支撑着我们的喜怒哀乐,支撑着我们一天天活下去。
包括这三本书里有一个很重要的人,吴奶奶,第一本书里我写她的孙子在一条河里淹死了,第二本书里我采访了她的儿子儿媳,那对在青岛打工的、死去的孩子的父母,第三本书里我写到有一天她去理发,让孙女带着她去,其实她是想上街玩。我想这样一个非常可爱、日常有点耍赖、幽默乐观的吴奶奶,才是一个相对完整的吴奶奶,这也是她的存在的面向。
《梁庄十年》最后一章写的是一个少年,叫阳阳,他在《出梁庄记》里才六岁,到《梁庄十年》已经十四岁了,从一个小男孩变成了一个少年。这让我觉得时间简直太有意思了,这样一个沉默的少年,我看到他的过去如何影响了他的今天。所以我想把梁庄继续写下去,一方面可以记录当代村庄不断往前走的步伐,另一方面也想留下每一个村庄人的历史,尽管他们都无名,但我希望能够赋予他们姓名。
凤凰网读书:《梁庄十年》跟前两本书有个不太一样的地方,它专门开辟了一个章节来讲梁庄女性,叫《丢失的女儿》。您写到其实是在一个很日常的情况下,发现这个人叫吴奶奶,那个人叫霞子妈,另一个人叫万家的媳妇,她们都是没有姓名的,只是别人的母亲、别人家的媳妇。联想到当下,女性主义貌似一路高歌,好像女性群体有了自主意识,地位得到很大的提升,但戴锦华老师说,网络上女性主义的叙事其实是中产的、城市的,很显然跟梁庄这些女性是有鸿沟的。所以也想请梁老师谈谈这个话题,您怎么看?
梁鸿:我前两本书里女性写得不多,当时也没有深思。到《梁庄十年》,当时第一章已经写完了,写的是一位老年女性,有一天被别人扒出来她年轻时候的风流韵事,然后张贴在电线杆上,一下子变成了村子里的轰动事件,其中有个小细节,就是这张小字报是韩家媳妇发现的,我非常自然地写了这句话。然后我在写第二章《丢失的女儿》的时候,突然发现我根本没写韩家媳妇的名字,我也不知道她叫什么名字。
这样我就回想到,我前面两本书也非常自然地用了唐嫂、吴奶奶这样的称呼来写这些女性,但是我写到堂哥们的时候,我都会说堂哥万生、堂哥万毅,他们都有名字的。那一刻我非常震惊,因为我觉得我还算是一个女性主义者,我读博士期间曾经想写女性方面的论文,看过不少女性主义的书,在日常生活中也非常关注女性的社会生活和社会运动。也许有一种不易觉察的文化惯性,像我这样还算有点所谓的知识背景的人,也会很自然地这样写作。所以我就专门加了一个注,把这个过程写下来,其实也是希望能带动读者思考,是不是这些东西已经成为日常了,而恰恰是日常值得我们警醒。
后来我就重新做了写作上的调整,组织了一场对话,请了吴奶奶、霞子妈,请了我的三个姐姐和其他几位更年轻的女性,我们在一起聊天。我就说有谁知道吴奶奶、霞子妈的名字?然后我问吴奶奶,你到底叫什么名字,她非常地羞涩说我忘了。她当然没有忘,肯定不会忘,只是太久太久没有人提起过了,她的身份就是奶奶,可能更早的时候是妻子,但是她嫁到梁庄以前那18年的生活已经完全被遗忘了,甚至她自己都遗忘了,所以我那章就叫《丢失的女儿》,其实就是想写出女性的身份,女性的主体是如何呈现的,又是如何被遮蔽的。我觉得恰恰是最日常的称呼、最日常的看法、最日常的行为,蕴含着文明内部最大的裂缝,今天的女性看似有好多好多的运动,有各种各样的讨论和争论,但其实女性生活内部的裂缝,我们是看不见的。
这一章里,我也采访了在北京生活的三位梁庄女性,她们都是我童年的伙伴,是我童年时在村庄里特别知名的女性,但是到了现在,她们生活的境遇是有很大变化的。我觉得我写女性,不单单是为了彰显女性的什么,而是希望大家能够意识到在我们最日常化的生活内部,关于女性所谓的某种偏见,关于我们自身的情感状态,其实都特别值得思考。

作家、学者梁鸿
凤凰网读书:像刚刚提到的女性的鸿沟,您觉得有没有什么方式可以让它稍微缩减一些,或者能够建立一个桥梁,让农村女性和城市的话语体系连接上?
梁鸿:我觉得挺艰难的,首先需要我们这样的书写者,因为中国大部分农村还是处于失语状态的,处于一个被代言的状态,经常有人会说你凭什么代言它,但我觉得这是一个伪问题。既然农村是沉默的大多数,我们真正应该思考的就是如何去代言、怎样更好地去代言,而不是是否有代言的资格,这是个无解的问题。是啊,谁都没资格代言,但是我们又该做什么呢,因为我们没资格代言就不说话了吗?我觉得这样是不对的。所以既然我想写这些女性,那我就要好好去写,书写是非常必要的,它几乎成为一个最大的桥梁。
我看到很多做深度报道的记者,像《南方人物周刊》,像《人物》,包括真实故事计划,他们采访了很多女性。包括有一天我看到拉姆案,大家都知道了,她在网上算是个小网红,但因为跟丈夫关系不好,后来就被她丈夫烧死了。我当时看到一个细节,就是记者去采访拉姆丈夫家的邻居,邻居们都摇头不语,觉得拉姆不是一个守妇道的女孩子,就是虽然同情拉姆,但又觉得她自己做得也不好,天天在网上抛头露面、载歌载舞。换句话说,这些沉默是可以杀人的,因为它们无形中支撑了她丈夫的某些行为的合理性。
我觉得这其实也需要记者,需要具有书写权利的人去书写。这需要书写者去架构多方向、多维度的思考空间,而不是简单地做判断,否则我们就是愤青,只是发发言,骂一骂,是于事无补的。所以我自己也是持有非常谨慎的书写态度,希望把一个事件多维度地呈现出来,写出内部空间的肌理,真正让读者感受到,这是有可能成为桥梁的,尽管我其实并不乐观。
2. “很多话是轻飘飘的、不落地的”
凤凰网读书:您本人作为从梁庄走出来的女性,也讲过自己曾经在农村当小学老师的故事,说那个时候拿到一本盗版的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一边读,一边幻想一个更广阔的世界。后来的故事就是梁鸿老师走向了更广阔的世界。这中间的历程大概是怎样的,能不能给我们分享一下?
梁鸿:这个历程其实是比较傻的一个孩子往前走的故事。我自认是个比较单纯的人,想着我要上学,我要读书,我要上中文系,就朝着这个信念走了。我觉得正是这样一种单纯的热爱,支撑着我往前走,虽然当年我是中专毕业出来教书,教书后再出来读书,其实还挺艰难的,但我自己好像并不觉得艰难,当时还在日记里写知识多么让人开心。
但是万变不离其宗,我不管上哪个学校,大学校、小学校还是什么样的学校,文学作品都是最大的营养。另外就是我较少考虑到现实问题,这个不是有意的选择,而是我好像缺了这根弦。当时英语是比较好的专业,学法律更能挣钱,但我好像觉得只要我能活就行,我对生活的要求比较低,可能不会想着一定要吃燕窝或者吃什么,就喝一口汤也挺好的。我现在也是处于这样的状态,所以读书、写作还是让我觉得很愉悦,让我能够真正感受到心灵的纯粹。

《一直游到海水变蓝》中的梁鸿
凤凰网读书:作为一位女性写作者,您在写作的时候有没有遇到过什么困境,或者最大的困境是什么?
梁鸿:其实有很多困境。我在《神圣家族》里讲过一个故事叫《美人彩虹》,里边有个美女老板娘,她一辈子没出过门,但能把她的小店经营得活色生香,成为吴镇最著名的百货商店。当时我写她的时候有一个特别大的困惑,就是我要怎么描述她。因为她的原型是我的一个同学,长得非常美,是那种雅致的美和粗俗的美的结合体,我不想把她写成某种性的存在,而她身上又具备这样的因素,那我怎么来处理她,怎么把她塑造出来?

《神圣家族》,梁鸿 著,中信出版社
最后我一方面写了她的外貌,另一方面写了她对小店的依恋,那是一种物化的依恋,希望能够摆脱她作为一个性感的符号的形象。这种努力是否成立很难说,但对于一个女性作家而言,当我试图塑造女性的时候,我出于本能不想把她写成被观看的对象,“天生尤物”,我对这样的词语是非常反感的。我看过很多这样的男作家的作品,但都不太喜欢,所以这是我最本能的反抗。当然这种反抗,是否真的反抗了,是否写的还不如男性作家,这就是另外一回事了,这跟观念和书写能力都有关系。
凤凰网读书:能再给我们分享一两个梁庄女性的故事吗?
梁鸿:那我分享一下《梁庄十年》里的一个故事吧。这本书的第二章写了我与姐姐们和奶奶等人的闲谈,她们聊了一下各自的童年伙伴,我也找了我的童年伙伴,结果发现很多人都流散了,找不着了。其中一个女孩子叫多子,这是她的真名,意思是这个孩子生下来就是多出来的那个,农村里会有这样的名字。
多子家和我家中间隔了两户,我每天上学必须先经过她家,我们年龄差不多,就变成了非常好的玩伴。她家很穷,比我家还穷,父母也没有知识,所以她就没上学,但是她非常健壮,庄稼活干得非常好,我非常崇拜她。我每天放学后不回家,先到她家坐一会儿,看她在那忙忙碌碌,又是做饭,又是喂猪,我就跟在她后面。我简直太佩服她了,那时候农村都有麦场,她会在那里翻跟头、打车轮子,甚至也能保护我。
后来我到镇上去读书,又读了师范,离开村庄,我们俩交往就比较少了。过了几年,我发现在村庄里找不到她了。我父亲说因为她家比较穷,村里有一户富裕的人家想让他们家孩子娶多子,但是多子家得把自己的宅基地给他们,本来说好了,多子不同意,就被赶出村庄了,后来她找了一个人家出嫁了,我们俩就再也没见过。因为她父母也都去世了,她家的房屋因为纠纷被封,村子里就再也没有这个人了。去年因为写《梁庄十年》,我才回家又找到她、见到她。那真的是完全不一样的人生,当然还挺开心的,但还是觉得不一样了。
有很多这样女孩子的故事,随手拈来,太多太多了。包括我妹妹的一个同学,年龄跟我一样大,她出去打工认识了一个女孩子,春节到她家过年,结果那个女孩的弟弟强奸了她。被强奸之后她怀孕了,就去找那个女孩子,后来就说干脆让他们俩结婚吧。就是这样,让你听了特别无语,但它又是非常现实的解决问题的一个方法。在乡村,你很难用一个理论来解说他们的生活,那你说怎么办呢?让这个女孩子去告这个男孩子吗?好像那样她就身败名裂了,对吧?那在乡下要承受多大的议论,所以干脆就结婚了。她现在40多岁了,之前在北京打工,得了哮喘,还挺严重的,后来回家了,现在一个人在家种了十亩地,养了两个孙子,她的丈夫和她的儿子都在外面打工。
我在听这样的故事的时候,心里特别复杂,不能说悲观吧,就是有时候在生活内部,你很难用在现代社会里接触到的某种理念做判断。既然他强奸你,你为什么不告他,为什么还要跟他生活?这些话都是轻飘飘的,是不落地的。但是反过来你又觉得,她好像也不值,是吧?但对她而言,她觉得那是最好的解决办法了,她也不用承担她可能面临的身败名裂的遭遇。所以我在写乡村女性的时候,我自己也避免下判断,因为我不能代替她说什么。虽然在我们的概念里是有很清晰的法律界线的,但真正等你面对现实生活的时候,这些女性的存在和生活方式,让你没法去判断。
包括我在书里写到的另一个人,叫春静,我们俩是同班同学,她长得特别好看,比我大了3、4岁,属于那种有书香气,又漂亮,又善解人意的女孩子。后来她嫁给镇上一个党委书记的儿子,那时候在乡亲眼里是高攀,大家都觉得她特别幸福,但没想到这个男孩子酗酒,酗酒之后就打人,每天喝酒每天打她。我把她请到我北京的家里聊天,我们三个女孩子一起聊天,在一块睡觉,待了两天挺开心的。
我听她讲这些事,简直就像天方夜谭一样,怎么可能呢?她跟她丈夫结婚19年,后来她丈夫死了,我们长舒一口气。他真是每天喝、每天打,她给我举了个例子,说她刚生完孩子的时候,有一天在家里用高压锅炖汤,她丈夫喝酒回来,端起高压锅就往她身上砸,幸亏那锅汤是已经放了一段时间的,而且砸到她背上,能让她护住孩子。我觉得这简直不可思议,因为她对于我来说是非常有见识的一个人,她还是村支书的女儿,她们家在乡村里是有头有面的人物。后来她跟我说,这个男孩的父母是我们镇上最高的家庭,她父母又是村庄的干部,都是有头有面的人,离婚很丢人。我觉得真是,后来幸亏他死了,当然这样说有点不太公平,但也挺公平的,这19年来她所忍受的东西,一定是大家无法忍受的,大家可以去看那本书,我都说不出来。
但是这个女孩还在自救,这让我非常感慨。不管生活怎么踩她,怎么让她到了一个最泥泞的地方,她依然努力探出水面,试图呼吸,甚至不单单是呼吸,她还要寻找更平静的内心。她信佛,现在给我的感觉是非常平和、非常温柔的,不单单是悲惨的。但在这样一个悲喜交加的生存过程中,你会发现女性所遭遇的其实是看不见的,她内部受到的伤害,如果我不来写,她真的不会讲。
当然这都是一些事例吧,我希望用女性的故事,包括我身边的女孩子的故事,写出我们的当代生活。这就是我们正在行进中的一种中国社会的现实状态,其实就在我们身边,只不过我们没有真的去关注,去深入理解。
凤凰网读书:刚刚您讲的很多处都让我觉得,怎么会这样?其实有一个很大的问题是她们不知道怎么去做,我们现在应该做的第一步肯定是像您这样去书写,让这些人被更多人看到。另外我觉得还有一个东西不知道怎么解决,就是让女性知道,在这种情况下是可以say no的。我希望有一天女性都能知道如果自己被强奸了,就要站出来指责他,他应该被抓起来,而不是我要嫁给他。
梁鸿:这可能是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虽然好像是很显然的事,但在实际生活中真的需要很长时间来改变。只有全社会都不认为女性被强奸是羞耻的,那个时候才有可能发生真正的变化。社会的眼光是最难改变的,那种指指点点是我们文化深处最难以去除的东西,尤其对于女性而言,它带来的羞耻是无法想象的,带来的压力是让人无法继续生存的。

《盲山》剧照
我在《出梁庄记》最后一章里写了一个8、9岁的女孩,她不是我们村庄的,是到我们村庄看病。她被邻居一个老头强奸了,未遂吧,但已经破坏了身体。当时我花了两天时间陪伴这个女孩和她的奶奶,真的不知道怎么办,我当时特别绝望,因为这等于是我具体参与的,我也找了派出所的警察,找了医生,我甚至还做了录像、录音,到现在都保存着,我希望有一天能够呈堂证供,当作证据。但实际上我后来再也没跟这个女孩子联系过,我们相忘于江湖,因为我不想让她知道我知道这个事情。
她的奶奶到最后实在没有办法,选择了沉默。那时候我也在找人,真的是觉得他太坏了,我们一定要用法律去约束他,但是经过了挣扎和斗争之后,我也屈服了,到现在已经过去七年了,我没有再跟这个女孩子联系过,我也真的忘了她在哪个村庄。这是我作为一个现代知识分子,一个所谓的好像斗士一样在呼唤的人做出的选择,只能这样,这才是我们所面临的困境。
你不能说我一定要鼓动你去告,这也不公平,对女孩子来说不公平,因为你不能代替她过她之后的生活,所以你只能尊重她的选择,这是我们面临的一个特别大的困难。我们怎么样让法律真正成为法律?法律能让我们挺直腰杆,但不能让我们克服羞耻,因为羞耻是一个道德名词,它不是一个法律名词,所以当你没办法解决这些事情的时候,所有的法律都变得无所依附了,就是这样一个特别尴尬的,但是又无奈、又长远的一个问题。
3. “不要塑造极端的形象,虽然那很抓人”
凤凰网读书:这可能是刚刚我提到的鸿沟的地方。不管是学者、法律的制定者还是更多能够发出声音的人,他们不应该只讨论所谓的城市中产女性的问题,而是应该看到更广大、更基层的女性,她们真正面临的一些问题。第一步就是让这些女性更加知道。
梁鸿:对,我现在看到很多电视剧都特别无语,女性前半生被老公养,后半生突然一路开花,碾压了她的前夫什么的。那些编剧很有水平,但我经常在呼吁一件事,就是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刻板印象?你既然拥有权利,你在言说,对吧?编剧是大众传媒的一部分,肯定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为什么不稍稍增加一点复杂性?你稍稍增加一点都行,不要那么简单,那么偶像,那么时尚,那么容易,有那么容易吗?一个女性前三年没有工作,被老公养,后面突然开挂,有总裁护着她往前走,可能吗?对吧?它把女性的生存、女性所面临的困境,想象得太容易了,那不是解决的办法。一个35岁的女孩子,拖着一个孩子,能有几个深爱她的总裁?加上她已经脱离社会很久了,能找到工作吗?这本身是一个特别值得探讨的问题,结果变成一个一路升级打怪兽的过程。
所以我经常说,电视剧作为流行的大众传媒,为什么编剧们不能在迎合所谓的资本要求的同时,也加入一点点东西,也不是不可能的。当然我觉得很多人是不知道的,包括从他们对农村女性的刻板化的描写来看。我经常举一个例子是《双面胶》,大家可能看过,很著名的一部电视剧,把一个农村婆婆写的很不好。包括前段时间孙俪演的《安家》,她是一个房产中介,早年被她的母亲抛弃了,我看一集就气得受不了。也许在农村有这样的家庭,在城市也有这样的家庭,但是当你如此漫画般地把这样一个农村状态写出来的时候,它影响了无数人的观点,“千万不要找凤凰男”,“千万不要找农村出来的男生”,它会把你拖到深渊里。我觉得这加剧了城乡对立,加剧了我们对乡村的刻板印象。

《安家》剧照
乡村是现实,我们还有那么多乡村人民,为什么要这么写呢?没有一点点复杂性。比如说像我,我的姐姐帮助我完成了学业,那我回馈我的姐姐,当然是正常的,为什么不可以回馈她呢?那你的家庭那么贫穷,举全家之力让你到了上海工作,对吧,你为什么不可以帮助你的家庭?这是错的吗?你作为他的妻子帮他,真的变成深渊了吗?太绝对化了。我觉得这真的是当代社会里的问题,一方面在弥合二元对立,另一方面所有艺术形象的塑造,都在加深这种东西。所以作为一个作家,作为一个写作者,我自己肯定要竭尽全力去关注生活内部的复杂,不要去塑造极端的形象,虽然那很抓人。
凤凰网读书:但当编剧们这样去写的时候,有没有可能也是因为在迎合观众,观众喜欢看爽剧,这背后到底是什么样的逻辑?
梁鸿:我觉得不要把观众想得那么愚蠢,我们是喜欢看爽剧,喜欢看古装剧,卿卿我我,小清新,是这样的,但是在小清新里面加一点点思考,我们也是能理解的。编剧应该有一种职业道德,加入自己的思考,加入一点点,那些资本也不会一句就把你拿掉,但是如果一味地迎合,其实也把观众的智商想低了。其实是我们懒惰,说到最后是我们不愿意承担那些责任,觉得这样挺好的,观众那么喜欢看,骂得那么开心,把樊胜美的妈骂得要死,多开心?但是这真的是值得思考的。

《欢乐颂》剧照
凤凰网读书:最后我问一个问题,关于您面对梁庄人的时候,一个写作身份的问题。您在演讲里面提到过,您在西安跟一群拉三轮车的人沟通,其中有一个男孩,他才18岁,穿得还挺洋气的,但是面对您的采访,他就一直不敢看您的眼睛,好像是说您的存在让他感觉到了自己其实是一个“农民工”。我想知道,您这么长久以来的写作,对自己的身份是怎么认知的?
梁鸿:这也是一个慢慢嬗变的过程。我为什么说我希望这是一种谨慎的写作,因为我也可以不写我,把自己推得远远的,不承担任何责任,但是我写了我,我也是梁庄人,既然加了我,我的这个身份就非常重要了。很多人批评《中国在梁庄》里的我有点高高在上,情感过于充沛,这些我都承认。
但是到《出梁庄记》我开始做调整,站得稍微远一点,但我仍然在,我也把自己的疲惫、厌倦、不适感写出来,这种坦率的承认也是希望读者能够读到,这就是我自己,我是城市人,因为读书人大部分还是留在城市里生活得不错的人,我希望能够通过你对我的不满意,勾起你对你的不满意。另外我这种厌倦,这种不适感,甚至有点高高在上,也是我们这个时代走出农村的很多人的一种不自觉的反应,我也希望把自己袒露出来,供你们批判。
到了第三本书《梁庄十年》,我更加自在了,回到家里吃吃喝喝,玩玩乐乐,我突然觉得我就是梁庄人了,我不再是前面那两个要调查社会问题的人,这个时候我的身份好像更加隐蔽一些,也更能够融入梁庄一些。这个过程我经历了十年,其实挺珍惜这种变化的,如果有人一定还要研究梁庄,我希望他们研究一下“我”这个存在。“我”从一开始的不适感、分离感,到最后非常自在,其实是身份融入的问题。当你真正把目光投向家乡,你会慢慢爱上它的,虽然它仍然有缺点,虽然它仍然是那片荒寂的土地,里边充满了各种各样的问题,我觉得这种交织着的情感,才是最真实的情感。
也许过了十年,我的感受又变了,这是随着时间自然行进的过程,我希望我的情感的变化、身份的变化,也成为人类志的一部分,成为一份材料。我为什么这么想把自己袒露出来,也是这个原因,就是说一个人是可以变的,你对故乡的感情也是可以变的。我们现在经常会说,回到家里太讨厌了,三姑六婆老是问结婚了没有,我就会想,那为什么不能稍微耐心一点点呢,就跟她聊一聊又怎么了,就说没结婚又怎么了,多说一句话又怎么了,对吧?干吗非要说那是我的隐私,非要用那种现代的观念来维护自己?其实没必要的,她无非是想跟你聊聊天而已,因为她不知道要聊什么。

《我在他乡挺好的》剧照
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一个重新看待生活内部很多东西的过程,甚至可以说是重新理解中国社会生活的过程。因为中国社会生活里包含着城市和乡村,这是我们的现实,是不可回避的,如果你对乡村只有厌倦,只有拒绝,只有深深的不满和否定,或者漫画般的理解,那我觉得你对中国社会生活本身的认识也不全面了,我是这样思考的。
现场观众提问环节
现在有一种说法叫大龄女青年,有人叫“剩女”,指的其实是那些“三高”,所谓学习高、智商高、工资高的优质女性。有人说这跟女权运动有关,好像女性主义越高涨,这部分女性结婚越困难。我觉得确实面临这种两难,一方面要通过女性主义提高女性地位,另一方面如果它带来了副作用,怎么办?如何平衡两者之间的关系?或者说您认不认同这个逻辑?有没有两全其美的办法,既能让这部分女性大谈女权,又能使她们的婚姻变得更容易一些?
梁鸿:我觉得可以用一句话来说明这个问题,就是女性已经成长了,男性还没有充分成长。女性独立了,拥有了自我意识,会为自己而奋斗,男性还是需要女性结婚后在家里操持家务,没有跟着女性步伐一起成长,这是最大的问题。所以为什么“三高”的女性好像很难找到婚姻,是因为男的自卑,因为他自己没有成长。在现实中很多竞争领域里,男性对女性的观念还停留在非常传统的状态,他们还不愿意接受今天如此独立、如此美丽的女性的存在,所以我觉得这是急需改变的性别意识的问题,而不单单是个社会问题。
但我觉得也没有那么严重,因为没有丈夫也可以过。你们不成长,我们也没办法,对吧,虽然我们渴望婚姻,渴望有孩子,但是我们也不将就,你迟迟不愿意成长,那就把你抛到后面。所以为什么说阴盛阳衰不是一个笑话,几千年以后,在以男性为中心的文明里,男性已经变成一个蚕宝宝了,然后他还非常自得、自满。你经常不知道为什么这些男的这么自在,我经常质问我的老乡说,你凭什么认为你老婆该伺候你呢?人家才是个研究生,你是个本科生,你为什么呢?他就说我是个男的,你看这个理由很简单。虽然是玩笑,但它确实代表了一种最基本的状态。所以今天的女性不愿意再伺候蚕宝宝了,对吧,那我觉得挺好的,好好让自我变得内心强大,变得更加优秀呗。
现在有一些独立女性,她们内心其实非常害怕表达、表现出情感方面的需求,好像我表达了,我就不独立了,我就不强大了。所以怎么样才能达到一种平衡,既能勇敢表达,同时也能做到独立?
梁鸿:首先我们要承认人类的缺陷,我们都是软弱的人,软弱是正常的状态,而不是让人羞耻的状态。我今天撑不下去了,老板批评我了,爸妈批评我了,男朋友说我了,我很不开心,这都很正常。再独立的人也是有软弱的时刻的,我觉得这个尤其是女性一定要克服,不是说独立女性就必须非常强大,把自己武装起来,像刺猬一样,不是这样的,那不是真独立。我觉得真正独立的人是可以直视自己的内心的,知道自己也会有软弱的时刻,有想依赖别人的时刻。所以首先要自信,确定自己没问题,我觉得一切都还是非常好的。
我想问一个比较文学方面的问题,前几年我在索邦大学参加研讨会,研究虚构和非虚构,现在也想问问您是怎样看待非虚构创作的?如果站在理论的角度,您会怎么定义非虚构,怎么看虚构与非虚构的界限?
梁鸿:关于非虚构是否能成为真正的文体,让作家去写作,我觉得现在谈论它稍微有点早,因为非虚构文学在中国还没有经过充分的发展。就现在而言,中国的非虚构文学还需要创作实践来支撑,我也把自己当作一个文本实验的实践者,来探索边界,让书写者、研究者看到梁鸿是这样写的,她写的是不是非虚构。像《梁庄十年》里,我用了新的笔法,也是想能否拓宽一点非虚构的写作空间。虽然可能有非议,有否定,但对于我这个“协作者”而言,这种突破非常重要,因为如果只有理论没有实践,它就没有任何价值。
所以我觉得,非虚构文学作为一种文学样式,作为一种文体,是可以存在的,而且它存在的空间、空间的容纳性都是非常大的,像社会学、人类学、历史学都可以非常自然地融到文本里,还可以有人物口述,有田野调查,并且它可能成为一个新样式,引起读者的共鸣。虽然我是做学术出身的,但我一直信奉一个信条,就是要突破界线,不要被概念所束缚。我还有很多选题,以后肯定还要再学非虚构,然后等待时间,继续去写。但我觉得最好是它既是文学文本,又能提供很多交叉的思维给大家,成为一个丰富的非虚构。这当然是个想法,有待摸索和实践,但我充满信心。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凤凰网读书(ID:ifengbook),作者:梁鸿,整理&编辑:巴巴罗萨、白羊,主编:魏冰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