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扫码打开虎嗅APP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凤凰网 (ID:ifeng-news),作者:张小莲,编辑:马可,原文标题:《90后为独居老人整理遗物,揭开孤独死的残酷真相》,题图来自:电视剧《Move to Heaven:我是遗物整理师》剧照
“因为他过世了,他用过的所有东西难道就变成垃圾了吗?我觉得不应该那样去对待一个人。他的物品可能代表着我们一起度过的时光、我们的关系和联结,代表他生命中最重要的一些时刻,难道有些东西不值得留下来吗?”在西卡筹办的遗物展上,一位参展观众对人死后烧掉遗物的习俗感到不解。
西卡,90后,上海的一名整理咨询师。遗物整理是她的业务之一。这个对多数人而言仍很陌生的工作,被她这样描述:就像平日一样,正常地吃过早饭,正常地出门,去一个正常的家里,这个家不久前有人过世,但跟旁边邻居的家门也没什么区别,你正常地进门、打招呼,然后就开始整理东西。
“观念是我们遇到的最大的困境”,西卡深知,中国人传统的生死观无法一下改变。遗物被视为不吉的背后,是对死亡的避忌。
人们总是以金钱去衡量物品的价值,不值钱的东西难免被遗弃,甚至销毁。值得玩味的是,西卡在每一家的遗物里都整理出了钱,一个破破烂烂的袋子可能就装着几千元,“就像逝者留下的一个trick(诡计),你要是不用心整理我的东西,不好意思,这个钱可能就被你扔了” 。

而在西卡眼里,逝者留下的可能不是钱,而是一份情谊,一个念想,是带着温度的生命痕迹。
虽然整理的是死者的人生,但常常指向跟生者有关的话题,比如养老、亲子关系、弱势群体(孤老、心智障碍者)等等。正如直面死亡,是为了在终有一死的短暂人生里,更好地活着。
五线谱爷爷和写诗的爸爸
西卡出生于某国企职工家庭,从小作为“别人家的孩子”长大,保送上海外国语大学,毕业后从一家知名会计事务所的税务师,跨行转入BAT大厂做广告策划。身边的亲友都不理解,为什么放着体面的班不上,要去做家政保洁?
但对西卡来说,这是一个已经酝酿多年的决定。
2014年,西卡第一次打量自己的人生:万一离开这个世界,自己能留下什么?她想了很久,好像除了物品,什么也留不下。那是她第一次感受到,物品和生命的联结。也是她第一次意识到从小接受的教育只告诉她如何变优秀,却唯独没有教过她该如何认真对待生命。
这让她困惑于自己工作的价值,自觉“读了这么多年书”,只成为了庞大机器上一颗“可有可无”的螺丝钉,在日复一日的忙碌中越来越不快乐。她不想变成“社畜”,但不知道未来的路要怎么走,“人生的意义在哪里”。

2016年,西卡读了日本整理专家近藤麻理惠写的《怦然心动的人生整理魔法》,西卡一下被击中了,她恍然觉得自己活这么大,好像很多时间都浪费在不太喜欢的事情上,比如满足他人的期待,追求世俗的成功,在女性规训中不自觉地受限……当她试着给自己做整理后,发现整个人的状态、心境和思维模式都在发生变化,“可能真的是有魔法吧”。
一次健康危机后,西卡开始自学、实践,并于2019年辞职创业,成立了自己的家居整理团队,不过,她更想做的是遗物整理。在日本,普通的遗物整理是作为整理行业的一个分支,另一种则涉及孤独死、自杀等非正常死亡现场的特殊清扫,二者均属于成熟职业。但在国内,当时家居整理的概念尚未普及,遗物整理更是挑战禁忌的空白领域,她只能从最容易被接受的开始做起,“先让公司活下来,再慢慢推进”。
2020年春天,“求路无门”的西卡终于等来一个契机。
那年清明节前,西卡在网上看到了一篇题为《武汉遗物》的报道,里面记录了几位在武汉疫情期间逝去的人和留下的遗物。最打动西卡的是一位78岁的老先生,被送进金银潭医院时,已病重到不能下床走动,离世后,护士在他包里发现了一沓很厚的手抄五线谱,约30来张,都是他自己作的词曲。
看完后,西卡便有了志愿为这些家庭整理遗物的念头。在纪录片导演周轶君的支持下,她联系了近百个家庭,最终三家同意,其一便是那位“五线谱爷爷”。他热爱音乐,有小提琴、萨克斯、大小号、古筝、琵琶、二胡等近十样乐器,生前心心念念想在小区里组个乐队,总在老伴出去买菜时在家尽情奏乐唱歌,但只要遇到下雨天,就会放下乐器,拿着伞等候在老伴下车的公交站。
第二个家庭失去的是一位59岁的父亲,确诊入院两个月后去世,他的儿子希望重新调整书房的物品,将父亲的遗物更多地展示出来,放在最重要的位置。

当西卡将家中属于父亲的物品全部清出,依次铺在地上时,他的儿子才发现,父亲的个人物品最少,连爱好的书法都只用水帖练习,没留下一点痕迹。在一些零散的手稿中,父亲抄写了很多诗词,儿子感到很遗憾,从来没有问过他喜欢谁的诗词、有什么特别的感受,“没法再去跟他互动了。”
整理中途,儿子在父亲的一堆遗物旁边坐了下来,静静地待了一会儿。对他而言,这不仅是物品整理,也是心理整理的过程。他不想扔掉父亲的任何一样东西,也不愿注销那个用了近30年的手机号,怕之后忍不住给父亲打电话,听到却是一个陌生的声音。
西卡认为,遗物整理就像在生与死之间搭一座沟通的桥,让逝者得以纪念,生者得以慰藉。在武汉的尝试也让她意识到,照搬国外的理论经验或用一套模式化的流程是行不通的,“因为每个家庭太不一样了,需求也不一样。”
在54页的遗物清单之外
从武汉回来后,西卡将遗物整理正式纳入公司业务,目前有三位固定成员,汪悦是最早加入的兼职。她是一名民商事律师,五年前与西卡在徒步旅行中认识,对遗物整理有强烈的兴趣。2021年7月,他们终于接到第一个委托。
一位无儿无女的八旬孤寡老人,生前通过遗赠扶养协议将价值千万的房子等遗产,全部赠给照顾他十余年的护工小翠。老人去世后,小翠辗转找到季晨所在的公证处办理接受遗赠公证事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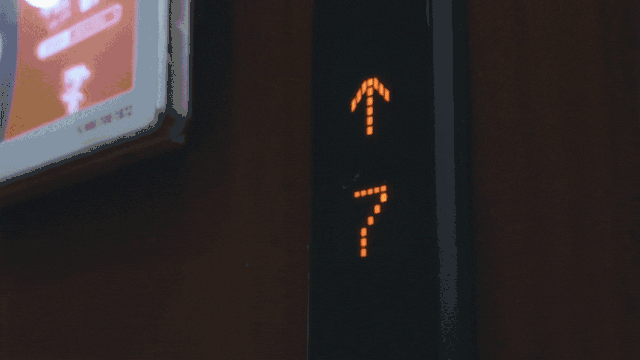
作为公证员,季晨需确认遗赠扶养协议的有效性,还要核查老人的法定继承人中是否存在“双缺人”,即缺乏劳动能力又没有生活来源的遗产必留份权利人,但小翠对老人的近亲属情况一无所知。另外,老人的遗产种类繁多,按2021年施行的《民法典》新规,小翠作为遗产保管人不得不承担起临时“遗产管理人”的职责:清理遗产并制作遗产清单。为了寻找老人近亲属的线索,同时保证遗产清单的客观准确,季晨提示小翠需要委托第三方专业人员来清点老人的遗物。
季晨想到了西卡。2019年,两人在首届安宁疗护大会上相识,常常交流遗物整理相关话题。“其实我们的工作就需要遗物整理,只是之前不太重视,这是法治的进步”,季晨说,过去遇到需要清点遗产的案子,都是公证员自己去做,但做得比较粗略,“拿摄像机一扫,房间一看没啥,这杯子不值钱,走了。”有时因时间有限,他们会快速“翻箱倒柜”,翻完了也不一定放回原位,他对此也感到很遗憾,觉得不够尊重物主。
在季晨看来,遗物整理分化成一种职业是社会发展的需要,“过去的财产传承很简单,一个人去世后房子给子女,也没有什么承载精神内容的物品,因为以前没有手机电脑,可能就一点日记照片。”如今人们的财富类型繁杂,一个不起眼的旧杯子,也许就是有上百年历史的古董。
与之相应,立法也改变了,“以前的立法只盯住财产”,现行《民法典》新增人格权编,个人对自己的器官、健康、去世后的遗体和隐私信息等有自我决定权,“以遗嘱的方式,对去世后除财产以外的涉及到人格的事物做出提前的安排,(包括)精神和肉体、殡葬仪式。”
而在继承编里,除了“制作遗产清单”的新规外,遗产继承第二顺序的兄弟姐妹若先于死者去世,其子女亦可代位继承。但逝者早年离开原生乡源,与血亲之间中断联系数年的情况并不少见,这时往往需要去寻找继承人。
季晨一年承办的超200例继承案件中,只有在遗赠、继承人下落不明、无人继承、遗嘱信托、保障弱势继承人群体合法权益等特殊情形下,才会针对性地委托专业整理人员参与遗产的清点,“估计不超过5件”。上述遗赠扶养案,便是民法典施行后第一个委托的案例。
逝世老人名叫唐启忠,出身于民国一名门望族,在历史动荡中经历抄家、坐牢、被判死刑等磨难,家族逐渐没落,兄弟姐妹分散各地,均已离世。季晨不仅要从遗物中寻找小翠履行了扶养义务的证据,还要寻找唐启忠血亲的线索。因此,西卡的整理工作是关键的第一步。
2021年8月,西卡等三人走进唐启忠的家,一套位于上海内环的老旧两居室,家具仍是上世纪的样式,灯泡也快坏了。顺着昏暗的光线,她们看到藏书上千的书房里,“黑压压”的四个书柜,柜顶、地上也堆满了,一捆一捆码得整齐,还按类别写了标签,本人的学术著作也夹杂其中。
现场三人各有分工,西卡负责翻找整理,汪悦负责在电脑上记录,另一人则负责拍照录像,以防产生纠纷。西卡没有放过任何一个角落,很多信件、日记、照片藏在缝隙里或夹在书页中。两天后,她们整理出一份长达54页的遗物清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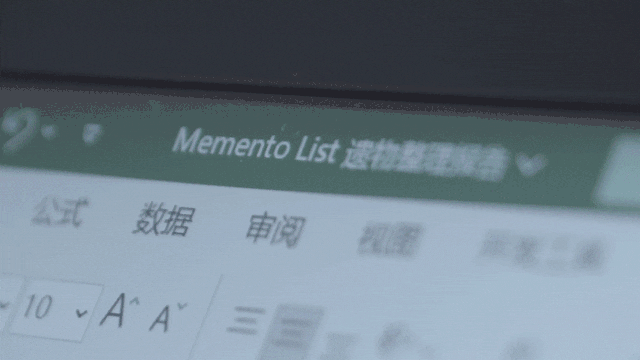
其中,200多封的信件引起了季晨的注意。他发现有个人的来信最频繁,共有63封,来自唐启忠在北京居住的胞弟唐启生。他抽出尤其厚的一封,足有12页,写于1997年,扫一眼看到“我的这个孩子是‘孤独症’(或名‘自闭症’)”,顿时脑袋“嗡”了一下。他知道唐启生已在2011年去世,但不知道他有孩子且患有自闭症,而妻子早已病故。
十年过去,信中那个叫“小明”的孩子如今在哪儿?他还活着吗?季晨迫切想要知道小明的下落,不仅事关遗产继承,更因为他接触过不少来做遗嘱监护的自闭症家长,他们无不担心自己离世后,“长不大的孩子”无人照料难以生活。
他和西卡当晚又回到唐启忠的书房,翻出小明的出生照和一份唐启生病故家中的“情况说明”,得知在其去世后小明被送进了北京郊区一所敬老院。季晨辗转联系上这家敬老院,通过视频通话,他终于看到了33岁的小明——不是想象中“骨瘦如柴”“病恹恹”的凄惨模样,而是“长得高高大大,胖胖的,比较惹人爱” ,不禁悲喜交加。
小明有每月四五千元的残疾人福利补贴,父亲还留下十万余存款和一套60平的房子,不属于“双缺人”。而唐启忠的其他侄辈均无异议,其遗产便由小翠全部继承。至此,季晨的工作已经结束。
但在职责之外,他和西卡都想再做点什么:季晨联系到北京的孤独症公益组织去定期探望小明,这是十年来小明第一次有人探望;公益组织还成立了用于改善小明生活的基金,小翠也加入了月捐,给小明买衣服;西卡和朋友则用小明父亲写的63封信办了一个遗物展,让更多人关注小明们的处境。
“我们挖掘了一个被遗忘十年的人,从我们手里转接到另外一批人去帮助那个人,这个工作太有意义了,所有人参与了都很开心,这种兴奋、喜悦一直存在。”季晨说,不是每个案子都会有这么圆满的结果,之后委托给西卡的几个案子,有的是找不到继承人,有的是几个继承人之间有分歧,“大家各怀心思,互不信任。”
西卡也觉得第一单是一个人性向善的案子,可遇不可求。西卡说,文字资料的整理非常耗时间,收费也会更高,有些案子的直系亲属不想多花钱,就让她全扔了,只留下值钱的东西。但当她和小翠沟通此事时,对方欣然接受,说老先生生前大部分时光都在书房中度过,书是他的珍爱之物,确实应该好好整理。西卡听了很感动,“她真的有站在逝者的角度去考虑”。
遗物真的没有大家想象的冰冷
如果说家居整理遵循的是生活逻辑,遗物整理遵循的则是生命逻辑。“遗物是一个人一生的写照,就像一面镜子一样”,西卡一直觉得,“物品是会说话的” 。在对待遗物上,她和小伙伴更多了一份敬畏和“福尔摩斯”的细心,更注意物品上的一些提示和线索。

整理唐启忠的遗物时,西卡冥冥中感觉老先生在指引她。他把所有书籍分类归置,所有证件放在同一个抽屉,所有掉落的牙齿都保存在一个空药瓶里,并记下每颗牙掉落的时间。他会在重视的物品上做标注,写着“内有照片,请勿卷折”的白纸包着一张工作集体照,妻子的遗像被安放在抽屉的一个纸盒里,盒上写着“亲爱的XX(妻子名字)走好”。他甚至还保留了一个巧克力包装盒,背面写着“XX(同上)遗物”。
汪悦则发现,唐启忠是一个喜欢戴帽子的老克勒。他足足有12顶帽子,照片里的他一直是金丝眼镜、洋帽加一件深色风衣的打扮。他还是一个“有知识、很好学”的学者,出版了自己的书,藏书中有英文、俄文、法文。他有写日记的习惯,早年写在日记本上,随着身体越来越不好,就在日历上写,片言只语记下当天比较重要的事,字也渐渐开始抖。
“遗物整理注定我们接触的物品主人不会跟我们有任何交集”,汪悦说,但通过物品可以跨越时间和空间认识这个人,“很奇妙”。
汪悦参与了几个案子发现,无论什么学历工作、拮据或富有,这些老人都有一个共性,就是不喜欢扔东西,囤着没用的购物袋、鞋拔子、超市宣传页、居委发的通知、各种水电煤账单和医疗单据,像唐启忠家里光脸盆就有十几个。这大概是某种年代的烙印。
另一个共性是老年人的性生活,西卡说“这是一个需要被正视的问题”。她在有的老人家里发现了性用品,而且放的位置非常隐蔽,“他们都会藏一藏” 。团队里的小姑娘看到会很惊讶,有种微妙的怪异感,西卡一开始也不好意思向委托人汇报,意外得到对方坦然的回应后,反倒觉得自己“有点狭隘了”。
“如果从另一个角度去看就很好理解,就是你也会变老的,老年人他也年轻过,也有欲望,他和你没什么不一样,为什么、凭什么他过了60岁,就要变成一个没有性别的人?我觉得这是一种对人性的不尊重。”西卡认为,子女需要去直面父母真实的人生,才能更好地和他们相处。
她原来对母亲有种囿于“妈妈”这个身份的苛刻,觉得“你是我妈,就应该包容我、迁就我”,但做了整理师后,她开始把母亲当作一个更完整的人去理解,“其实她也不过就是一个小女孩长大了而已”。由此带来的改变是,她和母亲的交流变得通畅了许多,“什么都敢聊”。她鼓励母亲去追求未竟的梦想,50多岁的人生“也可以是一个新的开始”。母亲也开始慢慢接纳她的事业,退休后拾掇老房子开书法工作室,还主动让她过来帮忙“断舍离”。

做遗物整理也让西卡变得更加包容,不会轻易评判他人,“每个人都有难言之隐,每个家庭都有一本难念的经。”
去年九月,一位独居上海的外籍商人,因在外地的亲戚联系不上他,拜托一位上海的朋友上门,才被发现死在了自住房里。他唯一的孩子幼时随前妻移民国外,没有联系,对他的情况也不了解,经由律师把重要财产证件保管到银行后,便通过网络找到西卡,远程委托她全权处理父亲的遗物。
这是第一个不经由公证处也不涉及财产继承的个人委托。在季晨看来,能找到公证处的还不算孤独死,“没有找到我那才是最孤独的。孤独在哪里?他的愿想无法得到平安的落地” 。
汪悦回忆,她们去整理时,冰箱里很多食物都过期、腐烂发臭了,还有疫情时政府发的物资。她们要从开不了机的电脑里刻录的数据和所有的中英文纸质文件中,搜寻重要的财产线索,“一张也不能落”。8本满满的名片夹,厚厚的个人简历……光鲜的工作成就,映照出家庭生活的黯淡。
他留存了历年给孩子支付学费、抚养费的汇款账单,甚至有次跟孩子去旅游时的住宿单据都还留着。除此之外,似乎找不到两人之间更多的交流,但思念仍有迹可循。他在一个笔记本记下的理财账户,密码只有四个字的提示:孩子生日。西卡特意截图发邮件给委托人,提醒她重点看一下,但没有收到任何反馈。
汪悦记得,当时西卡总希望委托人把一些有纪念价值的物品留下来,但对方觉得没有太大必要,让她该扔的扔掉,该捐的捐掉,能卖的就卖掉。西卡感到有些失落和遗憾,“可能这就是它们命中的命运吧。”
不过,有时一张废纸也可能会被视若珍宝。在一次男士遗物的整理中,西卡翻到一张便利贴,字写得龙飞凤舞,也不是财产相关的信息,很容易被扔掉,但上面写的一个地名引起了西卡的注意,她突然想到之前听一个家属提过,他们小时候在那个城市一起长大,便拍照发给了那个家属,对方特别惊喜,连用了几个感叹号。原来这是多年前他们兄弟姐妹在各自的家里看同一个节目时写下的经历,还打电话互相分享过。“她说,这是他留给我的一个念想,你能帮我留下来,真是太好了,太感谢你了。”西卡没想到,一个小小的纸片,也能触发一段这么宝贵的回忆,“就会觉得遗物真的没有大家想象的这么冰冷。”

有些逝者贴身用的东西,委托人不想留存,西卡觉得“就这样丢掉于心不忍”,就会向家属申请捐给自己。如今她收集了不少别人的遗物,眼镜、拐杖、票据等,还有一本唐启生写的书,是她当时特地从旧书网上买来收藏的。这些物品可能都会在她日后举办的遗物展上出现,告诉大家“普通人的物品也值得被凝视”。
向死而生
一个人的离世,对其他人意味着什么?尽管经历过几位至亲的离世,这个疑问至今缠在汪悦心头。
最早离开她的,是她的爷爷。高二有一天汪悦放学回家,看到爷爷躺在床上,脸上盖着一沓厚厚的黄纸,她掀起一角看他,“跟睡着了一样。”她不懂这沓黄纸有何意义,只觉得这个行为很随意,“原来一个人死亡是这么简单的一件事” 。她独自躲到厕所哭,明白这意味着永远地失去。
汪悦大学毕业第二年,奶奶独自在家摔了一跤,第一个发现的父亲破门而入时,人已经没了。当时母亲接到父亲的电话,对方一直嚎啕大哭,问什么也不回应,她一开始还以为是弟弟,根本没想到丈夫会哭成这样。听到母亲的描述,汪悦一下想起了爷爷去世时父亲的状态,当时操办后事的父亲一直红着眼,但仍克制着情绪,“他失去父亲时还很隐忍,但失去母亲时他就像个孩子一样。”
去年,汪悦陪西卡去录制一个死亡话题的节目,聊到宠物殡葬,养了两只猫的汪悦当场“哭得人都快没了”,她完全没法想象她的猫有一天会离开她。其实高二经历爷爷去世后,她无数次设想过如果父母离世她该怎么办,本以为早已有所准备,那天才意识到,原来自己对死亡仍存在逃避,“可怕的是你从来没有想过它,它就发生了” 。

汪悦记得北京清华长庚医院疼痛科主任路桂军说过,国内的死亡教育是欠缺的,“我们不知道怎么面对自己的情绪,或者说面对死亡。”路桂军一直深耕安宁疗护、生死教育领域,曾在2021年清明节给自己认认真真办了场葬礼,到了亲人诀别环节,他一个活生生的人躺在冰棺里,感受到妻儿抚摸他的脸的手在颤抖,一下就“受不了了”,立即叫停了葬礼和拍摄。这一幕也深深触动了汪悦。
在汪悦看来,思考死亡最大的作用,不是探寻死亡,而是回看活着的意义。怎样活,才对得起随时面临的死亡?她想在原则之下“随心所欲”地活着,不留遗憾,想做什么就去做,不再等人作陪,开始享受一个人旅游、看电影、吃美食、散步。为此庆幸的是,在2020年那个元旦,她独自去台湾看了五月天的跨年演唱会,圆了一个心愿。
“想做的事要早点去做,因为你不知道意外哪天会来。”西卡说,经历过疫情的人对此感受更为深刻,去年春天,她身边一些朋友、委托人因为一时没有陪伴家人,而没能见到最后一面,“一生就错过了” 。
季晨发现,疫情加重了人们的死亡焦虑,更多年轻人开始考虑生死问题,当他们困在一个空间里出不了门,“他思考什么?就思考人生。”
3月21日发布的《2022中华遗嘱库白皮书》显示,立遗嘱人群越来越年轻化,其中不乏“80后”“90后”,乃至“00后”( 2020年至2022年共有357人)。许多人不再把立遗嘱看成是人生终点要做的事情,而是一次对过往和未来的重新审视。

季晨观察到,相较于年轻人和老年人,中年人更为“回避死亡”,不敢参加葬礼,忌讳探望病人。但这些年他亲历了很多“迷茫的死亡”,也参加过不少葬礼,早已视如平常,“每一次去收拾别人的后事,都是对自己的一个警告,一个提示,一种减少死亡恐惧的安慰剂。”
他至今没写遗嘱,只把财产密码告诉了家人。“可能是觉得还没到时候,每个人都有求生欲,比较自信自己不会死。”其次,他也不是很在意死后怎么葬、物品怎么处置,还跟家人开玩笑说,等他死后火化,晚上悄悄去百年大学里找棵树,刨个坑把骨灰埋了,“回归大地,又融为了这个星球的一部分。”
他对身后事的不在意,更多是觉得,“活在当下最重要。”
“遗物”的生前整理
对多数老人而言,与死亡相关的抉择,总逃不开一些观点的束缚,亦或亲属间的拉锯。
季晨给老人讲意定监护中的医疗事务代理时,有些人听不懂“创伤性治疗”“安宁疗护”,只能用上海话翻译为“一脚去”,意思是一觉睡过去,“蹬腿蹬得爽快点”,减少痛苦;有些人甚至把“安宁疗护”理解为安乐死,“经常跟监护人说,拜托你跟医生讲打一针,让我死掉就行了,我说你不要害人家。”
大部分老人都希望死后尽可能不给监护人带来麻烦,让其顺利继承财产和执行遗嘱。所以即便不强制,他们都会在季晨的建议下做“生前资料的准备”,提前把财产和家庭成员的线索、亲属关系证明、人事档案等资料,记录和保管在一个容易找到的地方。
这种准备属于“生前整理”的一部分。“生前整理”指一个人提前对自己的物品和财产进行整理、安排归宿,应对随时可能发生的意外,以减轻亲属的负担。西卡介绍,在日本,许多人都会做“生前整理”,相关的笔记本随处可买,人们可以按照表格登记物品、资产、医疗、人际关系等方面的内容,包括葬礼的期望。
“立遗嘱还是会给人一点沉重的感觉,但生前整理笔记就像中间的一个过渡,可以是一个尝试的开始”。但抱着这个观点的西卡,也不好主动问别人要不要做生前整理——“这不咒人家嘛?太冒犯了。”她觉得中国人的生死观,像一张巨大的网罩在大家头上,很难突破。她原来有个家居整理的老客户,得知她做遗物整理后,就明确表示介意,不愿再来了。
生前整理比遗物整理更难落地。截至目前,约有十个人找西卡咨询过生前整理,最终一个也没成。在西卡看来,遗物整理会有一些刚需,如租房、卖房。但做生前整理首先要有一个强大的内心,“因为你整理的是自己的一辈子,不是别人的”。其次要有足够的财力和时间,可能还涉及财产公证等法律问题,一些人一听这些,“哇,好麻烦,那我就先拖一拖吧。”
这些老人的出发点是想梳理自己的人生,把一些财产和物品送给子女,但这动作一出来,往往招来不好的联想:“你现在就给我啥意思?是不是有事瞒着我?”或是子女不能理解,觉得不吉利,老人也会在意周围人的眼光;还有的老人,子女不止一个,想法也不一样,万一中间再起冲突,想想还是算了,“别惹事了”。“他们背负了太多的责任感”,西卡说。
这种观念带来的压力,可能也会压在子女头上。西卡曾碰到一个95后小伙,他父亲已经被下三次病危通知了,西卡劝他,都到这个节骨眼了,别把精力都花在痛苦的医疗上,好好跟爸爸聊聊天,了解一下他的财产债务情况。“但他就觉得不行,我要是开口问了,是不是就咒我爸爸死了?”
唯一的“例外”,是一个100多岁的老太太,“太开明了,说自己活够了。”老太太一生从事服装生意,衣着精致时尚,人也迸发着生命力,讲起自己的那些漂亮衣服,脸上都神采奕奕。但她的身体已无法承担长时间的生前整理工作,两人约定,未来一天有缘分,西卡再来帮她做遗物整理,她也很乐意展出自己珍藏的服饰。

尽管成单率低,西卡对行业未来依然保持乐观。不久前,国内一家知名的生前契约公司找到西卡谈合作,希望做一个关于生前整理的长期项目。她觉得,至少自己在做“一个往前走的事儿”。她还打算研究一下数字遗产的整理,其中涉及的法律问题更为复杂,比如逝者的社交账号能否被继承?家人有没有权限查看?
上述白皮书显示,自2017年起,越来越多中青年人群立遗嘱时会考虑“虚拟财产”,截至2022年年底,中华遗嘱库共计收到458份遗嘱内容涉及“虚拟财产”,包括QQ、微信、支付宝、虚拟货币、网络游戏账号等。
由于“现在很多资产、权益都已经网络化、数字化”,汪悦也考虑过,如果自己在父母之前去世,留给他们的东西如果不提前整理,他们可能无从下手。她决定先从整理照片开始,结果把自己吓一跳,电脑和两部手机里共有一万五千多张照片,她删了一晚上,还有一万出头,后面删到来气了,索性备份后一下全删了。
西卡设想,如果一个人生前委托别人整理数字资产,也未尝不可。但这或许是一个更具挑战的漫长探索。
文中季晨、唐启忠、唐启生为化名,部分案例故事来自公开报道。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凤凰网 (ID:ifeng-news),作者:张小莲,编辑:马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