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扫码打开虎嗅APP

我们该如何看待国际经济秩序的变化及对未来的影响?文章并没有也不可能给出明确答案,但作者试图通过对国际经济秩序从由来到发展的分析,反思其本质、特征及其影响因素,并呼吁应明了大变动阶段的到来。虽然如何理解变局充满了挑战,但我们更应增进对相关的一切因素的了解,同时构想如何重建较为合理的国际秩序。
本文首发于《读书》2024年1期新刊,授权虎嗅转载,更多文章,可订阅购买《读书》杂志或关注微信公众号:读书杂志 (ID:dushu_magazine),作者:瞿宛文,原文标题:《〈读书〉新刊 | 瞿宛文:国际经济秩序的变化》,头图来自:视觉中国(图为2008年金融危机时的美国)
中国的经济前景是众所瞩目的议题。中国是否能如二〇〇八年金融危机之后那般,带领全球经济增长?中国经济的崛起是否会告一段落?这些都是事关重大的问题。如今在疫情缓解之后,中国经济恢复的速度并不如预期,从而引发国内外众多学者的讨论,探究到底是什么因素在阻碍中国经济的复苏。
一般而言,讨论较着重中短期的视野。然而,本文在这里要讨论一个较为长期的问题,就是国际经济秩序的变化带来的不确定性,而这不确定性可能对中国及世界的经济前景产生难以评估的影响。
一方面,一些带来短期波动的因素,大家都较为熟悉,如新冠疫情对全球供应链带来的供给上的影响、其所引发的通货膨胀,以及中国与各国本身内部周期调整的问题等。对于这些中短期波动及政策周期调整的因素,相关的研究比较多,其中涉及的逻辑也较为清晰。
基于这些中短期因素的考虑,对各个地区的预期复苏速度虽然会有差异,且目前来说速度较预期缓慢,但是基本上仍会预期缓慢的复苏,只是速度与程度的问题。当然还有关于短期刺激性政策处方的争议,这是重要且有立即作用的政策议题。
但另一方面,有一个新的因素出现,它不仅已经在发生中短期的影响,也应会有较大而长久的影响,那就是国际经济秩序正在发生显著的变化。不过,大家对于如何看待秩序变化比较缺乏共识,且是否以及何时会出现新的秩序更是充满不确定性。而这不确定性必然会持续地发生作用,会持续地影响各方的经济行为,这部分的作用也较难以评估。虽然说经济秩序的变化是一个较为广泛的议题,但其确实会影响经济前景,因此且容我在此试着讨论如何理解国际经济秩序变化及其影响。
国际经济秩序是有“作者”的
近年来中国经济迅速崛起,中美关系急遽转向对立,这常被解释为地缘政治的变化,是新的国际博弈赛局,虽然会有巨大的影响,但亦被视为仅是此后国际权力分配上的博弈与调整。然而,本文在此所指称的国际经济秩序变化,并不仅止于此,而是国际经济体制的变动,涉及整个体制领导权的变动,涉及改变全球经济体制秩序与运作的规则。
注:Hegemony,常被翻译为霸权,涉及中文语境中既有的王道与霸道的区分。即使在英文语境中,TheH-Word的涵义也是众说纷纭,对于其是领导权抑或强力支配权(domination)或两者不同比例的组合,也有不同的说法(参见佩里·安德森:《原霸:霸权的演变》,李岩译,当代世界出版社二〇二〇年版)。
本文无法对此多做讨论,仅先以领导权称之,但假设其包括领导权与强力支配权。现今关于霸权的讨论多源自葛兰西(Antonio Gramsci)所提出的霸权理论,其原来主要针对国内以阶级为基础的权力关系,而阿瑞基(Giovanni Arrighi)将其扩大结合运用到国际之间基于政治经济的权力关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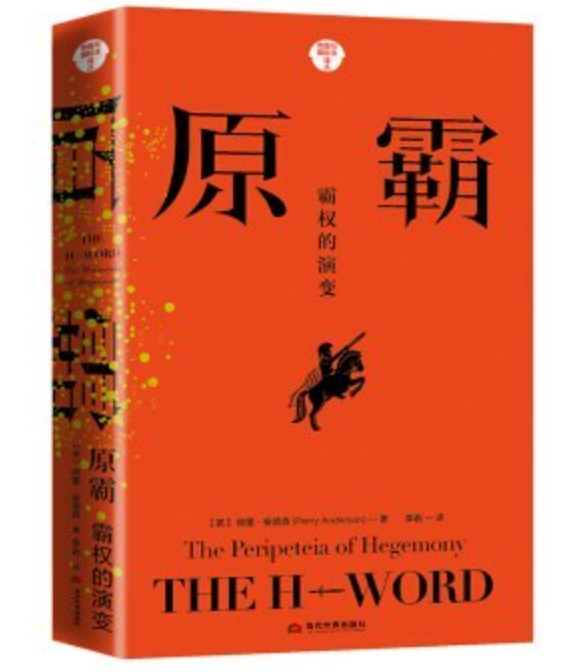
佩里·安德森作《原霸:霸权的演变》(来源:douban.com)
在体制秩序较为稳定的时候,体制秩序会被当作理所当然的背景因素,即如经济学者通常所假设的“其他因素不变”一般。然后,在假设架构不变的前提下,大家讨论或推导出各种被认为是由纯经济或技术因素所驱动的市场变化趋势,如运输革命、全球化、区域化、金融化、AI化等。政治干预常被经济学者认为是违反经济理性,并且难以理论化,多被假设属于不变的其他因素类别。
然而,这种说法假设既有国际经济秩序为自然天成,主要是由经济与技术因素驱动而成,而如此说法对于理解当今世界巨大变局并没有太大帮助。因为在较高的整体体制层次,经济与技术因素无法告诉我们中美博弈会如何发展,国际经济秩序未来会如何演变。
为了理解变局,我们必须提高分析层次,将其他因素都视为可变动的。其实只要回顾历史,就可以看到目前被认为理所当然的国际秩序,是“二战”之后才建立的,不同于“二战”之前的格局。两大强权国家美国与苏联,共同建立的“二战”后初期的秩序,只是美苏冷战已经于三十多年前结束,至今格局更凸显了美国超强的领导者角色。
简言之,“二战”后的新秩序是有“作者”的,并非自然天成。美国当初在设计战后秩序时,有其承续的历史性因素,但也涉及罗斯福及杜鲁门政府所设想的国际秩序蓝图。对于理解变局,除了理解当初的构想蓝图之外,更涉及其后数十年来美国及国际经济秩序的持续变化。因此,为了凸显世界大局的轮廓与变化,本文将简要地比较英国与美国领导下国际秩序的异同,以及两轮领导权周期的变化。
英国与美国领导秩序的异同
英国在十七至十八世纪陆续打败荷兰与法国后,借由一八一五年的维也纳会议,在欧洲建立了由其领导的保守的国际秩序(君主制、殖民地、奴隶制)。因为英国在此时已经累积了诸多方面的优势,包括最先发起了工业革命,伦敦成为世界的自由贸易港及金融中心,优势海军带来在全球范围建立殖民地并对其予取予求的能力,尤其是对资源丰富的印度。
因此,英国在此时刻改变了其以往的重商主义政策,对外单边实行自由贸易政策,即英国输出工业品,而由殖民地供给农工原料,但容忍欧洲其他国家采取重商主义政策追赶英国,同时以权力均衡的方式维持十九世纪欧洲内部的和平(虽说殖民地战争不断)。
当时欧美强国相对于殖民地的力量悬殊,不过英国最终仍难以权力均衡来维持欧洲内部秩序。因此,两次世界大战结束了英国领导的时代,主要是新兴的德国起来挑战其领导权,德国虽失败但也耗尽了英国的国力。
“二战”后由新领导者美国来主导世界秩序的重建。基于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经济恐慌的经验和教训,罗斯福新政的蓝图设计中,世界性机构——主要包括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及联合国——将在美国领导下治理世界。
同时,罗斯福对第三世界也采取不同于英国的政策,支持落后地区的去殖民化与经济发展,但并未如对西欧那般提供大幅经济援助。相比英国的规模,美国幅员广大,英国可以实行自由贸易,而美国多以双边贸易协议为主,治理与各国的关系。不过,美国特殊的优势在于其纵向整合、具竞争优势的跨国企业,可依赖投资来跨越贸易边界(杰奥瓦尼·阿瑞基:《漫长的二十世纪》,姚乃强、严维明、韩振荣译,江苏人民出版社二〇一一年版)。
简言之,英国与美国领导下的国际秩序安排,相同处是有清楚的最高领导国主导秩序。不过,在结构上,英国的自我定位是全球商业与金融中心,单边自由贸易配合着对殖民地的控制,以权力均衡维持强国间的秩序。而美国在结构上是自我中心的最大国,治理国际经济秩序多依赖双边协议与自身的跨国企业。
不同于英国的殖民政策,美国对第三世界前殖民地允诺了政治主权与经济发展,然而至今,多数前殖民地虽有形式上的独立,但恐未能拥有完全的政治主权,在经济上多数则仍延续着殖民地经济的模式,以输出原物料为主。
不过,即使如此,即使美国的军事力量几乎独霸全球,美国对前殖民地的控制程度,也已远不及英国当时所达到的程度。同时,也已经有少数落后地区成功发展了经济,缩短了与先进国家的距离,甚至成为美国力量的挑战者。
动态的资本主义周期
在历史现实上,英国主导地位的兴衰可说甚为明晰。然而如今,虽说美国实力较战后初期明显衰弱,但如何借鉴以往英国失去领导权的经验,来评判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是否已到了被更替的时刻?在此先讨论其中所涉及的资本主义的周期循环。
近数十年来的金融扩张趋势甚为明显,而金融化必然带来两极分化,难以真正维持荣景并解决经济危机,这同时会带来合法性危机以及社会动乱,亟待新力量来领导变革、建立新秩序,但也存在新秩序难以建立而世界陷入系统性混乱的可能。
金融化会带来两极分化的逻辑甚为简单清晰。制造业会带来数目众多的工作机会,例如在“二战”后初期,美国制造业兴盛且工会仍较为有力,故能支持工人进入中产阶级,壮大中产阶级的行列且使得分配较为平均。而金融业则创造数量甚少但极为高薪的工作机会,不能培育中产阶级。
而今,美国二〇二〇年近二十一万亿美元的GDP总值中,制造业创造价值的占比为11%,金融业的占比则达到22%。而所得分配高度不均衡,以至于二〇〇八年金融危机之时,出现了“99%vs.1%”的反华尔街运动的口号。
然而,金融化并不是新的现象,即如文艺复兴时代的佛罗伦萨一样,美第奇家族便是在金融化之后开始支持文艺活动的。法国年鉴学派大师布罗代尔在他的三卷本《十五至十八世纪物质文明与资本主义》中,即指陈从十五世纪开始,北意大利城邦就最先发展出了资本主义,而之后“生产/贸易扩张→金融化”的资本主义周期,就一再地重复出现。
他指出,在资本主义周期中,反复出现的金融扩张是一种信号,预示将由旧的积累体制进入新的体制。资本主义周期已历经数次循环,领导者经历了北意城邦—荷兰—英国—美国的更替。美国领导的体系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开始接手,“二战”后全面主导世界。美国体系在二十世纪五十至六十年代进入生产扩张期,却在七十年代就进入危机与金融扩张阶段。
在每一个体系积累周期中,在生产与贸易扩张阶段,若利润率高于平均就会吸引资本不断进入;随着竞争日益激烈,利润率会下降,当降至无利可图之际,就会有资本退出生产贸易领域,回复到流动资本的状态,转而进行金融扩张。当整体如此发展,就是这一体系积累周期进入了成熟期,即布罗代尔称之为体系“秋天”的阶段。时至二十一世纪的今日,美国体系进入金融化阶段已毋庸置疑。如上所述,近年美国GDP中金融业的占比已达22%。
布罗代尔认为,市场经济在历史上是普遍存在的,但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则是一种特殊的、近代才出现的体系;后者虽以市场经济为基础,却有着特殊的组织安排——资本与国家权力相结合,资本与国家政权各有各的目的,它们之间是一种既有矛盾又互相依赖的结合。布罗代尔认为资本主义的兴起与扩张依赖国家权力的支持,绝非源于市场经济的自然生长。
美国危机的来临于一九六八至一九七三年间显现:军事上越战难以得胜,金融上难以维持布雷顿森林体系,而意识形态上美国在国内外渐失去合法性。一九七三年美国政府在所有战线上撤退,开始忽视“世界政府”的职能。当时欧美薪资上涨速度加快,又出现石油危机,资本过剩而劳动力与原料供给跟不上。至此,凯恩斯式刺激需求的做法已失效,价格上涨。
美国将美元与黄金脱钩之后,世界货币有失控趋势,货币混乱不断增加。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期,美国政府决定控制货币,重建美元地位,政府与美联储联手实施紧缩政策。内外的危机治理使得美国政府此时放弃了罗斯福式新政,寻求与金融资本合作,以便在全球权力竞争中重获优势。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后,金融化确实带来了暂时的成果。购买力重归美国,限制性货币政策与高利率给第三世界带来毁灭性后果,南方的商品价格下降,拉美债务直线上升。这转变也使得苏东集团必须与第三世界争夺流动资本,并最终在压力下崩溃。
西方的美好时期再度来临,只是危机并未解决,稍后即以更棘手的形式再度出现,即如二〇〇八年的全球金融危机所证实。由盈利性危机导致的金融扩张带来贫富分化进一步加剧,更引发了合法性危机,造成西方国家政治上更剧烈的动荡。
一些案例或能显示金融化的实质作用。近年来,美国政府对美国正失去半导体产业主导权甚为焦虑。美国英特尔(Intel)公司是创立半导体产业的主要企业,从个人计算机兴起后,英特尔就以垄断个人计算机的CPU为主要获利方式。
在二〇〇六年左右,苹果公司正准备推出其革命性的产品——智能型手机iPhone,而当时苹果CEO乔布斯向英特尔提议,由其来为iPhone提供芯片,但英特尔认为利润太低而拒绝了这个商机,而日后iPhone的销售额很快超过了个人计算机。
英特尔早期开创者几乎都具有理工背景,然而当时(二〇〇五至二〇一三年)英特尔的CEO不是工程师出身,而是MBA出身,他主要担心新产品会拉低利润率,因而拒绝了这一黄金机会,也限制了该公司参与下一波技术革命的机会(Miller, Chris, Chip War: The Fight for the World’s Most Critical Technology , New York: Scribner, 2022, 195-196)。
近三四十年来,美国大企业领导层日益看重公司短期财务报表的绩效及其对公司股票的影响,未必关注长期科技竞争力,这已是普遍现象,也是美国产业实质竞争力下降的原因之一。
以上所言有关美国体系自身的发展动态周期,而百多年前,英国体系也呈现相似的发展趋势。英国在十九世纪末期经济大萧条之后进入体系的“秋天”,即进入金融化阶段。不过,英国金融中心的重要性下降速度缓慢,即使到了二十世纪四十年代,英国海外贷款占比仍有三四成,全球仍有过半的贸易是以英镑进行。直至“二战”后,美国才完全确立领导地位。
社会基础
领导权的转移中,社会冲突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
除了上述领导国自身发展周期的动态之外,领导权移转还涉及国家间以及资本间的竞争,还有社会冲突及各个因素相互间的影响。如英国失去领导地位,基本由于自身经济力的相对下降、替代者美国的兴起,以及德国的军事挑战带来的两次大战。
然而,国力衰弱下降所伴随的社会变动虽有深远影响,但是其对统治秩序的影响却甚为复杂,不易界定(参见乔万尼·阿瑞吉、贝弗里·西尔弗等:《现代世界体系的混沌与治理》,王宇洁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二〇〇三年版)。例如,十九世纪末英国与欧洲劳工力量兴起,社会冲突升级对统治者带来挑战,不过当“一战”兴起时,工人却热烈地投入战争而转移了冲突压力。
从二十世纪初期开始,尤其在“一战”后,落后地区陆续发生革命,开启了落后地区社会革命的长期浪潮,这也使得旧的殖民帝国在“二战”后难以重建其殖民统治。在此背景下,美国在“二战”后初期,成功地以去殖民化及经济发展的允诺,在落后国家间建立了领导权,这与其数十年后的情况大为不同。
卡尔·波兰尼(Karl Polanyi)在其名著《大转型》(The Great Transformation,1944)中阐述英国在十九世纪施行自由放任带来的恶果,而他认为利伯维尔场会带来双向运动(double movement),即社会结合起来设法保护自身,社会的反弹会约束市场力量,结束自由放任时代。只是他忽视了资本主义的周期性!在“二战”之前,欧美确实开始推行如美国的新政等限制市场力量的政策。
但是,到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下一个领导国—美国—在走向金融化的同时,意识形态也发生转向,利伯维尔场论再次以新自由主义(Neoliberalism)的面貌成为主流〔Silver, B., and G. Arrighi,“Polanyi’s‘double movement’: The Belle Epoques of British and US hegemony compared.”Politics and Society , June 2003, 31(2): 325-35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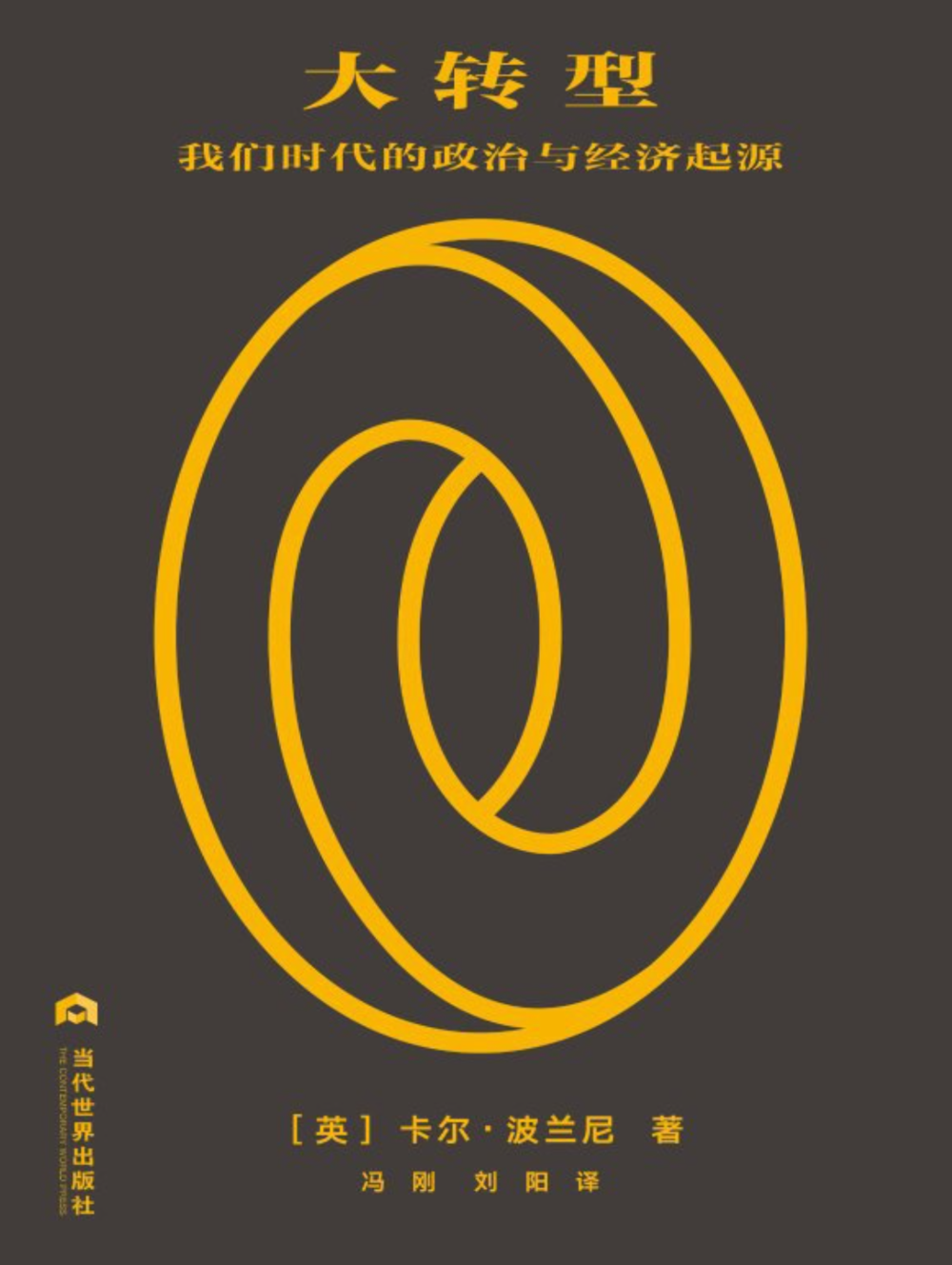
卡尔·波兰尼著《大转型》(来源:douban.com)
简言之,资本主义体系会有周期,每个周期由领导国主导建立新秩序,体系晚期会进入金融化阶段,而金融化会带来社会冲突的升高,若政治、经济与社会秩序上的混乱升高,亟须新的领导者出现领导建立新秩序。近年来欧美社会也清楚地显示出如此进入体系晚期的发展趋势。
不过根据以往经验,社会冲突与统治方式以及领导权的兴衰,其间关系错综复杂,并不易界定其影响作用。如今,较为确定的是传统工运的衰退,民粹政治的兴起,同时社会结构与以往高度不同,过去经验的适用性不易评估。
小结
国际体系秩序已进入大变动阶段,很难再视其为不变的背景因素。如何理解国际经济秩序的变局?如何进一步掌握领导国美国的政治动向、美国社会冲突的演变、美国对其全球领导权下降的因应对策,都是困难度极高的挑战,却甚为必要。
若这些动态变化难以掌握,整个体制未来的走向必然充满不确定性。较为确定的是,我们应该意识到国际秩序的局势正进入大变动的阶段,美国领导权正在衰弱中,但走向并不确定。我们应增进对相关一切因素的了解,同时构想如何重建较为合理的国际秩序。
本文首发于《读书》2024年1期新刊,授权虎嗅转载,更多文章,可订阅购买《读书》杂志或关注微信公众号:读书杂志 (ID:dushu_magazine),作者:瞿宛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