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扫码打开虎嗅APP

来源:一点儿乌干菜(ID:NarratorZhang)
作者:章程
一、柔软的乌托邦
是枝裕和的电影很轻柔。在十多岁的时候,我不会喜欢这样的电影,因为它絮絮叨叨,温温吞吞,正是我在经历着的日常。彼时的我认定,若电影不超越平淡,那就不足以对这虚度了的寡淡生活浪漫化地抗议。
可是,在而今二十五岁的年纪,我却越来越喜欢这样的电影,一如我开始喜欢清少纳言的清冷明净。
《奇迹》里航一的爷爷重新做起了轻羹——用山药,砂糖和米粉制成的简单甜品,似甜非甜。影片末尾航一在和弟弟龙之介会面的时候,把带来的轻羹分给弟弟,弟弟说味道淡淡的,航一自语道:“起先我也这么觉得,后来越嚼越香。”
是枝裕和的电影如轻羹,慢慢能让人嚼出甜滋滋的味道,稳妥又怅惘。
无比芜杂的心绪,在是枝裕和不紧不慢的镜头下,变得悠然顺畅又清朗通透,如这几日台风过境后凉如水的夜。有时觉得,生活不就是这样,无端的吵吵嚷嚷,欢欢喜喜,一个人十几岁时弃如敝屣的东西,也许在二十几岁的生命里金灿灿地发光。

电影《小偷家族》
今年五月份,是枝裕和在戛纳也发了光。凭着《小偷家族》这部电影,他成了继黑泽明、衣笠贞之助和今村昌平之后,第四位获此殊荣的日本导演。2017年《第三度嫌疑人》上映后,有人就以“很不是枝裕和”来评价这部电影。可见“是枝裕和”几乎成为了某种姿态的象征:以个体叙事对抗宏大叙事,以对生活妥帖入微的观察取代戏剧化的跌宕冲突。
一个导演,在二十几年从影的生涯里,能够创造出某种广为人知的类型语汇,已然是莫大的幸运。要是以新浪潮时期风靡的“作者论”而言,是枝裕和是典型的“作者型”导演。
八月三日《小偷家族》在国内上映,我立马就去看了。电影结束后,如鲠在喉,走出嘉里中心不远,华灯初上,食肆林立的街道熙熙攘攘,小贩们哼歌忙碌。好电影就是这样,看完之后你会重新打量这个世界,留意被惯常忽略的世界。这人世间素淡的市井气,让人从电影结尾那无以名状的怅然若失中短暂抽离开。
是枝裕和在《小偷家族》中选择刺探人性的灰色地带,无关好坏,善恶莫辨。和《无人知晓》一样,社会边缘人是文明社会的一根刺,让你在毫无觉察时疼痛。

电影《小偷家族》
可是,是枝裕和并不仅仅满足于展现这根不合时宜的刺,以满足观众对于贫穷的廉价怜悯。他的视野够深广,能够捕捉到产生这种个体的社会结构——尽管有近在咫尺的福利制度,可有人宁愿选择游离在这体制之外。这种观察的视角大概得益于他早年在TV MAN UNION拍摄纪录片的经历,他对福利社会的反思在1991年拍《然而……福利消失的时代》时就已经显露了。
是枝裕和并没有以一种他者的眼光来观察在体制之外的个体,贫穷不一定滋生良善,它也有恶、有欺骗、有盗窃、有丑陋。可是人性暧昧模糊,不能被盖棺定论,不能被非黑即白地判断。我相信《小偷家族》里的他们有着比血缘更深的羁绊,这种羁绊是信任与依赖。

电影《小偷家族》
安藤樱饰演的信代把优里红色的外衣以一种仪式般的方式烧毁了,同时消弭了的也是优里对原生家庭的恐惧。她本不相信在那种家庭之下成长起来的优里心里存着爱和善良,因为她也从那样的家庭走出。她紧紧地抱住优里,那一刻她或许是想保护优里内心尚未崩坏的角落吧。
祥太和中川雅也饰演的治,在昏黄的路灯下打闹,宛如父子。即便躲在壁橱里用手电筒凝视自己收集的小物件的时候,祥太依然是孤独又幸福的,这一幕像极了《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的主角。
亚纪与奶奶挤在一个被窝,奶奶能够凭着亚纪的脚冷判断她有不开心的事。信代在被工厂辞退后,和治在家吃饭,暴雨忽至,欲望变得明澈不再掩饰。奶奶虽然知道这一家庭主要的经济来源是她的养老金,但也甘愿和他们一起在抱团中取暖度日,一起在屋檐下看烟火璀璨明亮。在一家子去海边时,奶奶瘫坐在沙滩上,她知道自己时日无多,望着在海潮的涨退中跳跃打闹的五个人的背影,轻声地说了句:“谢谢你们。”

电影《小偷家族》
我想,至少在这些瞬间里,这个家对他们而言,是带着梦幻色彩的乌托邦吧,它庇护了这些被伤害、被冷落、被抛弃的孤独者们。
我喜欢是枝裕和,大抵也是因为他一直在构筑一种日常的乌托邦,每个逃离入内的人,都得到片刻的安稳甚至救赎。《海街日记》中四个女孩在老屋中共同生活,《奇迹》中鹿儿岛与福冈的孩子们盘算着自己的相遇计划,《比海更深》中失败的父亲和儿子在台风来临的雨夜,躲避在章鱼滑梯里。是枝裕和的影像,并不总是在描绘生活中无法承受之重,它们有时无限温情和柔软,同时也像镜子,反照着我们,我们从中看到悄然流逝的无法企及的自身经验。影像是虚幻的乌托邦。

电影《海街日记》
我们在美丽的乌托邦里,喝着青梅酒,吃五谷杂粮,放肆地大笑的那些时刻,我们知道,它是安稳的,像是我们在柔软生活里结的茧。
但乌托邦早晚会在现实里破碎。《小偷家族》中祥太最后觉醒,毅然抛弃了这虚伪的假象,这是他必须做出的取舍。我们总要在真实的世界中习得爱的能力,在认清现实后依然选择爱它,有时候乌托邦的破碎也许未尝不是好事。但对于优里而言,这一切未免太过残忍,影片结局,她在当初被带走的那个阳台,捡着弹子球,呢喃自语,茕茕独立,无奈又心酸。
二、灰色的是枝裕和
是枝裕和在九岁前,家里住的是两栋有点倾斜的老旧长屋,只有一个六叠大的房间和一个三叠大的房间。在这局促的空间里,挤下了是枝家的六口人。他对于童年的记忆最深的是台风,每年到台风季节,家里就要用绳索固定屋顶,以防被台风掀掉,还得用白铁皮把窗封起来。屋里到处都是接漏雨的洗脸盆,天花板嘎吱作响。
后来他们换到了三室一厅的福利房,是枝裕和在那里一直住到二十八岁。而父亲母亲最终的住处也是在这里。是枝裕和在后来的电影中注入了很多早年的经验,比如《比海更深》中就加入了母亲和儿子回忆小时候台风的那幕。

电影《比海更深》
是枝裕和从小喜欢看电视,每天要在电视连续剧播出前赶回家。他迷恋过《我们的旅程》《敬爱的母亲大人》等电视剧史上的名作。他说相比于小津安二郎和成濑巳喜男这些影史上有着煌煌大名的大导演,他心中名列第一的还是向田邦子。他在读了山田太一和向田邦子执笔的《仓本聪精选典藏系列》后,梦想由小说家变成了编剧。
我们无法忽略,在是枝裕和成为而今是枝裕和前,那个在电视台拍摄纪录片时期的他。这段工作的经历,让他以一种异于传统导演的方式审视周遭的世界。虽然直到八十年代他才加入TV MAN UNION制作公司,电视充满果敢和实验性的时代已经结束。但他依然从这电视的“血统”中受益。
是枝裕和把电视比作爵士乐。爵士乐能随着感受一边作曲一边即兴演奏。电视对是枝裕和而言也是这样,大家以各自存在的方式参与即兴演出,不是“过去式”,永远是“现在式”。

和伊那小学小朋友合影
电视的这种特质影响了是枝裕和的纪录片创作。在拍摄《另一种教育,伊那小学春班的记录》,他和孩子们玩成一片,和大家一起吃营养午餐。孩子们甚至觉得是枝导演并不是来拍摄的。在这段两年多的相处时光里,孩子们也让他记录下无比真诚的疑虑、哀伤和喜悦。这段经历让他意识到:“所谓的取角、构图,其实就是如何凝视自己的拍摄对象。”

电影《海街日记》
他把这些经验带到了自己的电影创作中。
在拍摄《距离》的时候,夏川结衣和伊势谷友介在河边的那段对话没有事先准备台词,即兴说出。《海街日记》中,他敏锐地捕捉到广濑铃身上不爱群集的独立特质,让她不用剧本,随时依据现场的台词来思索调整。《奇迹》里,他觉得航一沉默的表情在影像上更有魅力,所以说话就交给弟弟。而航一主要负责凝视、想心事等沉默的戏。是枝裕和很好地平衡了导演与演员之间微妙的自由度。
TV MAN UNION时期带给他的另外一种经验,是对社会事件要有具备同理心的冷静的判断,而不是以偏颇的是非观作论断。

电影《无人知晓》
《无人知晓》的剧本在TV MAN UNION时就已经完成了,是枝裕和根据一九八八年发生在东京的真实事件写成。当外界所有人都在指责母亲的不负责,在怜悯这四个孩子的悲惨生活时,是枝裕和却并不这么认为。他觉得被抛弃的六个月里,他们看到的风景应该并非只是灰色的“地狱”。他自忖道:
“他们的生活是否存在某种有异于物质性富足的‘富足’呢?其中是否包含了兄妹之间共有的悲喜情感,和属于他们的成长与希望呢?如果答案是肯定的,公寓外面的人就不应该说地狱什么的。”
从《无人知晓》的剧本开始,到《然而……福利消失的时代》《我想成为日本人……》等纪录片,再到后来的电影,是枝裕和从不审判个人,他不觉得导演是上帝或者法官。
在《无人知晓》中,母亲并没有被任何道德批判。《距离》中,他开始站在被千夫所指的罪人的立场上,思索在没有足够保障的社会里,加害者也可能成为受害者。《小偷家族》也是,安藤樱饰演的信代最后的那一段带泪的反问,观众的同理心已经完全在她这边了。

电影《小偷家族》
是枝裕和有一段话我很喜欢,他说:“设计一个坏人故事,世界也许就变得黑白分明,但我认为不这样做,反而会让观众将这个问题带回自己的日常生活中反复思索。那样的想法基本上至今仍未改变,我总是期盼看电影的人回到日常生活时,对日常生活的看法能有所改变,能成为他们改掉用批判性眼光看待日常生活的契机。”
没有绝对的黑白分明,灰色终究是这个世界的颜色。
三、何为“日常”
最早思考“日常”为何,并不是因为电影,而是因为建筑。初学建筑时,我看了《建筑的诗学》。建筑理论界的对话,常让我有种过度阐释之感,总在语境的差异中跳跃、踯躅、迂回。
“日常”这个命题在书中坂本一成的话语里逐渐浮现出来,但他思考的视角还是西方式的,因为从列斐伏尔提出对日常生活的批判为始,至本雅明和罗兰·巴特,在理论界,“日常”已被视为二十世纪的一种视野转向,这是一个被学术裹挟了的语汇。
可是我总觉得没那么复杂。

筱原一男的“白之家”
从坂本一成,我循到了他的老师筱原一男。筱原一男显然更吸引我。他有一个叫“白之家”的作品,空间最具紧张感和戏剧性的是正中心立了一根柱子。二十年后,“白之家”被迫拆掉,但因为主人实在太喜欢,就择地重新盖了一座。
筱原去参观新的这个“白之家”时,总觉得不对味,因为一切的物事都太崭新,少了时间感。当他正寻思的时候,女主人走过柱子,微微往正中的那根柱子上倚了一下。那一瞬筱原才恍然,原来“白之家”没有变,它还是那个存在了几十年的老房子。空间中的身体性是不会变的,只有长期使用的人才能感知到。
一个缺乏体贴与敏感的建筑师是不会有筱原这样的观察与感动的。是枝裕和作为导演却有这种功力。
《比海更深》中有一幕,母亲在姐姐背后开冰箱门的时候,姐姐自觉地身体往前倾,避开了母亲开门的动作。她太熟稔母亲的这个动作,也深知家的空间的局促,以至于根本不需要回头即可判断,抑或之前的经验让她自然具备了这个动作习惯。

电影《比海更深》
学建筑时从没琢磨透过的“日常”,在是枝裕和的电影里,我理解了。电影中这种被空间塑造了的不自觉就是“日常”,和筱原一男“白之家”中女主人的动作,有着微妙的一致。要是没有彼此在共同的空间里度过足够多的岁月,是无法拥有这近乎本能的习惯的。
在拍摄《步履不停》时,因为拍摄租借的是医生的家,出现厨房端茶到客厅的距离无法说完该台词,只好当场修改。而《比海更深》则不,是枝裕和想着自己从小生活的房间格局写了剧本,当演员实际走在同样大小的房间里,不管是台词长度还是动作都不会出现误差。例如阳台回到三坪大的和室,母亲抱着棉被说话的台词就刚好是那些字数。
他感叹道:“这一次几乎不用修改的奇妙经验今后也不会再有吧。”每个创作者成年后的作品,无非都是对童年时期的图像的某种修正。

电影《比海更深》
生活就是枝裕和的“日常”。
“日常”不需要那么玄妙的理论。它可以大到一个时空的风土,可以具体到空间与人长期建立着的某种关系,也可以细微到生活中琐碎平凡的不经意瞬间,比如一场台风,一顿早餐,一只螃蟹。
除了必须以哲学的思辨来厘清社会问题外,是枝裕和在具体生活中,从不进行艰涩的思考。平实质朴的生活不需要这些。
四、未知生,焉知死
在是枝裕和的电影中总有缺席离世的长辈。
法国观众问他为什么总是描绘死者时,他答道:“日本与法国不同,在日本没有绝对的神,取而代之的大概就是死者吧。有句话叫‘无颜面对列祖列宗’,要活得一生无愧,就需要‘死者’的存在。”是枝裕和并不迷恋死亡。他关心的是那些遗留下来的人,如何好好地活下去。
或许也可以说,是枝裕和关注的是与死相伴的生的时刻,以及在这些时刻里,人生的某些悲喜、坚定与犹疑。

电影《海街日记》
所以在是枝裕和的电影中,他不会过度渲染死亡带给人的悲伤,即便是《无人知晓》中,长子把妹妹的尸体埋葬后,他依然在灰暗之后,用欢欣明媚的画面收尾。《海街日记》的最后,是“海猫食堂”老板娘二宫女士的葬礼,但是枝裕和随即将镜头转向海边,四个女孩互相嫌弃着想象自己七八十岁后的样子,大海辽远明净,似乎能治愈生命中一切的缺憾。
《步履不停》也是如此,父母过世后,横山家的次子已为人父,虽然有“人生总是来不及”之慨,可整个扫墓的基调没有太过悲恸。回去途中,次子对着自己的女儿说起以前母亲和他说过的那个蝴蝶的故事:
“冬天没有冻死的纹白蝶,隔年会变成黄蝴蝶飞回来。春秋流转,时间只是转了一圈后停在稍微不同的地方。”

电影《步履不停》
东方式的日常,往往就是这样隐而不发,比海更深的情愫都在心里藏着掖着,父母望着子女背影渐行渐远,大家在各自的生活里慢悠悠又从不停歇地向前。恍惚之间,物走星移。
是枝裕和的电影如此,小津安二郎的电影也是,侯孝贤的电影也是,森淳一的电影也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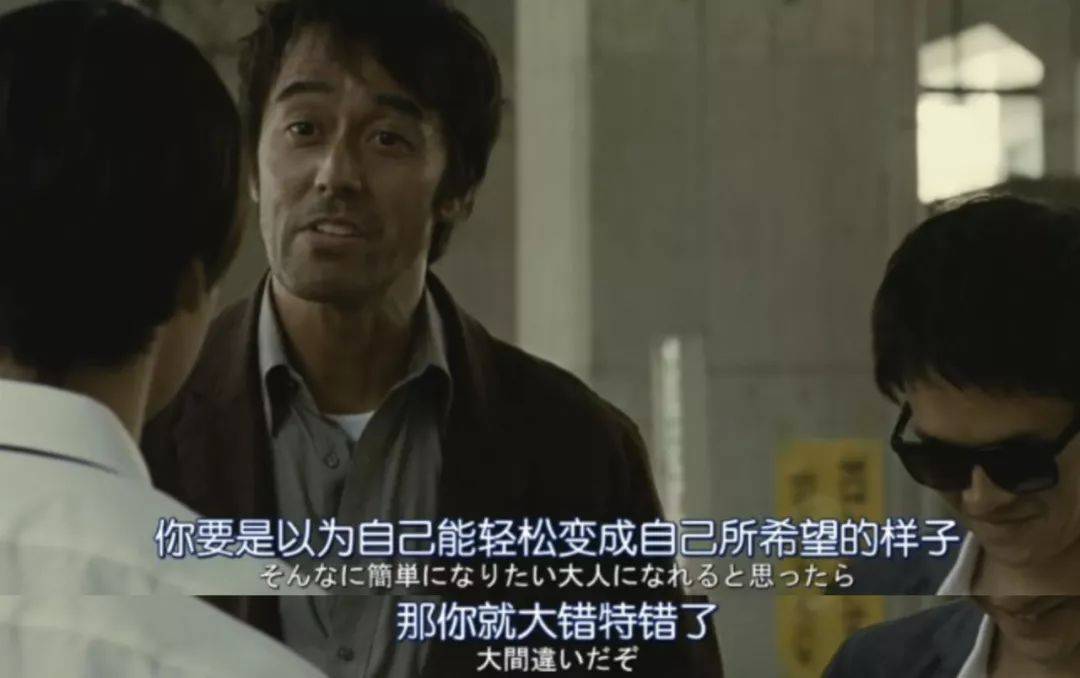
电影《比海更深》
是枝裕和在《比海更深》中借着阿部宽饰演的父亲之口说:“你要是以为自己能轻松变成自己所希望的样子,那你就大错特错了。”一个谅解平凡的人,是没有对于平庸的恶意的,他不会去触碰他人生活里的伤疤。
毕竟我们都生活在英雄没来拯救的那部分世界,每个人都在为朴素的生存做着最大努力的坚持。
对于平凡的宽容与善良,大概就是我们柔软生活里结的茧。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一点儿乌干菜(ID:NarratorZhang)。作者:章程,野生建筑师,青年写作者。豆瓣号:夜第七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