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扫码打开虎嗅APP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新周刊(ID:new-weekly),作者:罗屿。
9月 7日,相声艺术家常宝华去世,享年88岁。
9月 7日,小提琴演奏家盛中国去世,享年77岁。
9月11日,评书大师单田芳去世,享年84岁。
9月15日,表演艺术家朱旭去世,享年88岁。
9月19日,音乐人布仁巴雅尔去世,年仅58岁。
9月26日,粤剧名伶吴君丽去世,享年84岁。
9月28日,相声艺术家张文霞去世,享年84岁。
9月28日,摇滚乐歌手臧天朔去世,享年54岁。
9月28日,相声艺术家师胜杰去世,享年66岁。
......

2018年9月28日,相声艺术家师胜杰因病离世。图为2014年08月30日,相声名家齐聚天津,纪念马三立诞辰100周年,师胜杰在会上表演了相声《杂学唱》,图/视觉中国。
九月似乎被下了咒语,一个又一个艺术家离开了我们。在常宝华的告别仪式上,冯巩表示:“我听的第一个作品是常老的,那时候我上初中,它引领了我一生。哪怕是在很多困难的时候,常老都给观众提供了很多难得的笑声,创作了很多经典相声。”
清白做人,认真演戏,是那一代艺术家的共同特点。在下面这篇怀念北京人艺往事的文章里,我们可以看到真正的演员是如何诞生的。
斯人已逝,经典永存。那些相信“戏比天大”的演员,他们对艺术的敬畏与谦卑之心,不会也不该随大幕落下就离我们远去。
作为演员,有人说方子春是“含着玉”出生,史家胡同56号北京人艺家属大院是她从小生长的地方,她对众多人艺老人有着最贴近的观察与体悟。
即便过去几十年,方子春仍清晰记得儿时的某个傍晚,放学后的她推开家门,见一屋子的人正在对台词,有吕恩(1920~2012 )、舒绣文(1915~1969)、吕齐(1925年生),父亲方琯德(1921~1994)……

1962年1月20日,在北京电视台举办的第二次“笑的晚会”上,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演员方琯德(左一)在开场白中说道:“其实我不是喜剧演员,我是一个悲剧小生“。图/新华社。
她忙往外缩,却被方琯德叫住:“唉,你回来得正好,小春姑,给爸爸说一遍‘娘们儿’。”
娘们儿?方子春搞不懂父亲怎么让自己说这么难听的词。脸上热辣辣的她,使劲摇头捂嘴。
“春儿最乖了,就说一句,来。”
方子春被大人们哄得没办法,只好小声说:“娘们儿……”
“娘儿们”“梁们”“娘儿们儿”,方琯德他们学得南腔北调。方子春笑出了声,一遍遍大声教“娘们儿”“娘们儿”。大人们跟着认真学“娘们儿”“娘们儿”……
几个月后,北京人艺经典剧目《伊索》上演,扮演格桑的方琯德有这样一句台词——“这个娘们儿。”
在人艺大院长大,方子春常在不经意间就听到长辈们说出艺术真谛,她也见过他们从接戏开始就进入“神叨叨”的状态:黄宗洛会边炒菜边喊“修——理——皮鞋”;金雅琴练习跳大神,整日“天门开,地门开,我蛤蟆大仙下山来”,跳得全院出名;全院上下几乎每人骑一辆除了铃不响差不多哪都响的自行车上下班,一路探讨角色,车可不锁,但车筐里的水杯、剧本不能丢……
自2008年起,方子春用近十年时间探访、写作那些看着她长大的人艺前辈。在《一棵菜:我眼中的北京人艺》一书中,她写道:
我要通过这支拙笔,告诉人们醋打哪儿酸,盐打哪儿咸,如今我这一招一式是跟谁学的。“清白做人,认真演戏”这刻骨铭心的教诲,是我从父母和众多叔叔阿姨的言传身教中得来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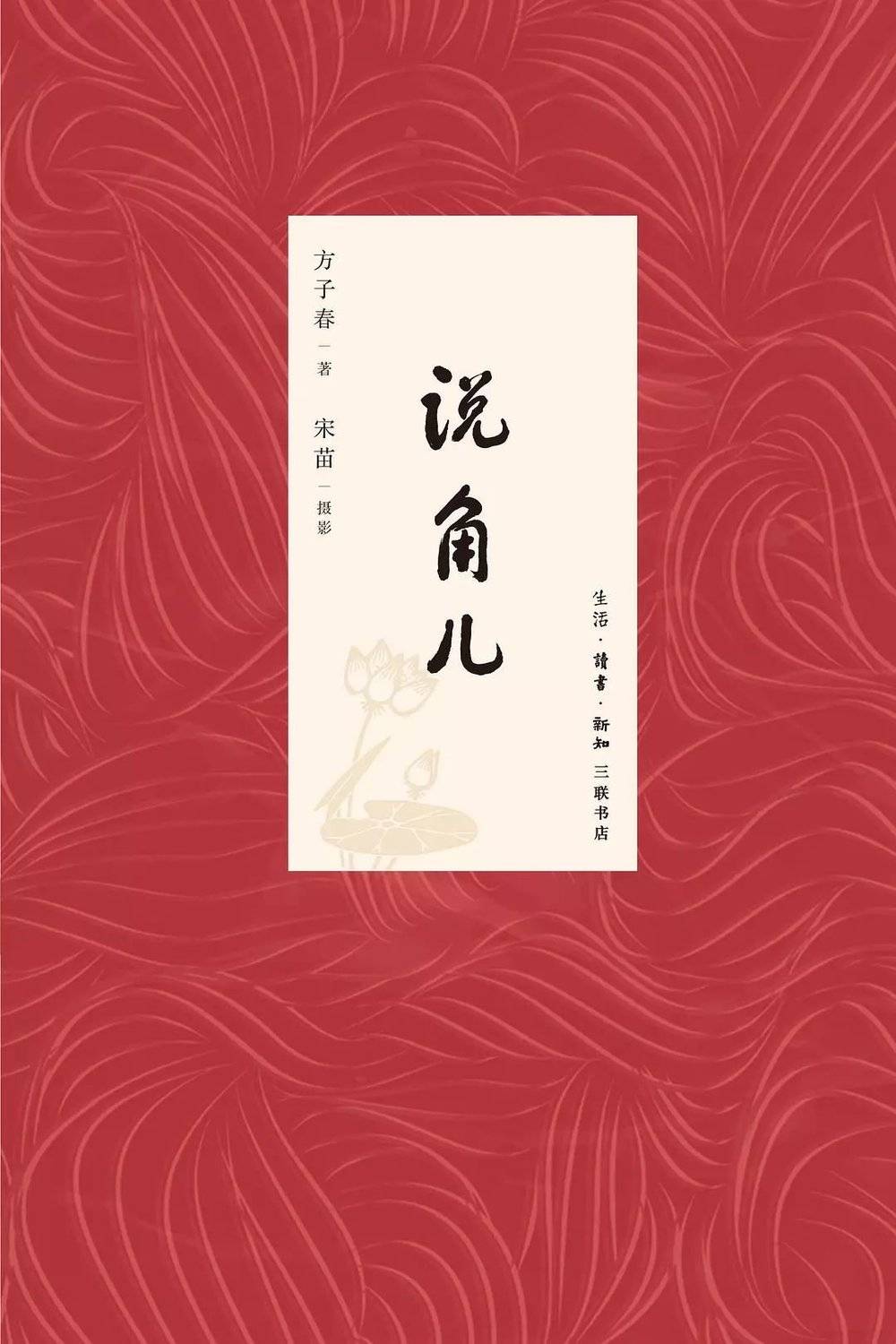
《说角儿》书影,作者方子春,中国儿童艺术剧院演员,中国戏剧家协会会员。
一、“演员没有扎实的文化基础怎么行?”
虽然没有成为人艺演员,但焦菊隐、夏淳、董行佶一直被方子春视作艺术之路上的恩师。
董行佶让她知道什么是吐字归音,为什么字正了腔就圆。夏淳告诉她,作为一个演员,在舞台上有激情只是最基本的条件,关键在于当激情达到极致时,如何控制和运用它。
当初想考文工团时,方子春本想让焦菊隐教教自己朗诵技巧,但焦菊隐却给她讲起《史记》。他说:“一个演员没有扎实的文化基础怎么行?”
“人艺是个学者型剧院,人人家里书多。”方子春记得,人艺老人们总讲演戏最后就是拼修养,搞文化事业的,没文化不行。
当年焦菊隐给方子春讲课特别认真:“《触龙说赵太后》的‘说’字为何读shui,他一遍遍站起,走到高高的书堆旁,打着手电从书堆里找出各种版本的字典,不厌其烦地告诉我,这是哪年出版的字典,里面是怎么解释的……”那时十几岁的方子春偶尔会发小孩脾气:“行了,我知道了,咱往下学吧。”焦菊隐却说:“别急,要吃透弄懂。”

焦菊隐(1905年12月11日~1975年2月28日),中国导演艺术家、戏剧理论家、翻译家,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奠基者之一。
焦菊隐在排戏时,同样也讲究吃透弄懂。他要求每个演员走进生活,以做学问的严谨态度,从生活中寻找创作的本源和力量。
方子春采访时,人艺人常会提到当年体验生活的情景:胡宗温演《山村姐妹》中金雁这个角色时已经40多岁,而金雁的年龄设定是24岁,怎么办?只有练。“体验生活时她在农村苦练,回来拍戏时筐里放上砖头,从一楼挑到四楼排练场,天天挑,天天练。”
1979年,夏淳复排《茶馆》,李光复坐中间桌,一句词也没有,可就是演不对,被导演轰下去好几回,让他去好好找找老北京老头儿的感觉。黄宗洛排《龙须沟》,故意在排练厅门口弄堆泥,要进排练厅了,先在泥上踩踩,带着人物感觉走进排练场。

1979年,《茶馆》在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公演。图/新华社。
方子春和黄宗洛有过一次合作,是在杨洁导演的《土家第一军》里,方子春扮演国民党特派员,黄宗洛饰演一名身为中共地下党员的采药老人。
“他房间里有好多好吃的,他会热情地请大家去吃,但有个条件,吃完不能一抹嘴就走,要和他好好聊戏。”方子春记得,第一天拍黄宗洛的戏,副导演亮开嗓子喊:“黄宗洛老师,到您了。”
就在大家东瞧西看地寻找他时,从导演身后不远处的犄角里站起一个裹着包头的老乡,嘴里说:“哎哎,我在这儿呢,嘿嘿。”
“只见他背着一个大箩筐,筐里有些野菜和一把锄头,头上用长长的布条缠了一圈,一件看不出本色的破布衫用布条扎在腰间,上边插的又是烟袋,又是放羊鞭子,还有草绳什么的,总之插满了七七八八的小道具。再加上他那一高一低的两个裤腿,腿上还抹点泥巴印,脚踩一双破草鞋,往本地人里一站,还真分不出来。”黄宗洛望着大家咧嘴一笑,露出两颗涂黑的大门牙。

黄宗洛(1926年9月26日-2012年6月30日),话剧代表作品有《茶馆》、《三块钱国币》,电视代表作品有《西游记》的铜台知府、《水浒传》的郓城知县、《笑傲江湖》的平一指、《新天仙配之七仙女正传》的槐树精等,被誉为“龙套大师”。
其实那天导演只需要黄宗洛在院子里走个过场,他那身行头全都没用上。但黄宗洛却对方子春说:“导演可以什么都不要,可导演要时,演员不能什么都没有。”
创作起来“极度忘我”的,还有演员田冲。人艺成立时曾排过一部波兰戏,田冲饰演剧中裁缝。道具组从著名老店普兰德借来一块上好布料,上台前嘱咐田冲:“别弄脏,别弄破,太贵,咱赔不起。”田冲满口答应,可戏演起来,他就全忘了,演到兴奋处,三下五除二,把名贵布料剪了,剪得一塌糊涂。据说当时负责道具的人差点晕过去。
人艺人不仅演戏忘我,还特别爱琢磨。
一个角色能琢磨几十年的郑榕,说自己“80岁以后才会演戏”。天生结巴的朱旭,之所以能把台词说得行云流水,在于他会用多于常人的时间把台词化成自己的语言。方子春采访吕中时,吕中提到,当年每次去外地巡演,于是之、英若诚、朱旭他们准会提溜着一瓶酒,端着夜宵,找个地方喝上一口。大家天南地北一通聊。
于是之讲:“今儿你那场戏,特……特……特棒!”有人回:“我当时就感觉,你给了我一个反应。”吕中他们端着饭在旁边看,特别过瘾。北京人艺甚至因此流传着一句话:“聊天是学习和增长知识非常好的方式。”

朱旭(1930年4月15日-2018年9月15日),1952年成为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成立后的第一批演员。1996年,凭电影《变脸》成为当年东京国际电影节的影帝。朱旭还曾荣获一次百花奖影帝,并五次入围金鸡奖影帝。
二、戏比天大,有什么话不能直说?
在方子春眼里,那些看着她长大的叔叔阿姨,不仅在艺术上才华横溢,生活中也单纯有趣。
史家胡同56号大门口有个外绿内白的搪瓷灯罩,春夏秋三季,夜晚的灯下总围着一圈人,这群人里准有朱旭。他要么笑呵呵地坐在棋盘前叫人家臭棋篓子,要么一脸认真地拉胡琴。春夏秋冬,日月更迭,朱旭带在身边的,从儿子变成孙子,然而即便成了爷爷,田冲撞见他,还会拍他后脑勺。
方子春有一次看牙医,碰到董行佶。“小董叔叔就站在走道上任人们在我们身边走来走去,从大夫如何撑开你的嘴开始表演,喉咙里还时不时发出电钻的‘吱吱咭咭’声和感觉疼痛的呻吟声,加上他痛苦地用手捂住腮帮和欲哭无泪的表情,我的牙真的痛起来了。”
而这时,董行佶突然从夸张表演回到常态,诚恳地对方子春说:“回家吧,不到万不得已,别看牙!”

董行佶(1929年4月8日~1983年6月21日),1951年加入北京人民艺术剧院任演员。1980年代初,董行佶主演电影《廖仲恺》,凭这个角色获得1984年金鸡奖最佳男主角奖。
热心的董行佶有一次却“败”在了更为热心的金雅琴手上。某日,董行佶、陈国荣夫妻吵架,金雅琴先是在人家门口大喝一声:“住手!谁动手我就打谁。”
只是,她非但没劝成架,反倒加入“混战”。“她抓过又干又瘦的小董叔叔,把他头向后、腚冲前往自己腰间一夹,捶鼓似的一通打……小董叔叔似干鸡般被高大壮实的雅琴阿姨夹得不能动,早已四脚离地一劲儿乱蹬。”
最终,还是陈国荣开了口:“雅琴,你别打呀,你不是来劝架的吗?”金雅琴听罢,“嘎嘎”大笑。
即便打成这样,大家心中也并无芥蒂。做人如此,做戏亦如是。
因为人艺排戏,多是几个人轮演一个角色,方子春有一次问蓝天野,大家难道就真没矛盾?
蓝天野倒也不绕弯子,他说演戏谁多了、谁少了,会有意见产生,但一般来讲,这种情况确实很少。“为艺术上的分歧争得不可开交、脸红脖子粗,很正常,过后便不是问题。”
方子春对此也有同感,之前她看人艺60周年纪录片,里面提到苏民排《蔡文姬》时,徐帆为了一个观点在排练场和苏民吵起来。
“进了人艺排练场这里没有什么叔叔、大导演、老前辈,也没有说不得的名演员。人艺排练场里贴着四个大大的字:戏比天大。这四个字下,有什么观点不能阐述?有什么话不能直说?在这里,人心还是那么干净。”

2011年,人艺复排《蔡文姬》,苏民、濮存昕父子齐上阵。右图为1950年代的苏民。2016年8月28日,苏民先生在北京逝世,享年90岁。
三、毕业就演大主角是一大灾难
十年间,方子春不仅采访人艺老人,也采访了不少同辈。
发小濮存昕被调到人艺后排的第一个戏,是蓝天野导演的《秦皇父子》,其中有段独白,蓝天野认为濮存昕演得“假大空”,重排了十多遍。休息时,郑榕一招手:“小濮,过来。”濮存昕就像落水时有人搭救一般向郑榕走去。“小濮,说话别那么说,放松,先解决放松,这是基本的……”
喜欢给年轻人讲戏的郑榕,可不总是这么温和。排练《秦皇父子》时,还是人艺学员的冯远征和同学们一起演大兵。冯远征他们在后面看激动了,窸窣有声,只听郑榕说:“谁在后面讲话,滚!滚出去!”舞台监督立马将这些学员从排练场轰出去,在楼道里罚站。冯远征说,人艺是讲规矩的剧院,是规矩不是规定,规矩靠的是口传心授。

《秦皇父子》剧照(摄于1986年),郑榕饰秦始皇,濮存昕饰扶苏。
和冯远征同在人艺85班的吴刚,显然就受了这规矩的影响。2004年排《合同婚姻》时,他只有一个要求——排练厅要绝对安静,打电话请到外面。“大家干戏就好好干,不干就回家睡觉去。”
同辈演员和方子春说得最多的,就是老一辈的“传”“帮”“带”。吴刚记得,当年夏淳给自己排戏,排了二十多遍还是过不了关,吴刚有点抵触,可夏淳不急不恼,依然用不大的声音慢吞吞地说:“再来。”直到真正上台演出那天,观众掌声响起,吴刚才知道夏淳的用意:“他这是在磨演员的性子,让你知道什么是演戏。”
钱波说,老一辈演员一接到饰演的角色,就开始从里到外找感觉,甚至上午排完戏,中午回家吃饭服装都不换。“他们让我们知道,当演员演戏和名利无关,所有人都好这口,如痴如醉。什么是‘本’?这就是‘本’。”

人艺85班五虎,左起:冯远征、王刚、丁志诚、吴刚、高冬平。
濮存昕记得,《甲子园》刚建组,朱旭就拿着《易经》在读,领会角色。“因为老艺术家生活中只有这一件事。但我们能做到吗?能把周围的事全放下?不可能。什么都想得到,钱要挣,戏要演,名要有。”
何冰回忆,上世纪90年代初,北京人艺排演《鸟人》,7点30分开戏,4点45分林连昆就已经在后台,“沏了碗茶,点了根烟,抽几口,喝口水,慢慢地默戏,找人物状态呢。你说和这样的先生同台演戏,怎么能不进步,怎么能不努力?!”
何冰和所有演员一样,进人艺先跑龙套,在舞台上戳大杆(站在台上举旗杆)四年。杨立新在30岁前没演过重要角色,在剧院就是踏实地学戏演戏。杨立新和方子春强调,北京人艺有句话——“毕业就演大主角是一大灾难。你没那能耐,站在台上会哆嗦,私心杂念太多,肩膀扛不起这大梁。”

2009年7月29日,新版话剧《鸟人》上演,何冰饰演剧中经典人物“三爷”。
梁冠华一直觉得前辈们不光教他们演戏,还教他们如何做人。当初他们班跟着剧院排《吴王金戈越王剑》,有几个同学演了小角色,没他什么事。他想不通,把想法写进日记。
苏民看了,告诉他,挑上别人,可能是形象合适,作为演员都有局限性,要有准备,不能患得患失。“老先生之间有什么矛盾咱不管,但是他们没有把不好的教给我们,只把做人的好品格教给我们。这是北京人艺深沉的一面。”
方子春记下的人艺往事,向我们讲述了真正的演员如何诞生。人艺那些经典戏剧从最初的磨砺,到成就光芒,时间是最权威的裁判。而戏剧背后那些相信“戏比天大”的演员,他们对艺术的敬畏与谦卑之心,不会也不该随着大幕落下就离我们远去。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新周刊(ID:new-weekly),作者:罗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