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扫码打开虎嗅APP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大家(ID:ipress),作者:邓文初(文史学者,思想批评者,著有《民族主义三部曲》等)。
华佗神功是真的吗?
从起源而言,《黄帝内经》大约是没资格坐中医头把交椅的,其作者一直无法验明正身,其内容也多经后世窜入与篡改,经典之说多少值得商榷。相反,20世纪70年代马王堆出土的《五十二病方》,不但时间精确(公元前168年),而且文本经泥土千年封存,如地下档案般容不得后人作伪,实在是应该出任中医群经之首的。

《帛书五十二病方》
然而,除了医学考古与医史专业的研究者们真正重视外,中医界反倒不太在意这部能彻底改写中医文化及历史的秘籍。
《五十二病方》不谈阴阳之类,没有五行之说,而是老老实实地记载了308例病方,299种药物;治疗以手术为主,而不是汤药,其中一些医案至今看来都称得上“高科技”,比如方中相当多的痔疮割治。
《牝痔》第七方所记为女性内痔割治,手术方法是:取狗膀胱,扎住其中两个管道,以细竹管插入另个一管道,塞入肛门之中,吹气使膀胱膨胀,然后再慢慢将膀胱往外牵引,待肛门向外翻转露出痔核时,再用刀切除。这套技术,据医界的说法,与现代西医外科“气囊充气式”割治痔疮术基本相同。
当然,《五十二病方》的价值,并非仅在印证中西偕同的原理,而是,它改变了我们对于中医的整体认知,一些历史上流传而被当做神话处置的史料就此得以进入严谨的医学史。比如华佗神话。

明人绘制的华佗像
《三国志》记载华佗医术:
若病结积在内,针药所不能及,当须刳割者,便饮其麻沸散,须臾便如醉死无所知。因破取,病若在肠中便断肠湔洗,缝腹膏摩,四五日瘥(病愈),不痛。人亦不自寤。一月之间即平复矣。
华佗医术中这些“刳割”“破取”“断肠湔洗”“缝腹膏摩”之类,在以阴阳调和为理、汤药主治为术的后世中医与文人看来,多少有些无法理解也不敢正视。因此,一些历史记载如“帝(司马师)目有瘤疾,使医割之”(《世宗景帝纪》)之类的眼科手术,就被史家沈约等怀疑;《汉书·王莽传》中王莽命令太医、尚方与巧屠将政敌抓捕,做“活体解剖”,说是为了治病,“量度五藏,以竹筵导其脉,知所始终”之类,自然被认为是不经之谈。尽管解剖一词最早记录于《灵枢·经水》,但传统中医总是讳言此类“血腥”之事。
到了科学化时代,华佗、扁鹊等医术引发质疑,也就顺理成章了。陈寅恪老先生就颇为怀疑华佗故事是比附印度佛教的,见其名文《三国志曹冲华佗传与佛教故事》;卫聚贤则认为扁鹊来自印度,后来的医学史家如廖育群则略微严谨些,认为华佗故事多少起源于后人的心理需求的建构等等,华佗技术于是真的被当成神话了。
那些遗失在方外的外科技术
不过,问题也还是存在的,华佗医术如果真能代表当时医疗水准,而非个案或神话,按理它不会随着华佗被杀而失传。要重建中医的新谱系,需要医学史拿出系统的史料。
好在《五十二病方》并非个案,2001年在山东大汶口遗址发现有一例开颅手术证据,如此,可以证明早在五千年之前,就已经实施这类高难度手术了。医学考古界发现的这类开颅术至少已经有了三十多起,这些算是地下的发现。
文献中的记载其实也并不算少。南北朝的《刘涓子鬼遗方》也是一部外科专著,一些史家认为它是刘宋武帝(420-422年)的随军外科医生龚庆宣的著作。魏晋南北朝之后,外科有传承发展,如兔唇修补术,《唐诗纪事》“方干”条中记载,替方干修补兔唇的医生曾治愈过十人(兔唇修补术的记载延续至17世纪)。一些医学史家如李经纬等为此认为,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医以外科为主流,原因可能与打猎和战争密切相关,需要面对经常性与大面积的创伤和化脓性感染。我国最早的医事制度和分科中设置了金疡和折疡应该也是反映这种社会需求的,如《周礼》中记载的“疡医”负责治疗疮疡、肿疡、刀枪和骨折之类。

《刘涓子鬼遗方》
此后的外科文献其实也是不绝如缕。1602年,王肯堂著有《外科准绳》,书中记载了诸如肿瘤摘除术、甲状腺切除术、肛门闭锁症成形术、耳外伤脱落缝合再植术、骨伤科整复术等,手术过程中的消毒技术也有详细记载。1604年申斗垣著《外科启玄》,1617年陈实功著《外科正宗》,书中尽管采纳了内外兼治理论,但却记载了相当丰富的外科术经验,如截趾术、下颅骨脱臼整复术、骨结核死骨剔除术、鼻息肉摘除术、咽部异物剔除术、食管气管缝合术等。

《外科准绳》
《外科正宗》记载了一则食管气管缝合术,即使放在今天,也足以令人惊叹。气管和食管都割断了,但如果还没有“额冷气绝”,可以迅速实施抢救:
急用丝线缝合刀口,掺上桃花散,多掺为要;急以棉纸四五层,盖刀口药上,以女人旧裹脚布将头抬起,周围缠绕五六转扎之,患者仰卧,以高枕枕之脑后,使项部郁而不直,刀口不开,冬夏避风,衣被复暖,待患者从口鼻通出,以姜五片,人参二钱,川米一合煎汤,或稀粥每日随便食之,接补元气。
手术自然要快,但康复时间却较漫长,陈实功说,食管气管都断了的得百日之功才能痊愈,只断一根则需要四十日之力。以此方式他曾治愈过强盗郭忠、皂隶沙万、家人顾兴,都是气管和食管俱断者,还治愈过十多个单断者。
不过这些高难手术很难为正统医家理解与容忍,为了说服自己接受这些事实,一些文人需要借助“兽医”技术以为佐证。明代叶权在《贤博编》中就以治疗鸡瘟的事来证明这些手术之可信,他说:“鸡瘟相次死,或教以割开食囊,探去宿物,洗净,缝囊纳皮内,复缝皮,涂以油,十余鸡皆如法治之,悉活。庄家所宜知,且华佗之术不诬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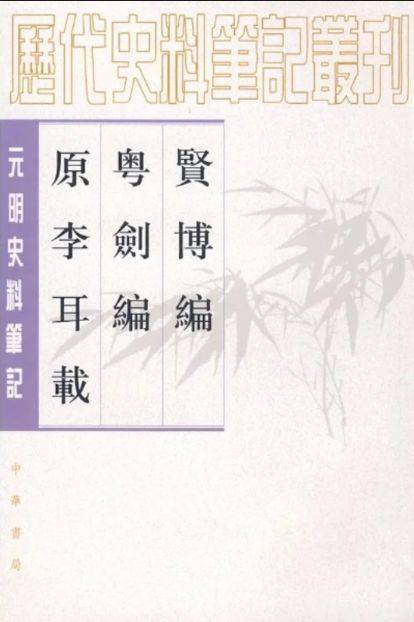
《贤博编》
这样的证明真是令人哭笑不得,然而却不得不如此。这里的“华佗之术”,简直就是乡下普通百姓的“日常之道”。农家自养鸡鸭有时误食了田间药耗子的谷粒,有倒地气绝的,农村妇女们舍不得扔掉,往往就自己动手,一把剪刀将食囊剖开,把里面的毒谷粒掏出来,再用水清洗,棉线缝合,伤口上喷几口清水算是消毒,就随手丢在泥地,过段时间,鸡鸭又活过来了。公猪阉割、大型动物牛羊等的破腹清肠之类,稍微复杂些,但几乎每个村子都有那么一二人会这活。
至于治人的外科,在西南等偏远之区也是“百姓日用”之类,湖南西部、云贵、四川、广西一带的民间“水师”(正骨兼外科,也具有部分巫术意味),其实就是“职业外科”,“华佗传人”。活动在云南一带的“老神仙”陈凤典(原籍河南),湖南辰溪骨伤科医生张朝魁、贵州的“李神仙”等,都是能“剖腹刳割”的“郎中”,只是他们被边缘化,只能在地方层级流传,那是属于方外传统,留待以后再说吧。
儒生入医与中医的玄学化
为什么外科医者只能在外围生存?这与儒生入医有关,与中医的玄学化有关。
一般认为中医的玄学化是从南宋开始的(理学正好那个时候兴起,台湾中央研究院李建明认为,外科的衰败,及其内化倾向,始自南宋,凡三变,即南宋、金元、明清交替之际),那时的主流医家往往将这些外科医生当做草泽郎中对待,责其为“庸俗不通文理之人”,说他们“甘当浅陋之名,噫其小哉如是!”

朱熹画像
清代苏州名医张璐在回顾自己从医经历时将中医的这种变迁划分为三期,其一在明中叶之前,为“其技各专一门”,接着,就是大量儒者进入医界;第二期,在明清交际,“壬寅以来,儒林上达,每多降志于医,医林好尚之士,日渐声气交通,便得名躁一时,于是医风大振,比户皆医”;第三期,是儒林医学全盛,而专科医生由此式微。尽管一些大儒进出医学,似乎不是为了稻梁谋(如吕留良不愿意出仕清廷,“自弃诸生后,提囊行药,以自隐晦,且以效古人自食其力之义”),但事实上,绝大部分士人是出于生存逼迫,科考失败,无官可做,又无一技在身活命,于是只好靠行医来救活自己了。
儒生入医,当然只能以“医之下者”的汤药为谋生工具,因为背诵几首汤药歌诀,检讨几首名家医案,就可以挂号接诊,手法至简至便,名声至高至清,收益似乎也多少不薄,于是乎大家都来“悬壶济世”,从此以后,“外治法衰,而汤药法兴”了,外科内化,谈玄说理于是大盛。
清著名温病家王士雄,在其《归砚录》中曾对中医的技术化路径中断有过分析,说远古医学,无分内外,刀、针、砭、刺、蒸、灸、熨、洗诸法并用,不专主于汤液一端(这几乎是当时医学界的共识,刘民叔分中医为六派,汤液只是其中之一,他近乎哀叹地说,“及于今日,惟汤液一派,用药治病,为世之显学”)。今诸法失传,而专责之汤液,故有邪气隐伏于经络之间,而发为痈疽也。

《归砚录》
事实上,绝大部分文人医者沉醉于文薄之间,所谓治病无非儿戏,偶尔治愈几个病人,则以神医自诩,其实这种利好不过是“待贼之自毙”,用现代医学术语来说,那就叫做身体自愈。
王士雄的批评,既针对这些业余儒医,也针对那些不知究竟的病人:
“今针、砭诸法不行久矣,医者弃难而就易,病者畏痛而苟安,亦由今时之风气,尚虚声,喜浮誉,循名而不责实。世道所以愈趋而愈下者,时也,势也。”
“医者自谓谨慎,而不知杀人无迹,病者乐于苟安,而至死不悟。”
王士雄还说,这些所谓儒医根本没受过外科手术训练,不知道如何使用刀针,因此,就只能凭借记诵的几个处方,开几副汤药,却装出一种爱护病家的样子,说手术会置生命于危险之中,且大伤元气。又将脓肿痈疽认做内病,而将那些重征认作死征,“果死可以显我之有断,幸而不死,又可邀功而索谢”。王士雄感叹,这种做法,其实就是“以愚病家,而自护其短”,真是欺天啊!

医者食病,尚可美其名曰自食其力,病者害病,只好归咎于命不好,或不遇名医。其实双方都苦,儒生不业儒而靠悬壶济世的大话假话过活,苦;百姓惑于名医之名而以一己的身体布施名医,苦;不过这苦有所不同,百姓即使做了牺牲,就算有怨,也不过怨自己的命;儒生收受些米谷钱粮,多少也心有不平,但这不平并非为百姓呼怨——他们本来就是寄生阶级,何在乎百姓之生死呢?——而是为自己做不得良相却转而求其次悲号。
由于儒家掌握着几乎所有的社会象征资本,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因此,医家只有走“文本化”、“经典化”之路才能获得社会承认,获得认可与声誉。而这些儒生,尽管他们并不懂医,也没有传授师承(专业医家绝对讲究“手法必求传授”),但他们却掌握着书写历史、建构医学谱系的话语权,什么是正统、什么是外道,是文人们说了算的,他们有如姜子牙掌握着封神之权一般。于是,一些真正的医家不得不屈身示好,以求厕身由这批文人所掌控的万神殿。
《归砚录》中还记载了一则逸事:一瓢先生本是一名医,但地位不显,其孙薛寿鱼于是给著名文人袁枚寄去墓志,望其能替祖父作序,借此得以跻身儒家名士之列。不过随园先生绝非陋儒,他并不相信儒士们的鬼话。序言倒是写了,却对世人以儒生名号为号召的时尚予以痛斥。随园先生说,一瓢先生本是“医之不朽者”,没想到你寄来的墓志却无一字提及他的医学,却托名其讲学之类,这真是不孝了,“天生一不朽之人,而若子若孙,必欲推而纳之必朽之地”,真是可悲啊。

袁枚像
袁才子并非责问个人而是针对文化风气,他说,“今天下医绝矣,惟讲学一流传而未绝者何也?医之效立见,故名医百无一人;学之讲无稽,故村儒举目皆是。”医学靠的是实在功夫,容不得半点假货,所以名家难成;但讲学之类却纯虚不实,所以大师之类满街都是。但那些真医家真名手却不得不依附文人名士以获得这些微声誉,他们弃实学而崇虚名,绝功夫而谈阴阳,于是,中医走上了玄学这条不归之路。这段话放在今天,似乎也蛮应景的。
文人易为而方技难通,专家难以享受声誉之隆而文人最易获得声望,因此,医家中的那些业余爱好者便以玩文字、读《内经》而出名,正如佛教中苦修之徒少而口头禅者多,中医变成现在这个样子,话语喧嚣而技术滞碍,正是中国文化的一个表征。
彼得·科斯洛夫斯基在《后现代文化》中说,技术知识与技艺的发展、奠定和传承,有它们的文化前提,“采取何种技术方式,是由文化决定的。”玄学化之后的中医强调自己独特的文化传统,其实不过是儒家文人的强势话语对中医历史的改写与重构的产物,是“文字教”传统塑造的结果。
要复兴中医,大约得中医先给自己把把脉,清理清理这条玄学之路所造成的后果,救人总须先自救呢。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大家(ID:ipress),作者:邓文初(文史学者,思想批评者,著有《民族主义三部曲》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