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扫码打开虎嗅APP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经观书评 (ID:jingguanshuping),作者:何奎,题图来自:视觉中国
卢周来先生作为一名出道和成名皆甚早的“70后”经济学家,近期出版了一本新作《极高明而道中庸——经济学读书札记》。
这是一本他进入新世纪以来对经济学领域诸多名著进行阅读与思考之后的随笔集,凝聚了他对近20年中国与世界经济领域和经济思想种种变化的集中思考。
在这本书中,他重点表达了一个极具启发意义和现实价值的经济学立场,即在市场与政府、效率与公平、民富与国强、个人自由与集体规制等看似矛盾的关系中努力追求均衡,达到一种最优的经济发展状态。

《极高明而道中庸:经济学读书札记》
卢周来 | 著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3年6月
一
从亚当·斯密开始,随着古典经济学的诞生,人类对经济学的理解才有了一个独立完整的、一以贯之的思想理论体系。
虽然随后的两百多年经历了新古典经济学、凯恩斯主义、新奥地利学派、货币学派、公共选择学派、理性预期学派、新制度经济学、信息经济学等各种流派,但是概而言之,主要是两种经济学思潮在人类历史上交替出现:
一种是经济自由主义思潮,主张自由竞争与自由放任,充分发挥市场“无形之手”的作用;另一种是国家干预主义思潮,主张政府对经济活动干预,充分发挥“有形之手”的作用。
虽然他们出现的时代背景与逻辑前提各不一样,但平心而论,这两种思潮基本是在不同时代以不同的面貌交替出现,回答不同时代涌现出的“时代之问”,成为一个时代的“精神标记”。
这既是基于当时的政治、经济与社会变革的现实需求,也是基于市场与国家的两重性在不同历史情境下的轮流演绎。
所谓“市场的两重性”,一方面是指市场机制是微观经济运行的核心,通过价格和信息等信号促进资源配置效率的帕累托最优或次优,激发微观主体的创造活力,并实现社会收入的自动分配和经济秩序的自动调节。
另一方面,市场机制也会出现失灵的时候,在面对垄断、负外部性、公平缺失等难题时,它也无法实现自我调节。
因此,亚当·斯密在充分肯定由“利己主义”驱动的市场机制的合法性同时,也明确意识到“个人利益在引导人们的行为方面的失误是大量的和一贯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施蒂格勒语)。
所谓“国家的两重性”,一方面是指国家干预通过财税、金融、产业、法律等宏观政策熨平经济周期的剧烈波动,解决“市场失灵”时的顽瘴痼疾。
另一方面,国家的干预又极有可能引致市场信号失真或资源错配,甚至伤害微观市场主体的创造活力,进而成为“政府失灵”的痛苦渊薮。
因此,在市场与国家这两只手分别发挥作用的时候,既有各自的边界与疆域,又有着各自无法抵达和无法企及之处。
因此,新古典经济学大师马歇尔承认国家在控制垄断、解决穷人的住房和处理贫困问题上的潜在作用的同时,也强烈坚持对私人企业的偏好。
在他看来,这种偏好基于这样一种信念:官僚主义的管理必定是难于负担的和无效率的。他1919年在《工业贸易》一书中发表他一生中最勇敢的言论:
“如果100年前(1807年)政府的控制就取代了私人企业的控制,那么就会有很充分的理由设想,我们的制造方法的效率将和50年前一样,而不是比那时高出3倍或5倍。”
其实,从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史嬗变的历程来看,市场与国家的两重性既历史地存在,也被历史地感知。
管仲既认识到“市者,货之准也”,又认识到“通轻重之权,徼山海之业”“上下有义,贵贱有分,长幼有等,贫富有度”。荀子既认为“农农、士士、工工、商商,一也”,又认为“工商众则国贫”。司马迁既主张“善者因之”,又主张“其次整齐之”。丘浚既强调“民自为市”“听民自便”,也强调“稽岁计之出入,审物产之丰约,权货币之轻重,敛散支,调通融,干转一切”。
这些思想虽然皆以朴素而零散的语言呈现,缺乏一个现代经济学意义上的独立完整的思想体系,但基本都充满了对市场与国家的两重性的辩证思考,闪耀着真理的光芒。
对于中国古代先贤们相继涌现出的这种思考,李约瑟曾经说过,“当希腊人和印度人很早就仔细地考虑形式逻辑时,中国人则一直倾向于发展辩证逻辑”。
事实上,后来的萨缪尔森也同样意识到新古典经济学与凯恩斯主义各自存在的问题,于是提出新古典综合理论,力图“让国家之权威与私人之策动互相合作”,并宣称“星期一、三、五,我可以是一名萨伊定律的侍从,而星期二、四、六,我却可以是一名凯恩斯分子。”
只是他的新古典综合理论有着刻意拼凑之嫌,存在内在的逻辑矛盾,因而没有在学界与现实中完全站稳脚跟。
二
回到现实中,我们简单回顾中国经济改革过去四十多年的历史进程,发现虽然其间经历过时代的荣光与岁月的淹蹇,但是中国经济这艘航船总体在动态的调整中沿着一个正确的航道运行,而且在不同的历史时刻发生了诸多关于市场与政府、效率与公平、民富与国强之间的热烈争论。其中既有着基于不同历史语境的洞察与卓见,也有着基于不同话语立场的偏狭与坚执。
近几年,关于民营经济、共同富裕、网络超级垄断以及一些产业政策与宏观经济取向不一致产生的一些争辩,究其思想根源,似在于对市场与国家的两重性的理性认识不足。
因此,卢周来先生在书中大声疾呼“极高明而道中庸”“取各家之长,舍各家之短”。“极高明而道中庸”一语源自儒家经典《中庸》,其要义是“叩其两端,允执厥中”。
这是一种先进的思想方法论,即发掘各端之优长,抑制各端之弊短,努力防止偏执一端形成“片面的深刻”,进而达到一种均衡和“善治”。而要实现它,既离不开一种理论认知上的清醒与自为,也离不开一种现实运作的理性与自觉。
王阳明云:“无善无恶心之体,有善有恶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宛如人性有着善与恶的两重性,市场与国家也潜藏着各自“善与恶”的两重性,而其中的“善”既是各自的天然优势,其中的“恶”也是各自的天然缺憾。
这就需要我们在“格物”之时,平衡好二者内在的“善”与“恶”,各善其善,各美其美,以此之善去彼之恶,以彼之善去此之恶。故而理想的经济路径选择,应该充分认识市场与国家的两重性,超越“左右之争”和“两端之争”,择“中道而行”。
此外,对于经济学家的使命,卢周来先生虽然没有在本书中展开大篇幅论述,但从其一直以来的治学实践来看,不论是此前写的《穷人与富人的经济学》,还是他在诸多报刊上发表的经济学随笔,其实是在扮演着一个大众启蒙经济学家的角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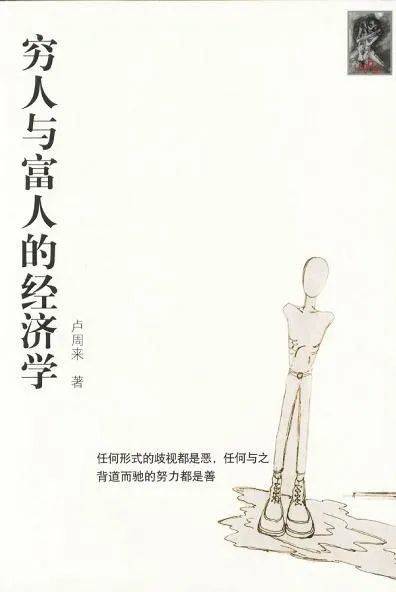
《穷人与富人的经济学》
卢周来 | 著
海南出版社,2002年5月
纵观自亚当·斯密以来不同流派的经济学家的理论思考和现实作为来看,经济学家的使命,既不只是根据不断变化的历史语境在理论建构上不断进行刷新和超越,也不只是影响一个国家或时代的社会经济政策走向,还在于在庙堂与林泉之间、在经济运行与普罗大众之间搭建一个良性互动的信息桥梁。
因此,乔治·斯蒂格勒(George Joseph Stigler)在《经济学家和说教者》一书中曾经旗帜鲜明地指出:
“经济学家的主要任务一直是以大众可以接受的方式解释实际经济现象。近200年来,我们始终满怀信心地面对这一任务,尽管我们并不总是能取得极大的成功。”
这不仅是因为经济现象、经济政策既影响着普罗大众在微观领域的自由选择权利与资源配置效率,还因为它们会在政策效应与微观活动之间构建起一种关联关系。
此外,大众的经济行为和政策效应也会给经济学家提供新的通路反馈和思想刺激,进而帮助经济学家们重新去反思一种流行理论的“灰色之处”(施蒂格勒也曾说过“不要把流行的哲理炫耀成科学”),探索在新的历史语境下理论创新的可能性。
当年,理性预期学派正是关注到了微观经济主体在作出行动决策前,除考虑到当前物价、工资及资产收益率等经济变量之外,还会对这些变量将来可能出现的情况作出预判,才提出了“理性预期”学说。
虽然理性预期学派对大众预期的有效性与国家干预的无效性作出了过于绝对化的判断,但大众的预期尤其是对未来经济的整体预期也实实在在地影响着一个国家的宏观经济绩效及其政策走向。
当下,中国经济面临的一个很重要的挑战,就是大众对未来的预期与信心不足,进而在一定程度上引致民间投资动力不足、消费市场暂时疲软等问题。
这也恰恰需要重新审视施蒂格勒当年所言的“经济学家的主要使命”,亟待在中国宏观经济政策、社会经济现象与大众的认知预期之间搭建起一座座桥梁,从而避免信息的鸿沟与认知选择的偏差。
而且,这些桥梁的搭建不能是苍白的说教与理论的灌输,而是一个基于信息充分、基于“大众可以接受”的理性互动的桥梁。
2023年,中国宏观经济指标与微观主体感受之所以存在“温差”,虽然与不同的微观主体遭遇到不同的现实情境有关,也与这种桥梁尚未完全以一种“大众可以接受”的方式来搭建有着一定的关联。
当然,这种“大众可以接受的”言说方式,并不是简单地追随或盲从大众的情绪与意见表达,而要基于客观的事实、透彻的说理、漂亮的叙事以及经济学的基本伦理。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经观书评 (ID:jingguanshuping),作者:何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