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扫码打开虎嗅APP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晚点LatePost (ID:postlate),作者:曾梦龙,编辑:钱杨,题图来自:视觉中国
史上最伟大的视频游戏是什么?
所有玩家为此争论不休。从媒体的评选榜单来看,《超级马里奥兄弟》《塞尔达传说》《我的世界》常常名列前茅,但拔得头筹的却是一款 40 年前诞生的游戏——《俄罗斯方块》。
大众媒体《时代》周刊在 2016 年将它评为“史上最好的 50 款视频游戏”的第一名,称“几乎所有平台上都有这款游戏,这证明了我们对堆砌方块永无止境的热情”;科技媒体 Digital Trends 在今年也把它评为“史上最好的 50 款视频游戏”的冠军,说“40 年来,无论开发商如何变化(从眩目的 VR 版本到独具匠心的对战形式),这款令人上瘾的游戏始终如一,体现了一种不受语言或年龄限制的普遍娱乐形式”。
《俄罗斯方块》有着众多世界记录:它是发布平台最多的游戏,高达 65 个;它是最畅销的视频游戏,销量达 5.2 亿份,是第二畅销的《我的世界》的近两倍;它是第一款进入太空的视频游戏,陪伴宇航员度过了 196 天、绕地球超过 3000 圈等等。
在商业上,它为任天堂至少创造了数十亿美元的收益,并帮任天堂确立了从 1980 年代末期到 1990 年代中期的游戏行业霸主地位。它也改变了创业者亨克·罗杰斯(Henk Rogers)和发明者阿列克谢·帕基特诺夫(Alexey Pajitnov)一生的命运。它还被看作自从卫星发射以来,苏联最重要的技术出口产品。
《俄罗斯方块》在文化上也有诸多影响。它推进了人类对大脑的认知,加深了人类对电子成瘾和精神治疗的理解。它创造了一种流行文化,俄罗斯官方、各国民间、各个公司都各取所需地挪用符号。
《俄罗斯方块》在不同世代的旺盛生命力让人惊叹。“你的父母玩过俄罗斯方块,你的孩子玩过俄罗斯方块,你也玩过俄罗斯方块。在地球上几乎每个国家,你都会遇到同样的故事。”科技作家丹·阿克曼(Dan Ackerman)在《俄罗斯方块效应》(The Tetris Effect: The Game That Hypnotized the World)一书中写道。这是目前唯一一本有关《俄罗斯方块》的非虚构专著。
2024 年 3 月,《晚点 LatePost》通过邮件对话了阿克曼。他认为,“《俄罗斯方块》很可能是世界上最伟大的电子游戏。”因为它吸引了那些从不认为自己是游戏玩家的人,适合从妈妈们到数学家的所有人。它还是严格执行极简主义设计的典范,几乎可以在任何科技设备上运行,从手机、笔记本电脑、VR 头盔到游戏家用机、游戏掌机。这表明它可以不断发展,又不失其最初成功的最基本要素。在未来许多年,任何新设备或平台几乎都能立即获得《俄罗斯方块》的版本。
“一款以简单的方块图形和物理原理为基础,没有故事情节、人物或世界构建的游戏,在这么多年后依然能让我们着迷,这真是令人惊叹。它是我能想到的拥有超越语言和文化障碍的纯游戏元素的最佳范例,这也是它持续流行的原因之一。”阿克曼对《晚点 LatePost》说。
他觉得《俄罗斯方块》的故事本质上是一个科技创业故事,和 Facebook 没什么大的不同。但它的发生背景在 1980 年代的苏联,而非硅谷。
虽然几乎任何人都能玩《俄罗斯方块》,但只有少数人精通。它不仅是游戏,也是无法破解的密码拼图。它是一个独特的例子,一个想法、产品和时代在恰当的时刻汇聚在一起。
令人上瘾的四连方块
1984 年,29 岁的程序员帕基特诺夫在莫斯科一家玩具店看到童年熟悉的几何拼图游戏 “五连方块”(pentominoes)。他将其带回了工作单位苏联科学院,玩得乐此不疲。
“五连方块”共有 12 种形状的“方块”,如直线、T 形、L 形,每个“方块”由 5 个等大的正方形组成。玩家要利用这些零散的“五连方块”,拼成一个标准的长方形。他突然想到,或许可以基于类似思路开发一款电脑游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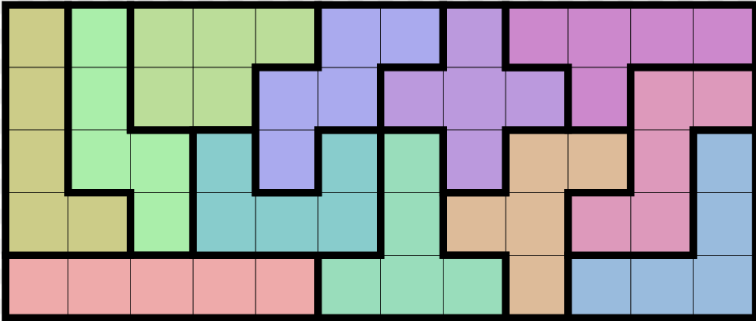
一种 “五连方块” 的组合。
帕基特诺夫当时使用的电脑是苏联产的 Electronica 60,笨重、过时,甚至赶不上 1980 年代初美国中学生在机房使用的电脑。由于 Electronica 60 没有图形功能,他就用键盘上的数字、字母、标点符号(主要是 “方括号 [ ]”)组合替代。
他先把“五连方块”简化为“四连方块”,12 种形状的“方块”随之变成 7 种形状。游戏过程设计为电脑不断随机生成一种形状的方块,方块下落,玩家必须迅速做出决定,赶在方块到达屏幕底部前旋转、移动方块,让它们互相拼接。随着游戏进行,方块下落的速度会越来越快。当方块堆积到屏幕顶端时,游戏结束。
为了增加玩家的紧张和竞争感,让他们集中注意力快速操作,帕基特诺夫将游戏区域创新地缩小成一个狭窄通道。但游戏几十秒或者几分钟就结束,也不太让人有重玩的欲望。他继续做了一项简单而重要的改进:如果方块之间紧密拼成一行,这一行就会被自动消除。
这项改进被看作《俄罗斯方块》让人“上瘾”的关键。“消除”能带来及时的正反馈,刺激人分泌多巴胺,让人获得满足和愉悦感。在短时间内,玩家不断追求“消除”,也就是不断追求“快乐”,形成无数个循环,从而“上瘾”。“消除”这一上瘾机制直接影响了后来如《宝石迷阵》《糖果传奇》《开心消消乐》等游戏。
下落方块和玩家操作的“对决”让帕基特诺夫想起了“网球”,所以他将游戏命名为 Tetris。因为在俄语中,Тетрис(Tetris)很像 Теннис(网球)。前缀 “tetra” 源自希腊语中的 “四”,也符合 “四连方块” 的含义。但中文将这款游戏译作《俄罗斯方块》,这名称带有其在欧美营销策略的印记。
早期的《俄罗斯方块》基本成型,它利用极简设计,让不同地区的玩家不需任何说明,都能立即明白游戏的特点和规则,触发了儿童将积木越堆越高的相似本能。但它没有图像、色彩、声音、背景、情节,显然欠缺一些吸引力。更重要的是,世界上没多少人使用 Electronica 60 的系统。
16 岁的高中生格拉西莫夫在计算机方面天赋异禀,自学了 DOS 操作系统编程等。在他的编写下,《俄罗斯方块》有了兼容 IBM 电脑系统的彩色版。帕基特诺夫的好友帕夫诺夫斯基还引入了游戏结束后显示的高分榜,增加了游戏的竞争和趣味性。三个程序员经过不断讨论、调试和更新,推出了最早病毒式传播的《俄罗斯方块》版本。
“我们那时候还没有版权法,而且根据当时的法律精神,我们无权向任何人出售任何东西,严禁谋取私利。”帕基特诺夫回忆道。所以他们将游戏程序复制到软盘,免费分发给苏联科学院计算机中心的同事和好友。
很多同事沉迷其中,称赞他们开发了如此出色的游戏。帕基特诺夫的好友、莫斯科第一医科大学的心理学研究员波基尔科也拿到了游戏。他最初感到兴奋,立马和同事分享,但很快发现他们的工作效率因此急剧下滑。有天下班后,波基尔科趁大家不在,挨桌搜寻游戏磁盘,全部没收销毁。
《俄罗斯方块效应》作者阿克曼分析了这种病毒式传播机制。他认为,过去 30 多年,独立艺术家或者小公司创作的作品在分发方式上几乎没什么变化,主要是免费分发。但现代的变化是采用了“免费增值”的模式,即免费提供基本版本,付费解锁额外功能。比如《俄罗斯方块》这样的游戏可以限制玩家玩到一定关卡或者时间,必须付费才能解锁。
不过当时帕基特诺夫既不能“谋取私利”,也没有现代支付技术等等的支持,他唯一的选择就是纯免费提供。
“当你免费提供一种令人上瘾的东西时,总有可能失控地传播,就像野火一样。”阿克曼评论道。
而且在早期电脑和苏联时代,他们采用的是 “人工传递网络”(Sneakernet)传播。人们自发地将实体软盘交给对方,绕过了当局的审查与注意。
《俄罗斯方块》这把野火迅速烧遍了莫斯科电脑界,还传到了匈牙利布达佩斯 SZKI 计算机科学研究所。冷战期间,匈牙利扮演了欧美阵营和苏东集团之间的桥梁。它是苏东集团中较早尝试经济改革和政治自由化的地区之一。匈牙利建筑师鲁比克发明的玩具“魔方”通过授权给美国公司生产,风靡世界。他也在 1980 年代成为社会主义国家第一个百万富翁。
在 1956 年,罗伯特·施泰因(Robert Stein)从匈牙利来到英国。到了 1980 年代,他在伦敦创办了仙女座软件公司(Andromeda),从事中介业务——施泰因利用自己匈牙利裔的优势,从苏东集团发掘可以贩卖到欧美阵营的软件,从中抽取大约 25% 的收入。
1986 年 6 月,施泰因又来到 SZKI 计算机科学研究所“寻宝”,注意到电脑上的《俄罗斯方块》。他坐下来,试玩了一下,结果根本停不下来。“既然像我这样不玩游戏的人都喜欢它,这款游戏肯定相当不错。”施泰因说。他向研究所的人询问游戏来源,对方告诉他来自苏联科学院计算机中心的一位朋友。
回到伦敦后,施泰因向苏联科学院计算机中心发了一封电报,表达购买《俄罗斯方块》国际版权的意愿。这对苏联人是新鲜事。帕基特诺夫在获得计算机中心几位主管的签字和科学院六七位领导的批准后,简短答复称:“好的,我们很感兴趣,也想完成交易。”
施泰因和苏联人的洽谈开始,这也是《俄罗斯方块》踏上全球传播的开始。当年 10 月,戈尔巴乔夫和里根在冰岛首都雷克雅未克举行历史性的见面峰会,冷战有了解冻迹象。欧美商人看到了机会,觉得《俄罗斯方块》是第一款来自铁幕之后的游戏,要包装它的异国情调,强调其苏联色彩。
太好玩了,这游戏是不是一个阴谋?
1987 年 6 月,在只达成意向、未与苏联人签约的情况下,斯泰因将《俄罗斯方块》个人电脑版的版权转售给了英国的镜像软件公司(Mirrorsoft)和美国的全谱字节公司(Spectrum Holobyte)。这两家公司同属罗伯特·马克斯韦尔(Robert Maxwell)的通信公司。
全谱字节打造了苏联风情的《俄罗斯方块》。他们首次给游戏添加了俄罗斯民歌《货郎》(另一曲知名的是任天堂添加的柴可夫斯基的《胡桃夹子》),还把游戏装在红色盒子里。盒子封面是标志性的圣瓦西里主教座堂,并用斯拉夫语写了游戏名,最后一个字母借用锤子和镰刀的形状。
游戏区域外空出的两边被各种苏联元素填充,包括列宁体育场、摩尔曼斯克的核潜艇基地、红场上的“五一”庆祝活动、苏联宇航员在空间站俯瞰地球。
他们邀请了一位苏联大使参加游戏的发布会,雇佣了里根和戈尔巴乔夫的模仿者陪同人们参加行业展览会。在没有互联网营销、云端下载游戏的时代,花哨吸睛的包装与宣传才能让玩家在实体商店驻足和购买游戏。《俄罗斯方块》就这样存储在大号纸盒里的小小软盘上,被称作“来自苏联的礼物”。一些版本还贴心增加了方便“摸鱼”但不被发现的“老板键”。
1988 年 1 月,《俄罗斯方块》的个人电脑版在欧美正式发售,一下引爆了市场。不太为游戏专题撰文的主流媒体也刊发了文章,比如《纽约时报》报道了游戏的苏联来源,称它是首个在美国销售的苏联电脑软件,游戏简单且令人上瘾;《芝加哥论坛报》宣布戈尔巴乔夫倡导的 “公开性” 原则进入了电脑游戏领域。《俄罗斯方块》如此出色,你无法对它说不。
甚至有报道称:“《俄罗斯方块》非常简单易学。你打开盒子五分钟后,就能掌握所有规则。但它又是如此让人着迷。你一旦开始玩,就会在电脑屏幕前待上好几个小时,以至于你会开始怀疑《俄罗斯方块》是不是邪恶帝国为了降低美国人生产力而策划的一个阴谋?”
阿克曼解释,一般而言,如果一款游戏在主流媒体中获得好评,并不意味着它在专业媒体也会受到好评。
《俄罗斯方块》是个例外,游戏媒体给予了热烈欢迎。比如《计算!》(Compute! )杂志称它是 “柏林墙一边最令人上瘾的电脑游戏”,并提醒读者,“如果你还有工作要做或者有约会要赶,那就不要开始玩《俄罗斯方块》”。
1988 年 5 月,施泰因终于和苏联软硬件出口部(Electronorgtechnica,简称 Elorg)签署个人电脑版的授权协议。他的野心扩展到拿下街机和掌机的授权,但谈判并不顺利。苏联人觉得之前电脑版的分成,自己一分钱都还没收到,没解决这个问题之前,不会考虑新的授权。
和施泰因在电脑版的“先斩后奏”类似,在未正式与苏联人签约的前提下,镜像软件将街机和家用机的美国和日本版权卖给了雅达利(Atari)。雅达利准备用子公司天元(Tengen)在美国发行街机和家用机版的《俄罗斯方块》,并将日本的街机版权卖给了世嘉(SEGA)、日本的家用机版权卖给了防弹软件(Bullet-Proof Software)的罗杰斯。罗杰斯还向全谱字节购买了日本的《俄罗斯方块》电脑版权。
如果街机和掌机的授权过程和电脑一样,也许《俄罗斯方块》最后只是一款成功的视频游戏,并不会迈入有史以来最畅销和最伟大的视频游戏之列。改变这一切的是具有创业气质的罗杰斯,以及雅达利当时在美国的对手——任天堂(Nintendo)。
阿克曼之所以觉得《俄罗斯方块》的故事本质上是一个科技创业故事,是因为这是一个精通技术的人有创造新事物的动力,并在短时间用原始设备创造出了 “病毒式传播”(那时人们还不知道这个词)的东西。此外,项目的创意、技术和创业潜力之间存在直接的紧张关系。“这是任何初创公司创始人都必须面对的问题。” 他对“晚点 LatePost”解释。
“即使在不同的时代,在不同的经济和政治体制下,一些人仍然有创造和利用技术的动力,并广泛分享他们的成果。”
罗杰斯是其中的创业者。他在软件业的第一桶金是借鉴自己在美国玩《龙与地下城》等角色扮演游戏(RPG)的经验,开发了日本第一款 RPG 游戏《黑玛瑙》(The Black Onyx)。在软银(SoftBank)的帮助下,《黑玛瑙》在日本取得成功。这对一个外国人来说并不容易。他是有着印尼血统的荷兰人,后移民到美国读书,23 岁时搬到日本。
罗杰斯的雄心不止于此,他想为任天堂开发游戏。在一本杂志上读到任天堂社长山内溥是围棋爱好者后,他给山内溥发了一份传真,提议为任天堂开发一款围棋游戏。两人见面,以 3000 万日元(当时约为 30 万美元)的价格在几分钟内谈妥交易。他从一个小有名气的电脑游戏开发者摇身一变为全球最大视频游戏公司的授权发行商。
阿克曼称罗杰斯为“软件人类学家”,觉得他善于通过国际视角看待游戏,并找出哪些概念能够跨越文化和语言的障碍,形成一种独特的商业模式。
1988 年 1 月,罗杰斯在美国拉斯维加斯的消费电子展(CES)上一个排队长龙中发现了电脑版的《俄罗斯方块》,彻底着迷。他努力获得了日本的电脑和家用机版权,卖了超过 200 万份。此时,任天堂革命性的产品 Game Boy 也研发成功。
因为和任天堂的良好关系,罗杰斯提前看到了 Game Boy 的样机。他初看觉得是口袋计算器,惊讶于掌上游戏机的创新设计——机身小巧便携,游戏屏幕缩小,显示不用彩色而用单色,供电只需四节电池,没有任何多余之物。硬件 Game Boy 设计的极简风格和软件《俄罗斯方块》的极简设计完美契合。
罗杰斯告诉荒川实(任天堂美国分公司总裁、山内溥的女婿),任天堂应该将《俄罗斯方块》变成 Game Boy 的内置游戏。内置游戏的商业模式就像剃须刀附带刀片一样,让人们尝试后,再购买更多商品。荒川实本来考虑的内置游戏是《超级马里奥兄弟》,罗杰斯劝说道:“如果你希望只有男孩们购买 Game Boy,那就内置《超级马里奥兄弟》,但如果你希望所有人都玩 Game Boy,那《俄罗斯方块》就是完美的内置游戏。”
Game Boy 打入全新广大群体的诱惑太大了,荒川实承诺,只要罗杰斯拿到《俄罗斯方块》的掌机版权,任天堂就愿意从他手中购买。
“见过罗杰斯的人都知道,他是那种能在暴风雨中找到正确道路的人”,任天堂的法律顾问霍华德·林肯说,“告诉他我们愿意向他购买代理权,无异于在饥饿的狮子面前抛出鲜肉。”
一场跨国版权争夺战
从 1988 年底到 1989 年初,罗杰斯通过数次传真、信件、电话等方式联系施泰因,希望获得《俄罗斯方块》的掌机版权。但施泰因含糊其辞,推脱说后面联系。罗杰斯明白,想要拿到版权,得自己去莫斯科谈判。
因为街机的版权交易已经发生,但施泰因还未与苏联人签订条约。加上罗杰斯的施压,他感到焦虑,必须前往莫斯科。罗伯特·麦克斯韦尔的儿子凯文这时也去了莫斯科。他是售出街机和家用机版权的镜像软件公司的老板,想绕过中间商施泰因,直接解决授权问题。
1989 年 2 月,寒冬,罗杰斯、施泰因、凯文在不知道对方的情况下,几乎同时来到莫斯科展开了一场版权争夺战。
施泰因和凯文由于和苏联的过往联系,顺利接触到了谈判方——苏联软硬件出口部(Elorg)。罗杰斯是个持旅游签证的 “非法” 闯入者,并不熟悉苏联,但他有自己的办法。不会俄语的他通过寻找莫斯科围棋玩家聚集的地点,和当地人比赛交友。在棋友的帮助下,罗杰斯找到一个非正式的口译和导游帮忙。
在苏联,私自为外国人做导游是一件会被官方注意的事情。导游非常小心谨慎,也告诉罗杰斯,如果没有受邀,苏联人和外国人都不能去苏联政府机构,何况他持的还是旅游签证。但这拦不住“饥饿的狮子”,罗杰斯冒险进入了政府大楼,遇到第一个看起来像官员的人,立马说:“我想找人谈谈俄罗斯方块。”
阿克曼和美国作家戴维·谢弗(David Sheff)都在书中详细还原了罗杰斯、施泰因、凯文和 Elorg 主任别利科夫(Nikoli Belikov)的谈判过程。
罗杰斯和别利科夫签约《俄罗斯方块》掌机版的授权协议后,在喜悦的气氛中,他拿出了一盒自己代理、在日本出售的家用机版《俄罗斯方块》的卡带,自豪地递给众人。但在场的苏联人全都露出震惊的表情。
双方对了信息,罗杰斯发现自己买的日本家用机版权是假的,别利科夫则发现,除了家用机,连街机的版权都已经开始售卖。他们都被骗了。
第二天,罗杰斯表示愿意为 13 万盒游戏卡带再次付费,当场开出一张 40712 美元的支票。这也是 Elorg 第一次获得分成收入。罗杰斯获得了苏联人的信任,并为别利科夫科普游戏的版权交易常识,还帮忙审阅了 Elorg 与施泰因的合同与往来文件。
在知道施泰因骗了他后,别利科夫并未打草惊蛇,而是拟了一个补充协议让施泰因签署,称这是他和施泰因谈论其他版权的前提。在这份补充协议中,Elorg 定义了之前授权给施泰因的电脑版权中的 “电脑”——由处理器、显示器、磁盘驱动器、键盘和操作系统组成的个人计算机。这其实是在补充说明家用机不是协议定义中的“电脑”。
但施泰因没有发现这点,误以为补充协议的关键是苏联人一直抱怨他付款不够及时,所以增加了延期支付许可费用的滞纳金。施泰因于是签署了补充协议,然后他被告知掌机版权已经售出,街机版权的预付金比之前沟通的涨了几倍,变成 15 万美元。虽有不快,但他知道还能赚不少,飞快签署了街机的授权协议。
别利科夫和凯文的会面短暂而有趣。他拿出之前罗杰斯展示的那份游戏卡带问凯文:“您知道这是什么吗?”凯文说这肯定是盗版游戏,镜像软件没有《俄罗斯方块》的家用机版权。这实际上变相承认镜像软件之前违规向雅达利出售了家用机版权。他们也没什么好继续谈的了。
罗杰斯告诉了荒川实谈判结果,他拿到了掌机的版权,苏联人也没有出售家用机版权,并想卖给任天堂。荒川实感到兴奋,他和林肯准备来莫斯科签署协议。两人为了不让对手雅达利察觉自己去苏联,先从西雅图飞到洛杉矶,再赶到华盛顿的苏联领事馆获取签证。拿到签证后,他们飞往伦敦,再乘坐下一班飞机来到莫斯科。
任天堂和 Elorg 正式签署了家用机的授权协议,预付金数额保密,据传有 500 万美元。这款协议也帮助任天堂彻底击败了雅达利。当时,雅达利已经投入数百万美元到家用机版的《俄罗斯方块》,发货量已有 10 万盒。当法院判决雅达利侵权的销售禁令一出,也意味着这家公司的投入全部付之东流。
“授权”给雅达利的马克斯韦尔没有认输,他开始寻求政治帮助以扭转局面。马克斯韦尔的影响力类似现在的鲁珀特·默多克。他当时建立了一个世界级的媒体帝国,在英国、中国、苏联和巴西等国成立众多通信公司,涵盖新闻、图书、软件等出版业务。他不仅是一名媒体大亨,也有着巨大的政治影响力。
谢弗在《游戏结束:任天堂全球征服史》中称,马克斯韦尔是以色列和加拿大领导人信赖的顾问,也是反对英国保守党政府的中坚力量。他深受戈尔巴乔夫的信任,认识勃列日涅夫、安德罗波夫、葛罗米柯、赫鲁晓夫等四位苏联前任领导人,还为他们出版了书籍。马克斯韦尔能使用九国语言,总是频繁接到各国领导人的电话。当秘书说有总理来电时,他还要问一句:“是哪一位?”
马克斯韦尔联系了英国和苏联政府的朋友,向 Elorg 施压。别利科夫称自己受到冲击,处于被人监视之中。马克斯韦尔也的确见到了戈尔巴乔夫,谈及了《俄罗斯方块》的版权问题,但戈尔巴乔夫只是口头上表示关注此事,告诉他,“不必担心那家日本公司”。
实际上,《俄罗斯方块》的版权争夺战宣告落幕,罗杰斯和任天堂成为最大赢家。1989 年 7 月,任天堂在美国推出了家用机版的《俄罗斯方块》,立马销售了 300 万份。当月,内置《俄罗斯方块》的 Game Boy 也开始发售,最终在全球销售了 1.2 亿台,女性玩家约占一半。当然,无法统计的是那些仿制 Game Boy 的游戏机数量,许多中国人童年使用的正是这类游戏机。保守估计,《俄罗斯方块》至少为任天堂带来数十亿美元的收益,罗杰斯从中至少赚了三四千万美元。
相比之下,游戏的创造者帕基特诺夫当时从《俄罗斯方块》中没有获得什么收益,最多涨了点工资、领了点奖金,远远比不上像宫本茂开发《超级马里奥兄弟》《塞尔达传说》的所得,但他成为了苏联最有名的程序员,也为全世界喜爱他的游戏感到开心。
施泰因和马克斯韦尔都是熟悉苏联的西方商人,理应更有资格成为商业上的赢家。但他们都太自信自己对苏联的了解,所以敢于在未正式签约的情况下,就开始版权转卖。即使出了问题,想到的也是通过政治关系解决,并没有按商业逻辑行事。
罗杰斯则像一个 “愣头青”,热爱游戏,就真诚地建立人际关系,没有太多意识形态偏见,正直地按照市场方式谈判交易。他也是当时来争夺版权的西方商人中,唯一一个和游戏发明者帕基特诺夫建立友情的人。
帕基特诺夫在谈判桌上观察到,开发过游戏的罗杰斯真正懂游戏、喜欢游戏。他邀请罗杰斯来家中做客,罗杰斯也邀请他来自己的旅馆。他和罗杰斯、荒川实和林肯一同去一家日本料理吃饭、喝酒,第一次吃芥末的他被辣出了眼泪。
1991 年 12 月,苏联解体,被国有化的《俄罗斯方块》像这个国家的许多资产一样,开始被变卖和私有化。控制它知识产权的 Elorg 被别利科夫变成民营企业。
1995 年底,帕吉特诺夫最初签署的十年协议终于到期,在罗杰斯的帮助下,他收回了游戏的部分权利。两人一起成立了俄罗斯方块公司,并在 2005 年购买了 Elorg。至此,他们终于能充分拥有和管理这款游戏,分享游戏的财务成功。
“俄罗斯方块大脑”
《俄罗斯方块》之所以能成为一款伟大的视频游戏,不仅在于它在产品和商业上的成功,也来自它在社会和文化上的影响力和丰富性。
1994 年 5 月,自由撰稿人杰弗里·戈德史密斯(Jeffrey Goldsmith)在《连线》杂志发表文章《这是你的俄罗斯方块大脑》(This is Your Brain on Tetris)。
文章源自他在 1990 年因为玩《俄罗斯方块》失去 6 个星期的经历。除了吃饭和买电池需要外出,他几乎都在房间里玩游戏。当他去便利店时,会先拿一些零食到收银台,最后一刻才装作漫不经心地扔一包电池,尽管他去店里的真正原因是为 Game Boy 补充电源。
戈德史密斯发现,当他白天外出散步时,大脑会将汽车、树木和人像游戏里那样拼在一起。晚上睡觉时,他能看到方块从黑暗中落下。他意识到,游戏已经改变了他的大脑,改变了他对现实的感知。戈德史密斯将其称为“俄罗斯方块效应”(Tetris effect),并反思这种让人成瘾的游戏可能是一种“电子药物”(pharmatronic)。
虽然戈德史密斯不是第一个严肃讨论《俄罗斯方块》成瘾问题的人,但他的文章引发了后续许多研究者的兴趣,探究这款游戏对人大脑的影响。
比如有研究者分析,因为《俄罗斯方块》能够影响人的程序记忆(频繁、重复的动作)和空间记忆(处理二维、三维形状及其相互作用),所以会改变大脑的认知。这种改变可以是坏的。

丹·阿克曼的《俄罗斯方块效应》(The Tetris Effect)和戴维·谢弗的《游戏结束:任天堂全球征服史》。
除了游戏,社交媒体成瘾在现代也成为一个问题,但它们和《俄罗斯方块》的成瘾机制类似,都是在利用人们追求新鲜和奖赏的多巴胺,形成循环。例如,微信或 Facebook 的每一个“赞”、微博或 X 的每一次刷新或“转赞评”、《俄罗斯方块》的每一次“消除”,都是刺激用户分泌多巴胺的一次回路。
但当人们将罪责归于技术本身时,一些学者强调人应该“驯化”技术,理解成瘾的机制,警惕公司的动机,从而摆脱对技术的成瘾。有研究者发现,《俄罗斯方块》对大脑的改变也可以是正向的。一些高手玩家分享称,玩时有进入“冥想”或者“心流”的效果。
1992 年,美国加州大学医学院教授理查德·海尔(Richard Haier)通过实验证明,人在玩《俄罗斯方块》之后,大脑某些部位增厚、活动下降,表明游戏让人的大脑建立了新的神经连结,运作更为高效,耗能减少。海尔将其称为“俄罗斯方块的学习效应”。学习效应揭示了人类大脑的可塑性,有研究者从这一角度出发,还发现了《俄罗斯方块》治疗精神疾病的功效。
2010 年,英国牛津大学神经科学教授艾米丽·霍姆斯(Emily Holmes)的团队研究发现,《俄罗斯方块》可以让人最初的创伤记忆免于凝固。游戏吸收了原本要将可怕记忆转为长期记忆的精神关注度,可怕的记忆存储不完全,甚或完全不曾存储下来。他们认为,游戏充当了“认知疫苗”(cognitive vaccine),可以用于治疗出现闪回的“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
即时正反馈回路之外,纽约大学的亚当·阿尔特(Adam Alter)分析了《俄罗斯方块》另一种上瘾机制。他认为,人类无法抵挡介乎于“太容易”和“太困难”之间的甜蜜区。“合适的”挑战带来的艰辛,远比知道自己铁定成功更吸引人。这种艰辛感是许多上瘾体验的必要成分。
谢弗对此有个总结:“完美的游戏是逻辑与人性结合后的绝妙产物——既蕴含逻辑和数学,也有心理和情感。一流的游戏既是挑战,也是奖励,还能给人带来特定的感官体验:探索与认知,挫折与成就。”
这引发出另一个问题,“你能在《俄罗斯方块》中‘赢’吗?”或者说,“如果游戏以恒定速度进行,是否存在一种获胜策略,使得完美玩家可以无限玩下去?”上述两个问题都是数学教授在论文中讨论过的难题。
2002 年,三位麻省理工学院的学者基本解决了这个问题。他们证明,《俄罗斯方块》是数学上描述复杂度的“NP 完全”问题。也就是说,人类无法找到游戏的完美解法,因为太复杂了,算出答案的时间要比人类历史还长。类似的,《扫雷》游戏也是“NP 完全”问题。这种解法的丰富性某种程度上也带来了玩家大展身手的空间。
在 2011 年的纪录片《成序的狂喜:那些俄罗斯方块大师》中,每个大师玩家都有着自己达到高分,甚至“爆分”(游戏能显示的最高分 999999)的方式。比如有玩家可以在方块下落的最后一刻旋转,让它的形状完美滑入所需位置,还有的玩家靠着拇指的高速连按(hypertyping),能让下落速度越来越快的方块移动到合适位置。
在每届的“经典俄罗斯方块世界锦标赛”中,玩家们各自施展绝技。但按照一些学者的计算,如果玩的时间足够长(约 7 万个方块),你还是会输,因为游戏中的 Z 方块的出现决定了结局。不过数学计算和实际游戏不同,大部分人一般玩不到 7 万个方块,而且当通关到一定级别时,方块下落速度太快,人的手速往往跟不上,输掉游戏也是迟早的事。
最近几年,随着 AI 的发展,《俄罗斯方块》的完美解法似乎有了可能。2021 年,玩家们发明了一种叫“滚压”(rolling)的崭新手法,将《俄罗斯方块》的通关推到了新的高度。所谓滚压,指从传统的用手指按键变成像弹奏乐器一样敲击手柄,让按键反复触碰手指,从而实现高频操作。由于采用这种新手法,《俄罗斯方块》在诞生 40 年后,美国 13 岁的少年吉布森成为首位玩到游戏宕机、屏幕卡死的选手。
40 年的时间也让《俄罗斯方块》成了一种多元的流行文化和象征符号。
例如,2014 年俄罗斯索契冬季残奥会的闭幕式以“俄罗斯方块”为主题构建;《俄罗斯方块》被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MoMA)收藏,也被设计成许多公共艺术装置等等。
不少公司推出了类似产品。麦当劳就发布了一款可以玩《俄罗斯方块》的麦乐鸡形状掌机,孩之宝有一款以“俄罗斯方块”为主题的积木玩具“叠叠乐”(Jenga);去年,苹果推出了电影《俄罗斯方块》,但影片对苏联的描绘和历史真实相去甚远,比如克格勃、戈尔巴乔夫的情节。阿克曼还起诉了苹果和俄罗斯方块公司,称它们未经许可改编了自己的著作。
人们对《俄罗斯方块》的解读上升到了哲学层面。比如说这是一款“存在主义”游戏,虽然知道自己最后一定会输,但还是会努力且一直玩下去,就像推巨石的西西弗斯;《俄罗斯方块》告诉我们,获得的成功会消失,犯下的错误会累积,或者是错误越多,成就越少;《俄罗斯方块》还告诉我们,如果你合群,就会消失,但不合群的人多了,大家又会一起玩完。
帕基特诺夫曾这样解释这款游戏的魅力:“人类都有一种内在欲望,那就是‘从混沌中创造出秩序’。《俄罗斯方块》的系统虽然简单,但却能从根本上满足这种欲望。”
阿克曼的看法类似:“《俄罗斯方块》让无序变得有序。这就像人们每天都要对抗日常生活中从天而降、五彩斑斓的随机事件和无休止的琐事冲击。”
部分参考资料
1. The Tetris Effect: The Game That Hypnotized the World,Dan Ackerman 著,Public Affairs 2016 年 9 月版。
2.All Your Base Are Belong to Us: How Fifty Years of Videogames Conquered Pop Culture,Harold Goldberg 著,Crown 2011 年 4 月版。
3.《游戏结束:任天堂全球征服史》,戴维·谢弗 著,吕敏 译,读库·新星出版社 2020 年 1 月版。
4.《欲罢不能:刷屏时代如何摆脱行为上瘾》,亚当·奥尔特 著,闾佳 译,机械工业出版社 2018 年 4 月版。
5.《数字的秘密生活》,乔治·G. 斯皮罗 著,郭婷玮 译,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 2023 年 2 月版。
6.Exclusive Interview: The Tetris Effect Author Dan Ackerman
https://paulsemel.com/exclusive-interview-tetris-effect-author-dan-ackerman/
7.This is Your Brain on Tetris
https://www.wired.com/1994/05/tetris-2/
8.The 50 Best Video Games of All Time
https://time.com/4458554/best-video-games-all-time/
The 50 best video games of all time
https://www.digitaltrends.com/gaming/50-best-games-of-all-time/
9.The 10 Best-Selling Video Games of All Time
https://www.ign.com/articles/best-selling-video-games-of-all-time-grand-theft-auto-minecraft-tetris
10.纪录片《成序的狂喜:那些俄罗斯方块大师》(Ecstasy of Order: The Tetris Masters)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tX4y137NK/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晚点LatePost (ID:postlate),作者:曾梦龙,编辑:钱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