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扫码打开虎嗅APP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WeLens(ID:we-lens),作者:Lens,头图来自:视觉中国
如果你对网络上的言论表达略有关注,可能会注意到一个现象:大部分人说话越来越“简单一致”了。
似乎有点道理就叫“金句”,以爱国名义群起攻之就变“出征”,谈恋爱不欢而散也常会被叫“渣男/渣女”,扔出些“不中听”的观点就变“带路公知”,多谈论几本书几个乐队就是“文艺青年”。

一些本来需要仔细琢磨和分辨的场景,在“一顿操作猛如虎”的粗浅概括下,不仅变得令人疲惫或污名化,也失掉了它的最初含义和表达该有的分寸。
近日和一位出版界的朋友闲谈,她坦率地表达了对当下网络语言环境的担忧。首先就是“金句”这个词。
“金句这个概念很有意思,造得很合时宜。在碎片化的时代里,大家对‘金句’的需求激增。好书被肢解,任由扭曲,刚好够各种营销号写出一些‘假养料’,给到读者短暂的快感,慢慢就让人失去阅读长篇和看懂别人讲话的能力。”
这种只言片语的“聪明话”看多了,很难感受到好文字的骨血和脉搏。
但只要说得够多,“金句”就成了大家会脱口而出的概念。

还有“渣男”这个词,虽然常常听到,但它本身的概念界定却特别模糊。
他们的主要特质是情浅言深还是始乱终弃?是已婚已恋男明星和女性朋友共用吸管,还是家暴行为、屡次劈腿,甚至性侵?没个定论。
好像这些案例都可能被称为“渣男”,连有些男生加班没秒回、回家不洗碗,也要被骂“渣男”。
从语言学的角度来看,这种含糊的概括和不分场合的滥用,其实是应该谨慎一些的,因为滥用往往会造成词义的不合理扩大(有时会是缩小)。

它带来的后果就是,即便这个人已经达到了犯罪的程度,事情的严重性也会因为蒙着两性薄纱的“渣”而被迫模糊掉焦点,严肃的“法律问题”也可以变得“私密化”。
还有一些复杂的感情,又会被这些标签简单粗暴地遮盖了,浪费了我们去扩展自己理解的机会:很多时候,人都有可怜的、困扰的一面,包括我们自己。
至于“带节奏”“屁股歪”“双标狗”,或者是“种草”“拔草”“吃土”这种词就更不用说,这两年铺天盖地地出现,如果听多了用多了,于人的心智也是一种损耗。
出现这样的现象,说到底其实还是一种简单化的“贴标签”,是思维上的懒惰。

说起来,“贴标签”是难以避免的正常行为,它帮助我们在理解世界时删繁就简,节省大脑能量。但如果过于习惯这样做,时间久了大脑大概就要钝化了。
面对层出不穷的复杂事物,思维要是变得单一,世界就会变得“非黑即白”,所有事情都可能在以秒计数的时间里被“盖棺定论”。
这种思想层面的“盖章”,反过来也会围剿我们的生活。
当人掉进热衷盖章定性的“回声筒”里,就会喜欢拿着放大镜审视周遭,试图用自己立下的道德标准来衡量一切。
这种审视出现的范围可以非常广,它可能包括现实生活,也有可能是虚拟的文艺作品。
在我们平常的话语里,常常能听到对身边事诸如“三观尽毁”“人设崩塌”这样的评价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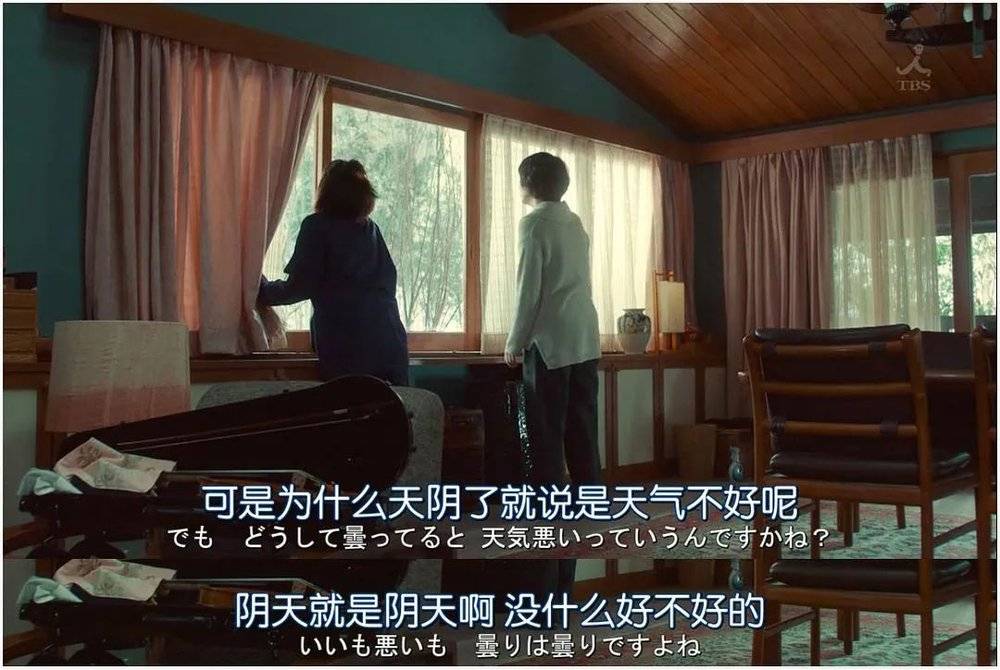
这个“三观尽毁”说得颇有点“居高临下”的意思,但本质不过是“跟自己的三观不同”罢了,“人设崩塌”听起来很灾难,但其实不过是简单思维对活生生个体的“完美假象”的扭曲渴求。
这样看来,12年前周慧敏关于倪震出轨的声明(因字数限制截取部分),几乎可以算得上“诠释复杂性”的典范:
我与倪震识于微时,一起共渡过不能尽算的高低起落,早已磨合了一套我们之间的相处艺术。一个人的问题,两个人去修正;一个人的挫败,两个人去承担。我俩是一个团队的,没分高低,输赢也是一体 。某程度上,周慧敏早已是一位不同面貌的倪震。任谁一方受到伤害,另一方都愿抵御百倍的痛。一起走过将近二十个年头,绝对不是在一般人的准则下相爱,但外人却总爱把自己的一套价值观去评价、批判属于我俩之间的爱情。
香港这片是非地,无风三尺浪,暗箭来自四方八面,行差踏错一步就如掉进斗兽场。当中我们需要的信心,包容,付出是一般情侣无法体会的。显微镜下看世界,任谁都难合格。
多谢各位。
“原谅与否”,这是当事人自己的事情,自与旁观者无关,这时候要是充满“立场感”地“站队”“表态”,反而挤占理性思考的空间。

王小波在《沉默的大多数》里说:
“我认为,在人类的一切智能活动里,没有比做价值判断更简单的事了。
假如你是只公兔子,就有做出价值判断的能力——大灰狼坏,母兔子好。然而兔子就不知道九九表。
此种事实说明,一些缺乏其他能力的人,为什么特别热爱价值的领域。
倘若对自己做价值判断,还要付出一些代价;对别人做价值判断,那就太简单、太舒服了。
讲出这样粗暴的话来,我的确感到羞愧,但我并不感到抱歉。因为这种人士带给我们的痛苦实在太多了。”
现实世界似乎是不够,于是这样的围剿延伸到了对文学作品的解读,甚至看教科书的眼光审视文艺作品,只可惜文艺作品从来就没有许下“正能量满满”的承诺。
《花样年华》作为屡屡登上电影评选前列的种子选手,其实讲的是一对双双被伴侣出轨的男女,合计对策,却也爱上彼此的故事。

片中男女主角出轨、吸烟一样不缺,但这并不影响作品的魅力。
《英国病人》曾经被英国布克奖(Booker Prize)评为“最伟大的小说”,但却在豆瓣上见到不少这样的评价。

我并不反对时刻想要看到“光明伟岸”的初衷,但是“不得见光”的东西,至少也得有存放之处,因为我们不仅需要给平淡生活一个出口,也要坦然反抗“美化现实”与“虚伪粉饰”。
如果一味地只给傻白甜的糖,捂住眼睛和耳朵,日后便再难打开那扇代表着创造里甚至是人生真相的天窗。
如果道德的枷锁时刻束缚着文学艺术,那艺术史上估计就得多不少的行尸走肉。

至于“教坏未成年”的论调,可以用心理研究学家布鲁诺·贝特莱姆的话来回答:
“这些对人造成‘冲击’的内容,有助于宣泄孩子的可怕冲动,让他们以极低的成本,提前进行一场社会演习。”
人性的灰色地带,即便多么反对,也至少应该允许它呈现形式上的存在。
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当时的英国社会形势动荡,有些人在交流的过程中呈现出一种不讲逻辑,甚至是反对逻辑反智的趋势。
哲学教授斯泰宾(Lizzie Susan Stebbing)写了《有效思维》一书,提到人们在思考时常会遇到内在与外在的干扰。

在公共的群众语言(mass language)里的空话、套话和陈词滥调被斯泰宾称为“罐头语言”,它在政治和商业场景中也经常会出现。
在复杂多变的事情面前,人们从现成语言中找到方便的解答,就会感觉到把握形势的力量。久而久之,很容易养成一种习惯,接受一些可以免除思虑之苦的简明论断。这就是“罐头思维”。
这种思维方式具体表现为“被一群人采用的一句话”(口号)和各种“听见别人说就跟着说的字眼”,它让人思想懒惰,先是不肯自行思考,慢慢就丧失了自行思考的能力。

斯泰宾说:“一种罐装的信念是方便的:说起来简单明了,有时还带三分俏皮,引人注意。”
但是文字的力量终究是强大的,当我们重复使用简单化的词语,就是大脑放弃思考、慢慢投降的过程。
历史上没有哪个时代的人们能像今天一样自由地交流,没有哪个时代的信息能像今天一样快速传播。但同时,也没有哪个时代的语言,像今天一样被滥用、被轻慢、被不加思考地复制。
当然,语言本身就是一个不断演变的交流工具,使用这种“简单化的字眼”并非罪恶。
但是,如果你每用一次这样的字眼,实际上就是在承认“对这个事物我没有能力认知其复杂与多样性,所以用这种方式”,每多用一次,就是助长公共话语和个人逻辑在智识上的堕落。
正如斯宾泰所言:“只有那些经过认真思考才得出的结论,并且认识到自己的结论与别人不一致的人,才能够容忍别人。容忍并不是冷漠,更不是无知。一个民主的民族极其需要清晰的思维,它没有由于无意识的偏见和茫然的无知而造成的曲解。”
否则,一个处于眼罩下的心灵,永远不可能自由。
主要参考资料:
https://book.douban.com/review/5102657/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WeLens(ID:we-lens),作者:Len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