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扫码打开虎嗅APP

从这个季度开始,除了延续既有的人物报道,虎嗅“新女性”栏目还将逐季设定特定话题,以该话题为索引,呈现多种场景下的女性自我发展与成长。
本季度话题关键词是“独自”。
第一篇,我们将视角投向那些从茫茫人群中“独自”站出,坦陈自己(曾)受到性侵或性骚扰的女性。
公开指控、甚至报警,这注定是一个“孤单”的举动。当她开腔,她将面临的是司法机构、舆论、亲友、陌生人全方位的检视,接近孤立、几近无援。
而这不会是某一个受害者的故事,这是全体女性有可能面对的困境。
它源于何处,怎么打破?
题图来自电影《不能说的夏天》剧照
虎嗅年轻组作品
作者 | 常芳菲

“我很希望让他(鲍毓明)自己意识到,他让我很痛苦,他毁了我一生。”
这是日前(4月16日)新京报报道中,李星星(化名)的公开回答。而面对指控,嫌疑人鲍毓明则坚称自己“很坦然”。
不仅当事双方各执一词,在不同媒体的报道中出现了各种版本的“李星星”——她可能是14岁受到侵犯的受害者;她又“像是向‘养父’寻求安全感的缺少关爱的少女”。这种截然不同的描述和对事实的判断在舆论场中引发了巨大争议。
几乎同一时间,Jingyao在明尼苏达波利斯法院对刘强东涉嫌强奸正式提起民事诉讼整整一年之后,据美国相关法院官网显示,4月6日,刘强东方面确认收到起诉书,并委托律师向法院提交出庭应诉的通知(Notice of Appearance)。
被告同是社会名流,控诉者背负巨大的压力,她希望社会能给出法律维度的答案,然而,推进同样艰难缓慢。
让人遗憾的是,不少人投向这些女性的眼神充满审视、揣测、甚至冷漠之意。“证词前后矛盾”、“一场精心策划的仙人跳”、“对方有权有势为什么选中普通女性”等等,每条来自虚拟世界的指摘背后,都是一个人真实的声音。
当被媒体问及有多少新闻用户会相信自己时,Jingyao曾无力地说:只有三种人会站在她这边——被性侵过的女性、女权主义者、认识她的人。“肯定没有30%,最多10%。”她说,“我一开始不想报警,因为我就知道会是这样的结果。人们看到我就会说‘她的故事太多漏洞了’。”
这并不是一个鲜见的局面。从站出来的一刻起,她们就不得不做好准备,独自和大多数人的审视和怀疑作战。
“我被雷劈了”——这是一个遭遇性侵女性的感受。雷劈与性侵表面的共同点:它们看上去都是小概率事件,能置人于死地,即便幸存也会留下可怖的伤疤。而这个近于本能的联想让人觉得不安的点在于:它对受害者有明确的道德指向——也就是说,她一定做错了什么,才会遭此厄运。
事实当然并非如此。

鲍毓明案引发争议后,微博一位女性网友@贴着创可贴的太史毛球,公开了自己隐藏的秘密——在她只有7岁时,17岁的表哥多次以游戏的名义性侵她。但在长达20年的时间里,她始终保持沉默。
在这条微博发出24小时之后,她收到了超过4万条私信,在这个树洞里,女孩和男孩敞开心扉,讲述自己遭受性侵的经历,而大部分施暴者都是熟人和长辈:
“我没有勇气把这件事告诉我妈,只能尽量避开和继父的一切接触,我太胆小了。这件事一直没敢告诉任何亲人,说实话我并不觉得他改过自新,只是因为我现在处于更强势的地位,才让他不敢招惹。”
“我虽然没有被毁掉一生,但是我特别想把他(继父)送进监狱,然后告诉他亲生女儿。”
“我知道我没有错,但我恶心我自己的身体。除了我和那个人,没有第三个人知道,我憋着这个秘密十多年,一直以为到死都不会说出来。”
这四万个受害者,在漫长的时间里,在没有人的角落中,永远记得,又永远沉默。
数据同样勾勒出令人心碎的图景。
在《耻痛与重塑:儿童期性侵犯受害者的自我保护因子提升》一文中称,研究表明,针对中国未成年人的性侵案件中,隐案比例高达1:7,也就是说,在7起案件中,只有其中1起正式进入了司法程序。且性侵案件逐渐呈现低龄化的趋势,受害者集中在7岁~14岁之间。
欧美也不例外。
面向英格兰和威尔士的“强奸危机”数据报告显示,年龄段在16岁~59岁的女性中,高达20%的女性遭受过不同程度、形式的性侵犯,而这85000人当中,只有15%的人选择向警方报案。
根据美国一项针对校园性侵案的调查显示,90%以上的受害者选择沉默。
在许多美国男性口中“已经失控”的#MeToo运动,直到2017年10月才引起大范围的注意。
而另一个可以用来对比的事实是,成为运动导火索的好莱坞大鳄哈维·韦恩斯坦已经用熟练的手段性侵超过30位女性,受害者名单中包括了安吉丽娜·朱莉、乌玛·瑟曼、伊娃·格林、格温妮丝·帕特洛。从他开始用各种手段围猎女性到被定三级强奸罪,监禁23年,正义迟到了超过40年。
直到2017年,这些在外界看来早已功成名就的女性,最常见的表态仍然是:如果有人愿意公开站出来,那我也可以。
这暗合了另一条时间线。我国首例因性侵而将教授和南昌大学同时告上法庭的案例同样发生在2017年。面对“首次”这样的字眼,当事人小柔(化名)说:我不喜欢媒体的这种表达。这种事(性侵)这么多,而我竟然是第一个起诉的,感觉好奇怪。
这似乎也反映了外界的疑问。大量受害者为什么不愿意站出来。
林奕含曾经在《房思琪的初恋乐园》给出过这样的回答:
我的孤独不是一个人的孤独,而是没有人的孤独。

站出来意味着什么?意味着要一个人同时面对司法机关、家人、朋友、陌生人、舆论全方位的严苛审视。
一项调查显示,阻碍受害女性报案的理由有三点,其中提及频率最高的是——畏惧他人知情。
你不必是一个完美的人,但受害者必须完美。
根据豆瓣网友“小波伏娃”总结的完美受害者规则,我尝试改写了一个性侵完美受害者的充要条件,具体如下:
1.性侵必须有足够的、多方面来源的证据支撑自己“被强迫”、“非自愿”,同时措辞严谨,逻辑清晰;
2.假设自己没有第一时间拼死抵抗,要有非常充分的理由解释;
3.没有可以被人肉出来的前科和不能见人的黑历史;
4.与施暴者不存在明显的权力不对等与社会地位落差(例如教师学生、导演演员、上司下属、普通人与上市公司高管的关系);
一旦受害者不符合这种假想,就会被认为是自找自愿的。而排名第二的理由正是“他人可能会认定案件发生是自己的错”。而事实上,这样的假想,无论从司法角度、权力结构都无法真实存在。
在法律维度上,性侵是否成立只需要证明两个问题:
1)是否发生过性行为;
2)是否为双方自愿;
然而由于过程的私密性,证明“非自愿”变得异常艰难。
当我咨询一位女性律师,是否只有存在挣扎的证据才能证明自己“非自愿”的时候,她的态度立刻暧昧起来:“法律层面上不能这样解读。因为鼓励拼死抵抗很可能会危及当事人的生命。但从取证的角度看,显然挣扎痕迹会让司法机关作出对受害者有利的判断。”
即便是鼓励反抗,对受害者来说都是相当困难的。
根据斯德哥尔摩强奸救助中心的调查,70%的强奸受害人在遭受性侵的过程中,会因为恐惧而导致身体无法动弹,无法表示拒绝,陷入一种解离状态,即紧张性强直静止(Tonic Immobility),通俗来说,受害者会陷入“假死”状态。
王尔德曾说,生活中的一切都是有关于性的,而只有性本身,关乎权力。
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和临床工作者指出,性侵犯是源于施暴者对于控制和支配的渴望。精神分析师 Yonack 认为,当弱势一方有所求,无论是工作、成绩、晋升的机会,能够帮助他实现这一切的另一方就拥有“权力”。而这方所实施的性侵就是“权势性侵”。
另一方面,施暴者的权力又会阻碍受害者在当下传递拒绝意图、事后提起诉讼。刚刚被判强奸罪名成立,入狱四年的台湾导演钮承泽,早在2007年就被传强迫演员柯奂如全裸拍摄床戏。
当年,柯奂如在Facebook里这样说:
因对方是导演,同时是男主角,当拍摄进行时,我感受到对方触碰令我不舒服之处,我是无法主动喊停的。
在现场,已无其他人权力在您之上。当您作为中间人的时候,我只能被迫接受这样的处理方式和您的道歉。
甚至有的时候,连受害者都不清楚自己是否“自愿”。说服自己主动“爱”,可能受害者唯一的出口。
前文提到对教授和南昌大学提起诉讼的案例中,受害者小柔(化名)也强迫自己爱上这位教授,也曾发送过表达爱意的信息。代理律师万淼焱曾说 ,“我们不得不承认像小柔这样遭受侵害后又强迫自己‘爱上’加害人,发送过表达爱意的信息并保持关系长达几个月,确实无法以强奸罪或猥亵罪追究加害人的刑事责任。”
林奕含在其长篇小说《房思琪的初恋乐园》里这么写道:“我想出唯一的解决之道。我不能只喜欢老师,我要爱上他。你爱的人要对你做什么都可以,不是吗?”
而最终,在林奕含自缢死亡113天后,台南地检署经过调查宣布不起诉陈星。因为即便根据心理谘商记录,也有前后矛盾的证据出现。林奕含曾说自己“被强迫”,同时也曾表明“就是一场恋爱”。
前后矛盾的证词、权力的不平等、没有激烈反抗和施暴者暴力胁迫的证据,性侵就很容易被外界解读成“各取所需的交易”。
“受害者原罪论”概念最早见于20世纪60年代,由梅尔文·勒纳提出。他称“这是为社会中的不平等和不公正现象在法律与道德上取得表面合理性而狡辩”。
那些倾向于审查受害者的人,对于世界绝对公平有一种病态的迷信,当它们对改变事实越无力,对受害者的责备就越无理。因为不能惩罚强者,就通过惩罚弱者来发泄自己的焦虑和恐惧。
“帕特洛还不是为了拿到角色”、“她都是看上了男方的地位与身份”,旁观者长出一口气——对他们来说,这个答案显然比这个世界就是有毫无理由的施暴者,令人安心。
受害者只会沦落到被怀疑、羞辱的境地,不得不和大众为敌,这让许多受害者宁可自认倒霉,也不愿意公开谈及这种伤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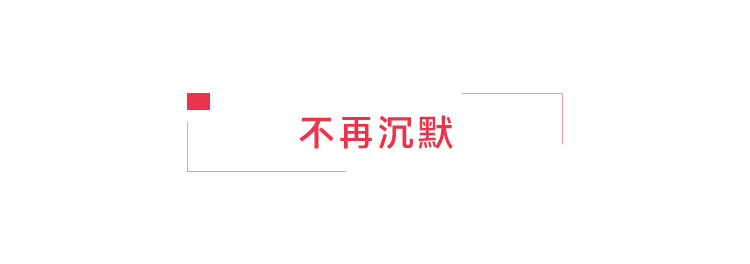
在整个社会的参与下,受害者的孤独循环正在形成:性侵犯会倾向于挑选经济地位弱势、父母关系不够紧密、落单的女性,而在施暴者得手后,对性的禁忌和外界的审视又令他们更加孤单。
而唯一能够打破这种循环的,就是法律和舆论的力量。
2008年,美国华府发生了一起“令人难以置信的强奸事件”——这正是2016年两家非营利新闻机构报道该案件的特写题目,该报道获得当年普利策奖。在这篇报道中,由于受害者拿不出更有力的证据和未成年人的身份,警察“相信这案子不值得浪费时间”,先是轻率地相信是她在编造谎言,并且起诉了她。
而对性的禁忌和羞耻,也为了让整件事快些过去,受害者最终更改了口供,承认自己虚假报案。得知这个消息之后,她的朋友们一个个打来了绝交电话。直到后续又有类似强奸案发生,两个女警察才最终艰难追查出罪犯。
7年之后,远在东亚的伊藤诗织,打破了东亚女性的沉默。
2015年4月3日,伊藤诗织与山口在东京寿司店共进晚餐,讨论赴美工作签证的问题。在伊藤喝过两合酒后,就感到头晕目眩,一进洗手间就跌坐在马桶盖上,失去意识。
随后,她被山口性侵。伊藤诗织决定报警。而接警的警员第一反应是:这种事太常见了,不好办。最后,其中一个警员问:“可能不太好回答,但......你是处女吗?”
2年之后,2017年5月29日,在父母的反对下,伊藤在东京地方法院二楼的会长召开媒体见面会。
然而这种挺身而出,带来了改变。
2017年年底,《纽约时报》以“She Broke Japan’s Silence on Rape”为题,大篇幅报道了伊藤诗织的故事。同年,日本修订了刑法。强奸的最低刑期由3年调整至5年。
2019年12月18日,日本东京地方法院最终作出裁决,认定性行为没有征得伊藤诗织的同意。四年之后,伊藤胜诉了。
而鲍毓明案中,李星星(化名)的控告最终能否得到法律层面的支持,目前看来仍是未知数。
我们所能确认的是,女性被性侵现象以各种形式广泛存在,而绝大多数受害者依然在沉默地忍受、甚至接受。
而只有广泛而持续的曝光,才能让侵犯者有所忌惮、有所收敛,才能让更多女性了解何谓好与正常的两性情爱关系,进而更好地保护自己。
那么,如何打破这条沉默的螺旋,让更多受害女性勇敢发声、让更多女性免受侮辱?
责任与权力在每位女性身上。
若你有被性侵经历,若你愿意(匿名)分享给我们,请扫描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在此收集,并将用适当的方式整理和公开。你的、ta的分享,一点一滴、交汇起来,可能会成为一道绳索,帮助别的女性在某个幽黯区域里,攀援而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