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扫码打开虎嗅APP

作者:贺雪峰(武汉大学社会学院院长,武汉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主任,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题图来自视觉中国
村庄是一个熟人社会,非亲即邻。村庄同时又是一个伦理共同体,是村民获得意义感的场所。村庄还是农民共同生产与生活的场所,是人情往来的单位。任何一个丧失生活自理能力老年人的悲惨处境都会在村庄引发舆论事件,引发心理反应。
在当前中国城市化背景下,在村庄生活的主要是老年人,村庄老年人主要有两种类型:
一是具有劳动能力的低龄老年人;
一是丧失生活自理能力的高龄老年人。
低龄老年人占到整个老年人群体的80%,丧失生活自理能力的高龄老年人占全村老年人的比例低于10%。
我们又知道,在当前农业机械化早已普及的情况下,有劳动能力的低龄老年人种自家承包地,每年农忙时间最多也就两三个月,有大量农闲时间,他们可能利用农闲时间到附近务工,或经营副业。
传统时期乃至进入21世纪之前的所有时期,总体来讲,村庄都是封闭的。
进入21世纪后,中国城市化加速,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大量进城,农村出现了普遍的“以代际分工为基础的半工半耕”家计模式,而且出现了进城务工经商农民年龄大了仍然要返回家乡种田的情况。
以农民家庭长期分离为特征的状态,使得传统时期以家庭为基础的养老难以维系。因此,在当前时期,推动农村互助养老就有了强烈需求,也有很大的可能性。
具体来讲,在一个有250名老年人的农村,如果有200名身体健康、具有劳动能力的低龄老年人,有15~20 名丧失生活自理能力的高龄老年人,则完全可能以村庄为单位,将低龄老年人组织起来为丧失生活自理能力的老年人提供基本照料,提供照料服务的低龄老年人可以获得一定的服务补贴,同时所提供服务的时间以“道德券”形式存入“时间银行”,待需要时可以将“道德券”从“时间银行”中提取出来获得相应照料。
被照料的高龄老年人的子女承担一定服务费用,国家给互助养老一定的资金补贴。
从而就可能在村庄形成多数低龄老年人照料少数高龄老年人,高龄老年人生活质量大幅度提高,而低龄老年人通过提供照料服务获得一定经济补偿和未来可用的“时间银行”道德券的双赢结果。
村庄社会互助养老关键在以下几点:
一、照料什么
对失去生活自理能力的高龄老人,首先是保证吃饭,一日三餐得有饭吃;其次是保证洗漱、卫生;三是精神照料。当然还可能需要医疗或其他更深度的照料,比如大小便失禁的情况。
重病、重残的照料如果依靠村庄养老互助很不现实。所以老年互助一般是轻度照料,主要包括送餐、清洁卫生、洗漱、精神陪伴。
二、在哪里照料
可以在高龄老年人家中,也可以集中在村庄人口聚居点作日间照料,甚至全天候照料。若有国家财政补贴或全额投资建设的村庄高龄老年人照料中心,一方面老年人自己组织养老互助,一方面国家给予补贴,是最好的。照料中心建设在村庄人口聚居点,若与村办幼儿园、村卫生室、村庄百货店、网购配送站建在一起,就更加便利。
第三,组织形式
老年人互助由老年人自愿组织,国家财政和乡村组织给予支持。老年人互助只有采取自愿组织的形式,才能最大限度调动农民自身的参与积极性,才能保证老年人互助的质量,也才能化解老年人互助中可能出现的风险和降低老年人互助的成本。国家和乡村组织支持老年人互助的形式有三种:一是财政补贴,二是具体指导,三是信用背书。
四、老年人互助经费的来源
收入主要有三部分:一是受到照料的老年人的家庭承担,这部分费用不高,占到全部费用的1/2左右。按一个行政村有250名老年人,有20 名常年住照料中心老年人计算,按现行标准,一个月1000元左右可以获得适当互助照料,合计收费24 万元。
二是财政补贴,大致占到整个互助照料经费的一半,即每个进入照料中心的老年人500元/ 月,一年大约补贴12万元。三是接受社会捐赠,尤其是本村乡贤的捐赠,预计每年获得捐赠12万元。三部分合计有48万元。
五、老年人互助经费的使用
老年人互助经费的使用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日常经费,其中主要是伙食、必要的日常开支,按每位老年人1000元/ 月,一年需要24万元;二是部分工作人员的照料补贴,比如有4位相对固定的低龄老年人负责照料中心日常工作,按每人2000元/月付酬,一年需要支付10万元工资;三是为义务参加老年互助的低龄老年人记分以外,支付少许补贴,比如500~1000元/ 月;四是其他开支。
六、老年人互助中的“时间银行”
凡村庄低龄老年人都可以义务加入到护理、照料高龄老年人的行列,每日照料护理工作记分形成“道德券”,累计起来成为年老失能后可以免费享受照料的“道德券”积分,这种“道德券”积分存入“时间银行”,由乡村组织进行信用背书。
时间银行的“道德券”积分不能兑换为现金,也不允许交易,只能用作未来接受照料时的免费凭证。老年人互助中,低龄老龄人参加照料,每月可以获得少许补贴。
七、鼓励大众参与
村庄所有超过55 岁的农民都可以参加到老年人互助社中来,互助社实行自治,由老年人自己组织起来,选举产生互助社社长、副社长,自主进行管理、民主决策。
乡村组织对老年互助社进行指导,国家对有效运转的互助社进行补贴。
在村庄熟人社会中,因为低龄老年人很多,他们既有全职在互助照料中心工作的积极性,又有义务提供照料的积极性。
在村庄熟人社会中,因为信息全透明,互助照料中就不会有为界定权责所进行的复杂制度设计,就可以做到低成本和低风险,在互助照料中就不会出现其他正规养老机构常有的道德风险。
以20名高龄失能老年人需要照料为例,我们来计算一下老年互助社的收支与“道德券”。
如前所述,每年的互助经费收入有48万元。现金支出中日常经费24万元,工资支出10万元,则结余为48-34=14万元。这14万元只用于支付参加老年互助社义务劳动的少许补贴和其他杂项开支。
假定照料20名高龄失能老年人,每天需要5 个低龄老年人参加义务照料,一年下来就需要365天×5 人/ 天=1825人。
按全村有200名健康低龄老年人来计算,每一年每个低龄老年人平均需要提供1825÷200=9.125 天。
就是说,只要每个低龄老年人每年参加9 天照料高龄老年人的义务劳动,就可以为互助社提供充沛的照料者。低龄老年人的义务劳动还会获得“道德券”和适当补贴。在农村闲暇时间很多的情况下,健康的低龄老年人提供义务劳动,应该是很轻松的事情。
村庄中建立老年人互助照料中心,生活不能自理老年人受到照料,在村庄熟人社会的生活就比较好。而低龄老年人有劳动能力,与土地结合起来,也几乎不用在国家财政支持的养老保障中生活。这样一来,农村老龄化问题就化解于无形。
顺便说一句,老龄化问题其实不是年龄问题而是制度问题。
当前中国实行男60岁、女55岁退休制度,所有正规就业退休以后就可以拿到退休金。一个社会中,拿退休金人口的比例越大,这个社会中拿工资人口的比例就会相对越少,劳动人口减少而消费人口增加,整个社会的活力就会下降。
尤其是中国这样未富先老的国家,随着老龄社会提前到来,劳动人口减少就往往很难为退休老年人提供可以体面生活的退休金。
实际上,当前中国有两个方面因素使中国可以避免老龄化问题,即虽然老龄化了却不是问题。
第一,随着中国饮食卫生条件和医疗条件的改善,中国超过60 岁的人口占比越来越大,同时,超过60岁的人口中身体仍然健康者也越来越多,这些身体健康的60 岁以上人口仍然可以是劳动力。
第二,中国农村家家户户都有承包地,有住房,有村庄熟人社会的归属。
超过60 岁在城市再找到就业机会相对较为困难,且城市生活成本也较高,一旦他们回到农村,与土地结合起来就可以继续作为劳动者参与劳动,就不需要依靠高额退休金也可以保障相对体面的生活。甚至劳动本身也使他们更有成就感,生活也更有意义、有乐趣。
反过来讲,正是农村这条退路,可以让农民与土地结合起来,使中国有了应对老龄化的最佳武器。
正视养老机构的困境体现在哪?
相对于基于村庄熟人社会的互助养老,正规养老机构具有高成本和高风险的弊病。
高风险就是正规养老机构必须要防范在照料老年人时出现的各种意外,从而必须建立各种设施,形成各种制度,以规避风险。于是,在养老机构与老年人以及老年人家属之间,就会形成复杂的博弈。
高成本是因为正规养老机构必须具备资质条件,以及必须有正式的护理员和管理机构。同时,要防范风险就一定要有更多保险资金的投入。
正规养老机构一般都是建立在非熟人社会中的,非熟人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就不能仅靠习惯、人情与信任,而要靠制度。完全靠收费营运的高风险和高成本的商业养老机构,农村失能老人完全不可能进入。
政府建立的农村福利院主要是照料农村“五保”老人。从我们调研来看,五保老人很少有愿意进入到脱离村庄的福利院生活的,原因是福利院没有自由,以及没有真正基于关心所提供的服务。
甚至当五保老人失去生活自理能力后,福利院的照料水平很低,虐待也很普遍,原因之一是福利院只有较少的护理人员,以及脱离了村庄熟人社会。国家为每位五保老人提供的保障经费有限,不可能通过正式渠道来雇请较多护理人员。
村庄熟人社会互助养老的好处是,因为有农村低龄老年人义务参加护理照料,而且村庄熟人社会中的信息对称,所以村庄养老成本低、效果好。
除了商业性的养老(基本上只能对应高收入群体),政府举办的福利院养老(基本上对应农村五保群体)、干休所(基本上对应军队干部)以外,中国养老主要靠家庭。在当前的城市化背景下,农民家庭客观上存在着普遍的家庭分离,家庭养老就面临着巨大挑战。
虽然仍然会有大部分农村老年人要依靠家庭养老,但同时也会有越来越多农村老年人难以获得有保障的家庭养老。因此,在中国农村建立互助养老制度就具有重大现实意义。
政府、社会、企业办养老,成本都会十分高昂,原因有二:
一是按市场价雇请护理人员,成本太高了;
二是养老过程中出现伤亡意外的风险太大。
武汉市新洲区有一个村集体办了一个失能老年人照料中心,有一次因为老人抽烟引发火灾,幸亏及时发现灭火了,没有造成伤亡。一旦出现伤亡,谁也担不了责。村支书受此事件惊吓,也不再敢办失能老年人照料中心了。
高成本与高风险决定了农村养老不能靠政府、社会和市场,也不能仅靠农民家庭,因为子女可能已经进城去了。
农民养老的办法是让农民互助,政府对农民互助及自治的老年人照料中心进行补助,这种补助不同于一般的“民办公助”,而是对互助的补助,对村庄低龄老年人照料高龄老年人的补助,对低龄老年人义务照料高龄老年人所获时间银行“道德券”积分的信用背书。
与互助养老同等重要并可以相互支持的一个农村老年人组织是老年人协会。
如前已述,在当前农业机械化已经普及的前提下,农村老年人种田,精耕细作,都可以种得好,且每年农忙时间很少,有大量农闲时间。农闲时间如何过得有质量、有文化、有意义,就成为决定农村老年人幸福指数高低的关键。决定农闲时间是否有质量的最基本方面是老年人能否组织起来,有集体的文化活动、社会活动。
从文化上和社会上将老年人组织起来,一个办法就是建老年人协会,由老年人协会来组织农村老年人,使他们“老有所乐”,并在此基础上“老有所为”,也可以与养老互助的“老有所养”形成相互支撑。
当前农村组织老年人协会有两个极好的条件:
一个就是农村老年人有大量闲暇时间,他们都很盼望闲暇时间能有高质量的文化生活;
二是农村有很多有闲暇时间的“负担不重的人”,这些“负担不重的人”因为子女在外工作有成就,或自己当过村干部,或见过大世面,而有很强的为村庄老年人提供服务的意愿与能力。
要将这两个条件结合起来,只需要一个很小的外在推动力量。
2012年以来,笔者在湖北省洪湖市和沙洋县四个村倡办老年人协会,为每个村每年仅提供5000元至1万元老年人协会活动经费,并为每个村老年人协会提供(建设)了一个140平 的老年活动中心。
结果,四个村老年人协会就一直运转良好,每一届老年人协会会长、副会长和常务理事都是无报酬的,村庄中却有很多“负担不重的人”愿意来竞争会长、副会长,他们最大的收获就是“老有所为”,为老年人服务,受到老年人尊重和村民敬重。
有了外力的推动,希望提高闲暇生活质量的“老有所乐”的老年人与希望通过为老年人提供服务而“老有所为”的负担不重的老年人如干柴烈火,一点就着,延续下来多年;老年人协会成为四个村老年人的组织,老年人从老年人协会组织的活动中提高了生活质量。有老年人总结了成立老年人协会之后的三个改变:时间过得快了,心情舒畅身体变好了,上吊自杀的老年人少了。
四个村老年人协会主要做了这样几件事情:
第一,除农忙以外,老年人活动中心每天都开门,日常活动主要是打牌、看电视戏曲、聊天;到老年人活动中心具体做什么倒是其次,关键是村庄老年人有了一个属于自己的随时去随时都很热闹的去处。
第二,主持重阳节、春节庆典。
第三,为高龄老年人祝寿庆生,为去世老年人开追悼会。
第四,维护老年人的基本权益,看望重病老年人。
第五,评选五好家庭、五好老人和五好儿媳。
第六,组织各种文体活动,尤其是主持诸如广场舞、腰鼓队等活动。
可以说,只用极少的投入与推动,四个村的老年人协会就都十分有效地运转起来了,成为村庄中最有活力的组织。
老年人协会主要是希望“老有所为”的老年精英,将有“老有所乐”需求的老年人组织起来,提高闲暇时间生活质量,增加村庄社会资本。在老年人协会基础上,再建立基于村庄熟人社会的养老互助社,就可以为农村失去生活自理能力的高龄老年人提供照料,让这些高龄老年人“老有所养”。
如此一来,中国农村就可以以很低成本让所有农村老年人有一个较为幸福的老年生活。
中国未富先老的国情决定了中国应对老龄化问题不能照搬照抄所谓发达国家的先进经验,而必须深入分析中国国情,找到适合中国实际的办法。
中国农村老龄化是中国老龄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农村最大国情就是,实行土地集体所有制,且中国是原住民社会,农民都有世代生活于其中的村庄熟人社会。土地集体所有制决定了所有中国农户家庭都有宅基地、住房,都有属于自己的承包地。
村庄熟人社会决定了农民回到村庄生活是有意义的,身体上、心理上都有安全感。
农民超过55岁,在大城市便很难再有就业获利机会,国家又很难提供进城农民在城市体面生活的养老保障,到了一定年龄,农民就退回村庄,与土地结合起来。他们可以从土地上获得收入,获得就业,获得与农时相一致的生活节奏,获得建立在农业生产基础上的熟人社会的社会关系。
他们大多数时候都在农村生活得很安逸,有大量的闲暇时间,可以通过老年人协会组织起来“老有所乐”,唯一让人担忧的是丧失生活自理能力。
不过,如果国家愿意倡办农村养老互助合作社,由村庄低龄老年人义务照料高龄老年人,就可以大大缓解失能老年人的困境,为所有人的“老有所养”提供保障。
如此一来,中国就可能建立起完全不同于基于正式制度的应对农村老龄化的有中国特色的互助养老制度,从而为中国缓解老龄化压力、增加经济发展活力、最终建成发达富裕的社会主义强国提供条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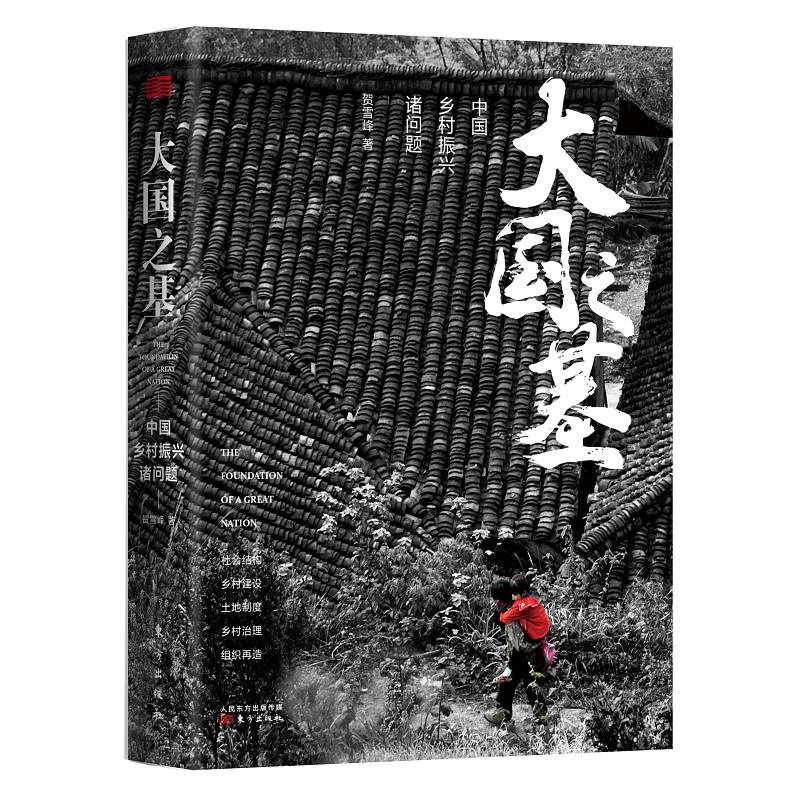
作者贺雪峰,现为武汉大学社会学院院长,武汉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主任,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主要从事乡村治理研究和乡村建设实践,长期坚持实地调研,学术研究上主张“田野的灵感、野性的思维、直白的文风”,在城乡治理、农业政策、农村经济、土地制度等研究领域发表了大量著述,是“华中乡土派”的代表人物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