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扫码打开虎嗅APP
首席科学家拍了下桌子,“你们就说想实现多少收入,这个指标我来扛。”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晚点LatePost(ID:postlate),作者:姚胤米,采访 :姚胤米、余洋洋,编辑:宋玮,题图来自:电影《好莱坞往事》
一、重新证明自己的价值
要学习和适应的东西真的很多——当一个科学家决定走进大公司、或是成为创业者时——这可不是换个名片title那么简单。
必须重新证明一件事情:你有什么价值?
2016年,阿里云杭州办公室,几位高层正在召开一场战略会,气氛并不怎么样,每个人音量都不小,且情绪分明:“你这个方案姿势就不对!”“这根本就不可放量!”“你是在瞎搞!”
已经记不得是第几次当面吵了。矛头的中心——阿里云机器智能首席科学家闵万里下定决心,定了定声,说:“你们就说想实现多少收入,我扛住这个指标。”
闵万里是数据科学家,曾经在IBM、Google就职。他博士毕业时就写出了受到学术界广泛认可的知名公式。但尝试用它帮一家公司赚到钱,还是第一次。
那原本是一个用于交通流量预测和优化的理论。闵万里的设想是,它可以在一些有大量数据积累的传统行业优化生产流程。他必须要证明自己的理论在实际场景中可以奏效。
第一个挑战是自己找客户。
杭州背靠江浙沪发达的制造业优势,有许多数据量大的头部工厂。闵万里和同事专门整理出一张列表,总共六七十家企业,他决定一一拜访,向他们销售自己的解决方案。第一个客户的名字现在仍然记得:江苏协鑫,一家光伏企业。
闵万里带着一位工程师一起赶往徐州。和这样一家公司谈判,他的经验值是零。同事介绍完他们的身份和来意后,轮到闵万里证明自己和团队的技术能力。他从电脑包里掏出一叠A4纸——是他最引以为傲的论文,里面有一大堆令人眼花缭乱的数学公式。
“我这个论文拿过很多奖,我们的技术很厉害。”一讲到公式和原理,闵万里就滔滔不绝。
对方听完。问:“你们是不是来偷数据的?”
列表上前四十几家公司,每一个都碰了壁。闵万里的团队当时只有6个人,每个都很沮丧——平时,大家都是天之骄子,突然摇身一变成了“求着别人的乙方”。印象最深的是,曾有位老总说话很不客气地说:“我们这行和你们互联网不一样,我们还是脚踏实地的。”
“言下之意,我们都是玩虚的。”闵万里说。
挫折感真的非常强烈。有人承受不住这种心理落差,选择离职。

(闵万里)
闵万里是那种把“不能降低对自己的要求”当成人生信条的人。他给团队打气,“同学们,这件事情是可以work(生效)的”。留下的人选择相信他,毕竟,他的学术能力和技术水平都摆在那儿。经过团队的坚持和努力,第一年,他们完成了将近一千万的指标。2017~2018年度,这个数字变成了6.7亿。2019年6月,闵万里从阿里离职,创立北高峰资本和坤湛科技两家公司,以“技术+资本”的形式与传统产业做数字化、智能化合作,继续用他的理论对这个社会的一些环节施以作用。
坐在深圳自贸中心的办公室,闵万里总结转型经验:“作为一个已经在学术界成功过的人,当你走进产业的时候,能否成功的关键是,你还有勇气撸起袖子加油干、走到最底层?”如今,每见一个新客户之前,闵万里都要求员工把演讲PPT带到他的办公室,花一两个小时听他们现场演示,模拟谈判时的状态,他不仅会看每一张演示文稿的内容、用词、字体和字号大小,也纠正员工的表述、表情和精神状态。
在一家公司里,技术只是生产链条的其中一环,必须务实,要能带来实实在在的增量。
公司和学校的逻辑完全不一样。快手AI Lab首席科学家刘霁对此感触深刻。在学校,环境相对单纯,找到一个学术问题(输入),花时间从各个角度去研究(输出),就好了。而到了快手,“很多时候输入输出还得自己去定义”。对公司也缺乏全面的认知。 “做技术的人总觉得把技术打磨好了,什么事都解决了,但其实在公司里你更多的是要去理解技术所处的环境、解决技术问题成本有多高、这个事情本身处于什么战略位置”他说。
2018年,快手商业化成立FeDA智能决策实验室,刘霁兼任这支团队的负责人,跟多个一线业务部门都有过深度合作。这个团队曾开发了一个名为Persia的基于GPU的广告推荐训练系统,单机效率提升640倍,意味着,以往用50台计算机一天只能尝试一个新想法变成只需一台计算机一两个小时就能尝试一个新想法,极大地提高了开发效率。刘霁觉得Persia证明了他们这些掌握最前沿技术的科学家所能对公司贡献的特殊价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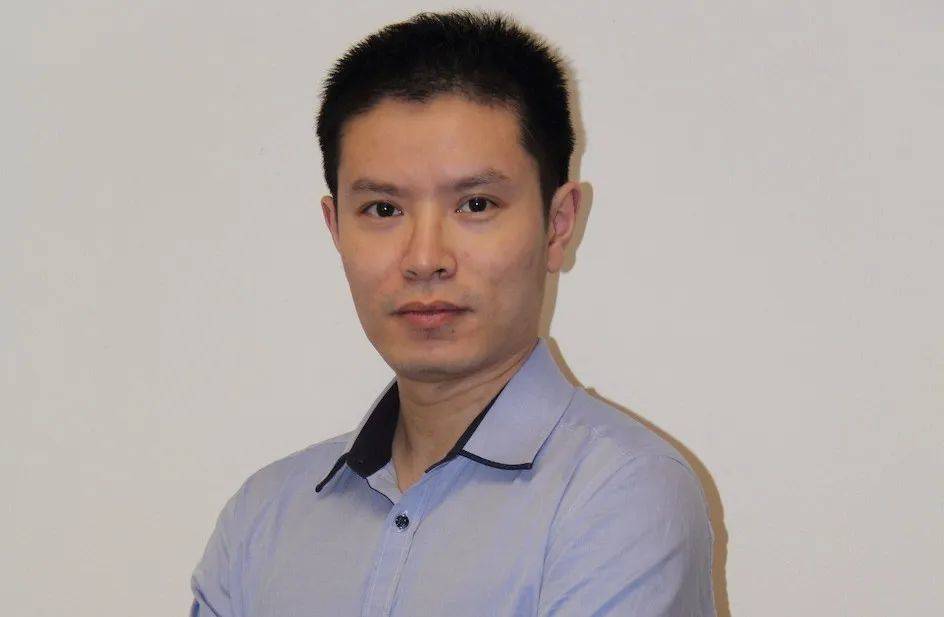
(刘霁)
刘霁出生于1983年,是威斯康星大学博士。在学校搞理论研究时,他就和别的同学不太一样,他最喜欢解决的是“工业界的人真正关心的问题”。刘霁曾帮IBM、NEC解决许多系统上真实存在的问题,毕业后直接选择加入大公司。在一家公司里,科学家的价值是要用业务产出而不是学术成果来计算的。他的思维转变很快,给研究院制定的OKR都是可量化的,比如:提升广告主投资回报率XXX,提升广告的收益XXX,提升用户点击率XXX……
“如果有研究员提出一个比较有前瞻性、有学术价值的问题,你会鼓励他们去研究吗?”
“这样的问题,说实话,它的价值首先要打个问号。”刘霁说。
二、曾经,大公司和科学家都没想清楚
几乎每一个赫赫有名的互联网公司都有一个人工智能研究院,吸纳了包括李飞飞、张潼、余凯、吴恩达、何晓飞等在内的知名科学专家。但每当谈起研究院的价值,许多互联网从业者都打出一个大问号。
一个很可能的原因是,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大公司没想清楚为什么要招科学家、怎么用好科学家,科学家也错误预期了大公司能提供的资源和空间。
前腾讯某部门知名科学家宋航(化名)是一位知名人工智能教授。几年前,他想把手上掌握的一个技术点做成APP,他试图说服几个学生,“学生基本上都翻我白眼”。
“老师,我是做研究的,你要做软件的话不要找我,我做不了,也没有时间。”学生回复。
宋航好说话,就答,“好哇。”
但这件事情很长时间以来都成为他脑子里一个强烈的愿望:他想到商业界去看一看。
几年前,腾讯向宋航发出邀请时,他感到很开心,那个等待的机会终于出现了。

虽然一直强调“腾讯对我很好”,但现在复盘那段经历,宋航觉得“和预期的有比较大的差别”。有一些问题他和公司都很难直接解决。
一个是公司给的时间包容度不够。研发有成本压力,“短期内不是特别能看得出经济效益的话,它的发展显得就没有那么快”。另一方面,人手也不够。宋航希望自己主导的产品能做得更大,理想状况下,他需要500人,“其实任何一家公司都很难满足我的设想”他说。能拿到的招人指标有限,高层也要去平衡各个部门,“比如我需要这么多人,其他部门也想要这么多人,老大怎么办?”而内部其他部门的人员和资源也做不到完全掌控和调度。
经过一段时间的权衡,宋航决定创业。创业的一大优势在于,宋航能获得比公司内更多的资源,钱和人和体系,他作为CEO对团队的掌控感也更强,技术空间也相对更大。
商业要求技术落地,背后的要求是科学家本人也要落地。看上去只是换种方式用技术做事,但这个转变对于科学家们来说,其实特别难。创新工场AI工程院执行院长王咏刚接触过许多从大公司出来的科学家,他们所讲述的片段可以拼凑出当时他们所遭遇的困境。

(王咏刚)
首先,命题变得非常直接:如何在下一次产品上线时,带来X亿的收入。需要开各种各样的会,所有产品经理、市场经理、销售经理的问题都提到你面前。“你很可能认为这是一个非常垃圾的功能,但你必须要按照客户的要求做出来。”王咏刚说。
其次,很多事情科学家们搞不懂。比如,把一个视觉算法包装成手机摄像软件里的一个功能,这里面包含大量产品化的东西:怎么和硬件结合?怎么突破手机CPU的限制?怎么让用户和真实的场景发生关系?之后这款手机怎么定价?如何占有市场?采用什么销售策略?在这些和业务紧密结合的讨论里,他们可能没有太多发言权。“科学家会觉得:这已经超出我的理解和能力范围了。”王咏刚说,“他就会感到孤立,会无所适从。”
“虽然绝大多数科学家非常愿意入世,愿意追求长远的社会贡献,但这种贡献没有那么容易。”王咏刚用了一个类比:做学术是站在非常高的山顶去寻找阳光,而做商业是站在草丛里把路修出来。“你知道,那些站在山顶看阳光的人往往会觉得:修路、搬石头,这不是我要干的事儿。”
以科学家的头脑,他们一定能把商业的问题考虑得非常清楚。“但很多时候他就是不喜欢,他不愿意去想钱的事情。”王咏刚说。最后,他们中的一些像宋航一样选择离开,有的干脆重新回到学校教书。
三、大公司往往缺什么招什么
2016年,AlphaGo战胜围棋世界冠军李世乭九段,让整个行业经历了一场火山爆发。一夜之间,所有人都在讨论人工智能。大公司们非常恐慌,焦虑地布局AI。当时,市场上很少有人懂这门技术,只能开高价(年薪几百到上千万)去学校招科学家。
研究院搭起来后,这些科学家应该怎么用、怎么考核?当时,公司们都没经验。
被借鉴最多的是微软亚洲研究院(MSRA)。它1998年就在北京成立,是国内出现最早的互联网公司研究院。旷视首席科学家、旷视研究院院长孙剑曾在那里工作13年。他告诉我们,MSRA对研究员的考核标准是“年底说出三件你做的了不起的事情”。而怎么算“了不起”?标准是:同行认可、同行考评。
其他模仿MSRA的大公司也一度把论文、专利、科研成果当作考核科学家和研究院的标准,甚至不是定量的。
许多科学家之所以愿意加入大公司,是因为看中那里的数据宝藏。可实际开展就会发现困难重重。大公司重流程管理,部门之间壁垒较高。大量数据都掌握在业务线,研究院想直接拿来用,有的也不情愿交出来。
曾就职于百度某业务线的高级技术陈飞(化名)解释:假设研究院做一个东西去帮助业务,业务方做出收益,那这个收益到底是归我业务方还是归你?之后我要升职加薪时很可能扯不清楚,那这边就会排斥。而且,“说白了,我们业务也可以自己招科学家来搞。”
因此,真要说进公司比在学校有什么具体优势的话,一位曾就职于MSRA的科学家总结:可能就是不用花时间去申请funding(科研资金)。
业务层对研究院的贡献也并不满意,在职期间,陈飞“确实没有感觉到研究院对自己有多大帮助”。“可能早期会提供一些工具,但后来发现那个也不足以解决问题,最后我们还是自己做的。”陈飞说。
两个部门在技术理念上也有差异,谁也不服谁,“研究院的人觉得自己很厉害,认为你们业务上用的这些算法都是很简单的东西,可能就不那么愿意投入。业务的人觉得你都是阳春白雪,能实际投产的太少。”时间一长,大家都心照不宣,墙越来越高,再后来,“可能研究院做出来个项目,啪往对面一扔,也不管你接不接得住。”
而更隐秘的心思是:科学家们也可能目的并不单纯。
AlphaGo出来后,有机器学习经验的技术人才一下子成了市场上的抢手货。王咏刚记得,当时,整个硅谷的机器学习工程师跳槽率极高,且工资都“一下子能翻好几倍”——要知道,从前这帮人是技术部门里的“边缘人物”,有的甚至“感觉入错了行”。几乎所有公司里最值钱的工程师都是搞AI的,而做C++、Java的技术人员那段时间心态“被打击得也很厉害”。
学术界里,peer pressure(同辈压力)也让科学家们心态失衡。闵万里就曾听到过同行感慨:XXX那小子都到某个大公司当CXO了,他当年还抄我作业呢。很多留在学校的科学家也想走出去,到底是利益驱动型的还是价值驱动型的不好说。“这其实是对科学家价值观的一种挑战。”他说。
大公司目的也不单纯。不止一位受访人说,有的公司之所以招入或仍然留着某些厉害的、知名的科学家,是为了“把他们当吉祥物”:向市场证明公司重视AI,愿意为此投入,还能吸引更多崇拜他们的优秀年轻人(可以干活)。
“吴恩达过来之后,为百度带来的价值是,估值蹭地上去了。”陈飞说。
四、从冷门到抢手货
如果把时间向前截取20年,科学家们谁都不会料到人生剧本会有如此大的变化。
回忆起自己的学生年代时,滴滴人工智能研究室负责人叶杰平总共用了五次“低谷”。2001年,他到明尼苏达大学计算机系读博时,人工智能是“很多人根本就不愿意学”的领域,整个明大计算机系一个专门研究机器学习的老师都没有。叶杰平坚定地选择这个方向,是因为“确实感兴趣”——他聊技术的语气和方式、讲到这几年工作时所流露出的满足感让你丝毫不怀疑这一点。

(左二为叶杰平)
从前在学校搞科研时,叶杰平的工具只有一台电脑和一支笔。缺场景、缺数据,研究样本只有一千个,“这已经算很大的数据量了”,他说。第四范式主任科学家涂威威2009年在南京大学读研时,用得最多的是NASA在几十年前公布出来的老数据。现实条件给研究带来很大制约。涂威威曾经听说过一个课题:如何用机器学习改进软件开发。倾注了很多时间得到的测试结果里,关联度最高的特征是:代码越长越容易出现bug(缺陷)。“当时我就对这个方向有点失望了。”涂威威说。
在那个人工智能=冷门的年代,选择在这个方向走下去的大多数是出于真诚的热爱。
刘霁是叶杰平在亚利桑那州立大学做教授时带的研究生。他非常聪明,数学底子很好,选研究方向时,特别钟情机器学习。机器学习是人工智能的核心。它研究的是让计算机通过算法,模拟或实现人类的学习行为,并获取新的知识和技能。它有极强的创造性,探讨更本质的东西——很难不让技术极客们为之着迷。
刘霁认为它“有一种抽象意义上的美感”。我请他详细描述这种“美”,他描述得非常理科:“我想主要是因为,它的本质是用数据辅以人类的非结构化认知,通过学习形成一种结构化的智能。”——仔细琢磨,能从中体会出一种理科式的朋克和浪漫。
叶杰平能感觉到刘霁的热情,但出于老师的责任感,他跟刘霁说:“你选这个能力上应该没问题,但是要谨慎,以后可能不好找工作。”这并非孤例,2013年,吴恩达在接受《连线》采访时提及自己读书时的经历:小时候,吴恩达就梦想能创造出“能像人一样思考的机器”,但当他上了大学,面对当时的人工智能研究状况,他选择了放弃。后来,身为教授的吴恩达也会劝阻学生追求同样的梦想。
谁也没想到后来AI“搞出了这么多事情”。随着互联网公司的规模迅速扩张,软硬件设施以极大的效率更新换代,更能支撑超大算力的芯片的出现,规模化用户群积累起的海量数据,让工业界正在演化成使机器学习生根发芽的沃土。
变化首先从硅谷发生,很快传到国内。
2013年,北京中关村微软中国总部。孙剑注意到Google Photos已经能做到把上传的几百张照片自主分类,分类结果“大多数还都没错”。“当时就是一个瞬间,深度学习改变了我对图像语义理解的认知,它来得比我想的更早”孙剑说。接着,他赶紧领导团队加大了对深度学习的研究。

(孙剑)
2014、15年,一小波人工智能科学家“下海创业”:汤晓鸥创立了商汤,朱珑创立依图,余凯创立地平线……宋航和他的学生很早就收到过这些公司邀请,但基本都拒绝了,理由是“看不懂。不知道这样的公司到底能不能走下去,能走多远。”而到了2016年,AlphaGo带来的那股热潮让这批公司估值再次大涨,他的学生心里泛起波澜:“就觉得我靠,以前我这帮同学们马上就财务自由了,我当时怎么就没这样。”第二年,他们一起加入了BAT中的一家公司。
工资、融资额、公司估值、身价……这一个个实打实的数字让许多仍在学界的科学家们经历了一场内心的风暴。
有些四处托人打听:“创业这条道路到底怎么样?”某高校旗下基金的投资经理韩东经常接触有创业意愿的科学家,他评价那几年科学家创业热:很多都是跟风的。一个表现是:老师们特别在意估值,内心深处是在和同行比较,“我学术成果不比他差,凭什么我的估值低?”
“对一些科学家来说,走学术路线,升副研、副教授也比较累,甚至已经是正研、正教授的也没什么奔头了——那还不如趁早把手上的资源和技术成果变现。”韩东说。
五、科学家在大公司如何发挥价值
叶杰平之前从来都没想过离开学校。坐在西二旗钻石大厦的办公室里,讲述自己前后两段人生路径时,那种割裂感让他自己都曾经感到意外。
2014年,被密西根大学聘用为教授时,叶杰平想的是:我应该待在这里十年不动。尽管互联网公司们早就因技术而广泛施加影响力,但他更愿意留在学术界一个安静的角落搞科研。
仅仅一年之后,叶杰平的平静就被打破了。
2015年暑假,滴滴向他发出邀请,约定回国后好好谈谈。反正也要回北京,叶杰平没想太多。从底特律上飞机的前一个小时,他突然接到滴滴的求助。对方在一个项目上碰到难以攻破的技术难点。当时,滴滴希望把抢单模式变成派单,但究竟怎么设计算法才能让司机更好地接受和适应指派规则、保证派单成功率,他们还不确定。
“我本来想轻轻松松回来旅游一下,那不是没得休息了嘛。”叶杰平心里犯嘀咕。但他很愿意去琢磨一个有难度的问题,脑力挑战能带来快乐。在飞机上安顿好,他掏出纸笔,十几个小时的飞行时长,一直都在琢磨。
那时的叶杰平对网约车毫无了解,唯一知道的是“听说过Uber这家公司”,还是因为有个学生被聘用了。网约车是什么逻辑、怎么运作、要经过多少环节、平台是怎么吸纳和调配司机的……这些业务细节他几乎全不知道。“那时候很想打个电话,让别人给我讲一讲。”他回忆道。
在机舱这个封闭空间里,叶杰平思维高速运转,用一个高度抽象的数据模型把问题简化出来。计算结果写出来时,他自己也忍不住内心的兴奋。一下飞机,他就直奔上地附近的滴滴总部。滴滴的工程师们早就在等他了,一间特别小的房间里挤满了人。叶杰平把电脑上的PPT打开,他在设计的主公式里加了一个参数变量,通过动态调整参数值,让司机在一两个月内适应派单逻辑,实现从抢单到派单的平滑过渡。
那是叶杰平第一次用算法试着解决一个生活中实实在在的问题。方案上线测试时,他每天都关注数据的变化。之后的一次复盘会,滴滴高层总结:派单项目是过去几个月最大的功臣之一。“啊,这个事情影响力竟然这么大!”叶杰平感慨。
这件事情让叶杰平的想法发生了颠覆性的转变,他觉得,公司是座富矿,“遍地都是机会”。以当时滴滴的体量,这套算法能影响成千上万人的出行。要知道,在学术界,要想达到同等的影响力,“除非你能拿诺贝尔奖”,他说,“而且诺贝尔奖也要等二三十年”。
返程的飞机上,叶杰平做出了改变后半生人生路线的决定。一回到学校,他马上把手下的博士生叫过来,说:“你们做好找工作的准备吧,我可要走了。”
本以为加入研究院是“一半研究,一半落地”,但在滴滴的头两年,叶杰平根本就没时间看文章,“全是落地”。业务很忙,“天天打仗”。这种感觉让他觉得新奇,战场是直接拼刺刀,技术的优势立竿见影,有“非常强的愉快感”。
公司慢慢稳定起来之后,从18年开始,叶杰平终于又有时间读论文,用科学家们的技术优势帮公司建立壁垒。最近三年他投入精力最多的一个项目是:将AlphaGo的强化学习方法用于网约车派单和调度。
向我们描述项目原理时,叶杰平像是一个深思熟虑的棋手:整个城市是一个“大型棋盘”,等待调配的司机像是棋盘上的棋子,决定留下来还是往东南西北开出去是落子决策,引入AlphaGo的算法,像决策落子位置一样给来给司机进行调度。“最后只是通过算法,在不影响用户体验的情况下,部分参与AI调度的司机收入提升了8~9个点。”叶杰平的语气里充满成就感。
曾因学术感到沮丧的涂威威也选择进入公司。临近毕业时,他经老师引荐,认识了百度搜索引擎营销平台、百度凤巢的负责人戴文渊。入职后,他们用机器学习方法理顺了平台的底层逻辑,带来的效益是老方法的八倍。看到收益往上涨的那个瞬间,涂威威觉得非常震撼,“没想到机器学习在公司竟然可以被用得这么好”。
涂威威出生在1988年,小时候信息比较闭塞,听到最多的是“美国包装出来的一些二十世纪最伟大的科学家”,比如,爱因斯坦等等。和那一代很多小朋友一样,涂威威从小被灌输的思想就是长大要当科学家,“这很伟大,很有逼格。”读书时,涂威威特别喜欢物理,还参加过物理竞赛,取得一些成绩。长大后,他发现,基础科学基本都是预测未来几百年,可能都没人能活着看到这些问题被解决。“实际上,那个理想是非常虚的。你想做爱因斯坦,但你并不知道爱因斯坦意味着什么。”他说。

(图右为涂威威)
人的一生是有限的。涂威威想,爱因斯坦之所以能被人记住,一方面是他确实让人重新认识了世界,另一方面是他改变了很多人的想法,对这个世界影响很大。“做技术的其实都会有这样的想法,希望自己做的东西能够去影响更多的人。”他转变了思路,用另一种方式去改变世界。
2015年,涂威威从百度离职,跟戴文渊一起创立了第四范式,公司定位是人工智能技术与服务提供商,目的是帮助各行业的企业低门槛地用上AI,影响更多的人。
六、科学家们决定走进商业
2017年3月,北京西二旗附近的百度公司总部。
时任前百度研究院院长林元庆和吴恩达坐在一起讨论一个宏大的命题:AI怎么样才能真正称得上第四次工业革命。——这是当时人们对AI最大的期待。他们得出一个结论:AI要落到“互联网以外更广阔的各行各业去”。就在他思考这件事情如何在百度内部推动时,吴恩达突然离职宣布创业。这给林元庆带来一定的冲击。当时市场环境好,投资人都看好AI项目,林元庆有些心动,经过两个多月的评估和纠结,他最终也决定创业。

(林元庆)
真格基金投资总监尹乐对林元庆的第一印象是:充满激情。描述创业想法时,林元庆说:“我要做AI to B”,下一句是,“我的公司就叫Aibee(AIB)”。但具体要深入到哪个行业、哪些场景,他都还没想清楚。第二天,林元庆就被引荐给了徐小平,三个人吃了顿晚饭,真格马上就决定投了。他们信任林元庆的学术能力,而他的职业经历也是很关键的加分项。
如果不是当时那个节点——市场上一切大门都为他敞开,林元庆不太可能出来创业。回国时,他想的是“在百度干到退休”。2018年初,林元庆获得了1.65亿人民币的天使轮融资,在那个时间点刷新了中国AI初创企业天使轮的融资记录。
见过大量科学家的投资人都会在意商业敏感度这一点:科学家们往往会低估商业。在交流时有时能明显感到老师们把创业想得太简单:“这个事情基本市场有多大、增速有多快,他们可能都是没太大概念的。”
科学家们需要商业上的帮助,这成为一个共识。王咏刚所负责的创新工场AI工程院创立的目标是连接科研和商业化场景,经常有科学家专门向他请教创业经验。王咏刚总结了几个科学家创业要注意的“雷区”,其中一条便是劝他们——一定要扭转心态:一旦决定要撸起袖子创业了,一定要补足产品化和商业化的能力。或者引入商业背景的CEO或合伙人,按需组建商业化团队——这是如今很多科学家主导创业的公司最常见的搭配模式,负责商业化角色的很多是他们的学生、前下属,或者投资人们也会主动帮科学家寻找和推荐合适的人选。
不管是科学家还是工程师创业,最终都要变成一个企业家创业。在一个新的社会角色里,他们必须重新开始学习。
一大堆名词扑面而来:HR、融资、业务、财务、商业运作、政府关系、媒体关系……每一个都跳出原来的认知体系,完全是另一个宇宙。得快速搞懂。并且,“光懂是不够的,还都要很懂。”林元庆说。
现在,林元庆70%、80%的时间用来管理团队、见客户。他把公司位置选在北京中关村壹号:一个距离地铁中关村站还有14公里的新产业园区,靠近西北六环。周围除了一组组拔地而起的新写字楼之外,没什么商业基础设施,显得空洞无聊——这倒是能让人更专注于工作,林元庆对这一点表示很满意。他就住在公司附近,经常骑车上下班,通勤单程时长20来分钟。这段时间,不太会想“宏大的、务虚的问题”——“创业没有这样的机会”,更多还是关心最近的业务。
6月初的一个下午,我们在林元庆的办公室第一次见面。他的电脑桌面上平铺了四五版公司简介PPT,他对它的熟练程度可以说是“超级精通”。每当我们抛出一个针对业务的问题,他都能在三秒内迅速滑出某一页,“快乐且滔滔不绝”地讲解起来。64页PPT,从想法到结构再到中英文表达都是他自己弄的,再由同事美化。“干一行学一行嘛”,他性格很开放,率直,说完这句后率先笑起来,对这变化欣然接受。
精确而高门槛的技术名词换成了模糊而重价值的创业话术:愿景、创新、革命、赋能、社会责任——在商业世界,只会讲技术要点是不行的。“一旦的身份是一个创业者,讲技术就必须要搂着点。”创新工场南京AI研究院执行院长、倍漾科技创始人冯霁说。

(冯霁)
拥有“创业者”这个社会身份7个月来,冯霁努力让自己“去学者化”,具体表现是:要懂得忽略细节(搞计算机的人控制感都很强,毕竟要让程序遵从自己的指令,以至于公司刚成立时,他连地毯是什么颜色都想管);要学会杀伐果断(第一次裁掉员工时,他两天都没睡好);要忘了自己是技术专家(不能总把算法挂在嘴边儿,“如果个人的技术对创业的重要性只占20%到30%的话,那么在和别人沟通的时候就不应该用超过20%的时间聊技术”)。
外出谈事,冯霁就假装自己不懂技术,以至于曾有人表示担心:“冯霁,你招一个技术时要怎么沟通?万一被骗了怎么办?”去年一次国际会议上,还有位朋友特地来问:“今天聊的技术你怎么都听懂了?看你跟别人说得头头是道的,是从哪个公众号上学的吗?”冯霁一听,“心里挺高兴”。然后,拿出来自己曾经写的“一堆论文”。跟我们重复这个故事时还是很沾沾自喜。
不过也都是昨日回忆了。现在,他每天使用最多的软件是Office。“想不到我一个天天推公式、写代码的也有今天。”他笑着感慨。
七、今天,科学家影响世界的新方式
科学家创业的模式在国外已经比较成熟。今天,国内体制和机制也在不断给科学家松绑,这个模式也在慢慢跑通。
一位投资人告诉我们,这几年,高科技公司是重点扶持对象,“这也是科创板设立的原因”。他说:“中国科技成果转化率太低,亟需提升,科学家创业是其中一个比较好的形式,国家也是也有砸钱的决心。”对于科学家们来说,自己创业的风险当然很高,但一个绝对优势是可以调配更多的钱和资源。环境和投资人也愿意提供帮助,创业成功的可能性也比之前更高。
但科学家们要忘掉自己是科学家。
做好这件事不仅需要耐心,更关键的是,一个科学家要有意愿去俯下身来。比如,怎么让不懂技术的人听懂技术?如今,消费互联网早就是一片红海,可供新入局者找到的场景太少,科学家们把目光投向产业互联网。
那里都是些和互联网有很大距离的人, 比如:传统公司里的销售、运营、渠道人员;或者,面板厂商、光伏厂厂长、制鞋厂老总、煤老板;甚至是高中生、甚至是大专生、初中生……大部分“对AI的基本理解都没有”。一位科学家说,曾客户直接问他:“AI不是万能的吗?”“AI就是应该达到100%的正确率啊。”(显然都是错误的认知)
科学家们只好先以一个专家的身份,花两个小时给对方科普“AI的来龙去脉”。在很多人看来,这对于科学家来说意味着一种牺牲,而冯霁不愿意这么理解。他师从著名人工智能科学家、南京大学周志华教授,曾得到“情绪极度内敛”的周老师这样的评价:“假以时日会在学术界成为someone”。
冯霁是85后,刚30出头,和他的老师所处的那个时代不一样,他更能敏感地捕捉到商业机会,是周志华门下唯一一个创业的博士生。冯霁明显不是那种看上去就“很科学家”的性格。他非常外向、喜欢表达、组织能力强,被李开复和王咏刚都判断为适合创业。他给自己取的网名叫“冯牡丹”,有点戏谑味道。这种感觉也体现在他想要创业这件事情上。
冯霁非常喜欢的科学家是被誉为“天才数学家、赌神”的爱德华·索普,理由是:“这类人能利用数学工具(如:机器学习)干翻一众传统做金融的人。这是the right way of doing investment(正确的变革方式)。”博士还没毕业时,他就坚定地想要用机器学习和深度学习算法在金融领域创业,早早下定决心。放弃科研,有遗憾,但绝对不是一个后悔的选择。“有时候科研是一件蛮自我的事,因为它最大的乐趣来自于你的内心。但是创业是,我可以去聚集一群最优秀的人共同去颠覆一个行业固有的范式。”他说。
如果真要拷问内心,林元庆最喜欢的还是钻研技术。平时在公司,如果条件允许,他就跑去旁听技术的讨论会,那是他最熟悉和喜欢的氛围。
但成为CEO就是要调动出商业的那部分。1999年,海淀黄庄最大的十字路口有一块超大的广告牌,那上面的第一个广告就是被林元庆卖出去的,客户是联想,那一单他赚到了6万。是因为对商业的不那么热爱和对技术的真诚喜爱,他才在之后的许多年里,成为一名技术科学家。现在,他要重新变成一个拥抱商业的人。
他的公司Aibee成立的第一年,100多个员工每一个都直接汇报给林元庆,这样决策链条最短、速度最快。他在两三个月里以极高的效率见了将近40家各垂直行业的CEO,果断而迅速地决定打入零售行业。Aibee的第一个大客户,广州K11购物中心就是林元庆亲自谈下来的。这个落地速度超出投资人们的期待,“没想到元庆是个商业奇才”。
去年下半年,林元庆召开了一次股东会,几十个股东代表坐在一间咖啡厅里。林元庆向他们展示公司项目的最新进展,全程说了许许多多次powerful(强大的)。现在,“技术理想”也更务实,一切都要回归商业,能变现的场景是最重要的。林元庆熟悉的那份PPT上,公司已经投入使用的案例包括在K11等大型购物中心上线的智慧停车、智慧VR导航导购等应用。
我们最后一次见他是在六月初一个星期日的晚上。那天,林元庆和同事一起从早上开会到晚八点,接受采访前,他吃完一桶泡面,跟我们一直聊到深夜十一点。
采访结束,林元庆送我们到电梯口,整个办公区,所有工位都是空的,只有他的办公室亮着灯。林元庆穿着方便又舒适的拖鞋,还三言两语讲着公司今年的目标。电梯门开了,林元庆向我们笑着挥手,看上去不知疲倦。
(记者马子轩、万佩、房宫一柳对本文亦有贡献)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晚点LatePost(ID:postlate),作者:姚胤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