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扫码打开虎嗅APP

有人说,衰老是一个不断失去的过程。随着年龄的增长,人会越来越多地失去那些曾认为理所当然的东西:朋友,工作,社会联系,听觉、注意力和行动能力……正如人无法免于衰老,当生命之路行至接近终点,大部分人也同样无法免于难以自我照料、失去独立生活能力的晚年。
我们应当如何面对和度过这段时间?对于那些真正需要“养”的老人,家人和子女是否还是唯一的“最优解”?《社会创新系列》第十五个故事的主人公王艳蕊十四年来一直在探求这个问题的答案。她和她所创办的乐龄养老希望通过她们的工作,让普通人在这条失去之路上仍然能够保有尊严。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世界说(ID:globusnews),作者:李何,责编:谢雯雯,题图:受访者供图
“你们终于开门了!”这是疫情高峰过去之后,终于随着北京市初步解封而重开的北京石景山区乐龄养老服务中心,与它的创始人王艳蕊,几天里听到最多的话。
2020年的冬春之交,乐龄的老人和工作人员都度过了一段艰难的日子。一部分老人在过年前几天被家人接回家去团聚,本想住上两三天就送回来,没想到正碰上新冠疫情爆发,就这样滞留在了自己家。在院内的老人与值守的工作人员同样面临巨大挑战,由于疫情防控原因,家属探视被完全禁止,院内所有人不能出门,这一封就是三个多月。

“封院”期间乐龄八角南里驿站的老人与儿子只能隔门相聚 / “乐龄社区养老”公众号
解除封锁的通知一下,滞留在外的老人马上开始返回,哪怕仍需经过核酸检测和隔离十四天才能进入中心,这些苛刻条件也没有拦住他们返回的决心。
“家属都要崩溃了,家里不知道怎么照顾老人,也没有能力照顾,没有人。”王艳蕊解释,“不止家属,也有老人在家觉得住得不合适,也想回来,但之前谁也没办法(回来),他们就天天来问。”
也有在院老人的家属在乐龄公众号文章下留言:“这些日子,可把你们辛苦坏了……不是一个谢谢就能让我们心安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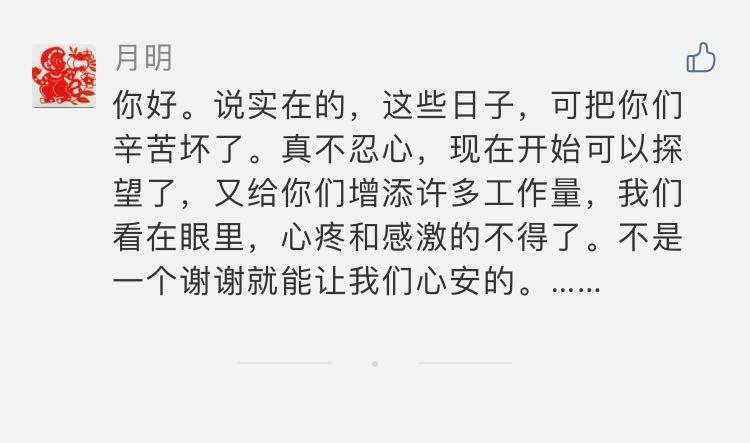
“乐龄社区养老”公众号留言 / 网页截图
这是2020年的5月底,“儿子活埋老母亲”与蓄意谋杀老人的“毒保姆”两则社会新闻在几天内接连刷屏,但在养老行业沉浮多年的王艳蕊看来,骇人故事背后,现实中的养老困局远非媒体公布出来的这么简单。
两个问题
“你想过为什么一般保姆不愿意照顾老人吗?”谈及两起恶性事件,王艳蕊摇摇头,“照顾老年人,尤其是卧床的老年病人,这样的保姆很难找,大部分人都不愿意做,保姆虐待老年人的事件确实存在,老年人或者是家属虐待保姆的例子我们听过更多,说到底,这个行业目前生态是极不健康的。”
住家保姆面对的问题来自方方面面,有老人和家属的坏脾气,有部分失智老人的无端控诉,有夜间休息时间无法保证,甚至还有更普遍而隐蔽的理由:因为吃不饱,因为老人的饮食通常量少且清淡,而雇主家庭不会为付出了高强度体力劳动的住家保姆单独做饭。
在业内看来,要解决保姆职业困境,让保姆的处境和行为都变得“可见”的方法并不复杂,但少人问津:建立家政公司合同制,一方面保护住家保姆的职业诉求,为她们提供社保和劳动关系保障,代她们与雇主家庭沟通;另一方面约束保姆行为,通过反馈机制排除“毒保姆”。
在不少其他行业都已发展成熟的这套职业法则,却在护理老年人的住家保姆身上失了灵。“大部分人不愿意额外出这部分钱,相反,真做起来的家政公司经常遭遇跳单,家属绕过公司直接联系保姆,觉得这样便宜实惠。”
监管和协调角色由此缺位,如此恶性循环的结果则是总有关系中较弱的一方成为这种不健康生态的牺牲品,有些时候是保姆,也有些时候是无法反抗保姆的老人。
“请保姆”就这样变成了一件需要承担巨大风险的事。而在许多人想象中,由足够孝顺的子女孙辈在老人晚年需要照顾时全权负责,始终是养老问题的“最优解”:既排除了老人被欺负、被虐待的可能性,也势必比“外人”更贴心和周到,还能在照料老人时给予充足的情感支持。
说到这里,王艳蕊抛出了第二个问题。“为什么要把找人照顾,和不孝顺,划上等号呢?”
现实困局
“养老”这件事,其实远非很多年轻人想象中的那样平和温馨:陪老人说说话,散散步,帮忙买生活用品,在老人身体不适的时候陪他/她去医院,或在重病住院阶段去医院看望和陪护。
在现实中,早在最终宣告情况危急之前很久,家里的老人可能就已经难以自己行走,可能失去语言和表达能力,可能失明失聪,可能逐渐失去思维和意识,变得无法交流,可能陷入幻觉乃至于做出一些家人无法理解的举动。

今年春节时,王艳蕊给在院老人送生肖鼠 / 受访者供图
“失能失智”,我们一般这样称呼这个老年人群体。他们需要的不再是“陪伴”,而是实实在在的“照料”,需要有人帮助完成大小便,帮助洗澡擦身,需要喂饭或者流食,需要有人24小时关注情况变化,制止危险举动——就像照料一个新生儿那样。
甚至比照料新生儿更难。
乐龄接待过这样一个家庭:家中两位高龄老人均为重度失能失智,老父亲失明且患有阿尔茨海默症,母亲则常年瘫痪在床,除了雇佣了一个住家保姆之外,还需要四个子女以月为单位轮流在父母家陪护,但实际上,四个子女本身也都已经过了退休年龄。
找到乐龄的是这家的大女儿,轮到她值守的那个月刚好赶上她自己的女儿怀孕分娩,住家保姆照顾一位瘫痪老人的生活起居已经工作饱和,而患有阿尔茨海默症的老父亲一刻离不开人。当“上有老,下有小”的中年危机,被拖入近乎没有止境的时间索取,几乎无法避免顾此失彼的结局。
她因此选择了向乐龄求助。
起初她为父亲尝试的是日托形式——早上她出发去女儿家前把老父亲送到乐龄站点,晚上再接回,尽管家到站点只有大约一百米距离,这种方式还是很快被证明行不通:移动过程中的困难还都在其次,阿尔茨海默症患者极其依赖熟悉的环境,而对于这些近期记忆几乎为零的老人来说,每天两次往返其实意味着一整天都在陌生环境中度过,而患者会因此格外焦虑不安,对于失明老人,这种影响尤其强烈。
“我能把他暂时放在你们那儿吗?”那位阿姨这样问王艳蕊,“晚上也不接了。”

乐龄广宁街道站点大门 / 网络
这是乐龄尝试老人入住模式的开始,王艳蕊将护理员们的排班从原本的统一白班修改为24小时倒班制——这位阿尔茨海默症老人只是庞大失能失智群体中的一个,实际护理起来,几乎每一位老人的情况都有不同:有失智老人没有办法睡整觉,有行动不便老人临时需要起夜上厕所,卧床老人需要定期帮忙翻身,因为容易坠床而应用约束保护措施的老人则出于防范意外的考虑,需要定期巡视。
在老人护理这件事上,照料者从来没有真正的休息时间。
而这样的晚年并不特属于某个“特殊群体”:它已经是许多家庭当下的现实,还将是更多人的未来。绝大多数人都会在晚年、或是在临终前经历这样一段生活不能自理的时间,时长或许是几个月,也有可能是几年甚至十几年。
没有家庭能够承受如此强度的长期照护工作,因为这意味着至少牺牲家里其中几个人的全部生活,包括睡眠,在个别极端情况下甚至也包括照料者自己的健康。
与照护困局同样现实的还有家庭财政负担:目前市场价而言,照料一个失能老人的保姆薪水至少在7000元以上,如果有专业技能,上万也很常见,即使在北京,这也不是一般人的退休金可以轻易负担得起的费用。
面对养老,我们往往过度强调诚心与爱,却闭口不谈种种难以突破的现实困局。
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
更容易被人忽略的是,除了海量时间精力之外,照顾老人又是一件处处需要专业技能的事。
一个最简单的例子是挪动老人——把失去行动能力的老人从床或者轮椅上挪下来,这听上去并非难事,现实中没有经过训练的人却很有可能发生意外:弄伤老人,或者弄伤自己。
“我们护理员培训的第一个步骤就是床上的挪动,从床上挪到轮椅上,或者从轮椅上挪到床上,那么首先你应该从什么位置下手去抱老人,不提前做这些培训,有可能你一拽,老人就骨折了,脱臼了,或者你自己发力不对,把腰闪了,这还都是没有摔的情况。”王艳蕊总结,“其实是真的挺难的。”

乐龄工作人员在开展培训 / 受访者供图
挪动只是第一步,照顾一个失去行动能力的老人,意味着每天在固定时间完成的一系列身体清洁,按照健康状况安排的特殊饮食,具体到小时的娱乐和休闲活动,定期翻身以及巡视,考虑到没有人能够独力承担如此繁重的工作,照护当中还涉及不同班次之间的工作衔接与记录……
而定期监测身体指标,为每一位老人安排需要按时服用的药物,及时识别危险信号并联系医院或出诊医生,更是每一位护理员的工作日常。
“这些东西,在家基本是没有办法实现的,家人精力和专业技能都有限。”乐龄接手的老人不乏来时身上有褥疮、或是因防护不周出现撞伤淤青的例子,入院后,这都是能够、并且必须避免的问题。

入住老人利用认知症辅具进行康复练习 / “乐龄社区养老”公众号
“我自己来说,如果有一天我父母离不开人了,要人照顾了,我肯定第一时间就会找人。”王艳蕊说,“情感支持和具体的护理工作是两回事,我当然会陪着,但是护理的事情,我做的肯定没有我们护理员好。”
但她也承认,现实并不是可以这样非黑即白划分清楚的事,亲人的照料与专业护理之间应该如何抉择,仍然受到更多条件的限制,而机构所能做的仅仅是为这些家庭和老人提供多一种选项。
“我也很矛盾,我自己家也有老人。”她的父亲也在近年查出阿尔茨海默症,而母亲仍在倔强地自己照顾着丈夫,“很多事情如果是我们护理员做出来,那肯定是不行的,像跟病人发脾气,骂他吼他,但我妈就会这样,即使我跟她反复解释他是病人,可我妈自己也有很多情绪要发泄。”
从六十五岁正式迈入定义上的“老年”门槛,一直到最终离世,这段极有可能长达数十年的漫长晚年时光当中,老人应当追求什么样的生活,接受什么样的照顾,每一个个体和每一个家庭都会有自己的答案。
但在当下,更迫切的问题并非老人或家人应当如何选择,而是绝大多数情况下他们缺少选择的机会。
做雪中送炭的事
“我对公益还是有情怀在。”谈到过去几年的选择与经历,王艳蕊这样总结,读书时选择了法律专业的她没想到未来自己会投身于养老事业,但一路走来,对社会公平正义的追求,希望“解决问题”、希望能为其他人做些实事的初心,直到今天仍推动着她。
“我们要做雪中送炭的事情,而不是那些锦上添花的事情。”王艳蕊总结。

王艳蕊(中)探访老人 / 受访者供图
2006年最初创办社区养老公益机构“乐龄合作社”时,王艳蕊和她在社区动员起来的老年志愿者团队同样没有特别注意过深处舆论水面之下的失能失智老人群体,在当时,动员本地社区力量,实现老人群体内部的互帮互助,被认为是解决老年人孤独等问题的先进理念之一。
但真正的刚性需求逐渐浮出水面:不断有老人因为家里保姆“断档”而寻求同为老年人的志愿者团队的帮助,老年护理方面的家政服务存在巨大缺口,尽管热心志愿者愿意提供一些帮助,但终究不是长久之计。
乐龄的全职家政护理员很快上岗,不久后争取到了部分社区居委会的场地支持,从上门服务发展到日托,之后又在家属要求的推动下,进一步从日托发展到入住。
“重度失能老人的护理是有极高需求的,有些家庭是临时找不到保姆,有些是刚出院的需要特殊护理的老人,家属担心照顾不好于是寻求专业帮助。”王艳蕊解释。第一个开放入住的站点最初的六张床迅速满员,随后开始加床,王艳蕊也收到了更多社区“能不能开到我们这里”的询问。

乐龄的护理员们在站点接受高级护理员培训 / “乐龄社区养老”公众号
摸爬滚打多年,王艳蕊始终坚持要做平价养老,要为普通人、普通家庭解决养老困境,但在此之前,乐龄始终没有解决需求端与服务端之间经济上的巨大鸿沟:一边是需要职业培训、需要稳定工资和五险一金的全职员工,另一边却是节俭了一辈子,最不舍得往自己身上花钱的老年人群体。
但从接收长期入住老人开始,乐龄虽然仍旧亏本,但终于开始有了稳定收入。“我们要做的是居家、社区和机构一体化的综合服务。”王艳蕊说,“这几年我一直在倡议,那些需要照顾的老人才是真需求。我们要做小型嵌入式的综合养老服务,但更多地偏向于失能失智、高龄、空巢、独居等等群体,那些低龄的活跃老人,我们希望他们能来当志愿者。”志愿者模式,是十四年前“乐龄合作社”的延续。
在找到正确经营模式之后,乐龄渐上正轨,2019年,乐龄接收的托管老人人数达到146人,老年餐服务超过4万次,直接接受服务的老人则达到1046人。如果不是新冠疫情突如其来,王艳蕊原本期望乐龄能够在2020年第一次实现收支平衡——但疫情打乱了一切。

乐龄站点内工作人员和老人一起做活动 / 受访者供图
“也不是没想过放弃,这次我也跟我们员工说了,要是今年撑不下去那咱们只能解散,我实在没钱继续往里贴了。”王艳蕊说着,笑了笑,“但现在还行,走一步看一步吧。”
可是,成立十几年来一直亏本,已经贴钱贴到没钱还能继续投入的程度,为什么还会一次又一次地决定坚持下去?
“有那么多小超市,小饭馆,都亏着,北京几千几万家饭馆,是都在盈利吗?”王艳蕊反问,“别的行业,也没有那么多人说因为现在不挣钱,我就不干了吧?”
沉吟片刻,她的声音低下去,“而且,我喜欢,我也知道这是真正有意义的事。”
为了有尊严的生命
在所有国家,养老模式问题如今都在探索阶段,并且前景都日益悲观:老龄人群获得的照料和医疗服务越好,人均寿命越高,社会的老龄化程度就必然越严重,长此以往,作为产业的养老服务模式似乎只有资金链断裂一种可能。
“这是事实,现在大家都没有答案,我也没有。”王艳蕊说,“但是不能因为这样,就不再去做了。”
过去几年,乐龄在联合多方力量推动“长期介护险”的发展,希望能够通过社会保险的方式帮助支付失能失智老年人的晚年照护费用,这也是一部分养老产业发展比较成熟的国家在多年实践中摸索出来的当前解决方案:调用类似医保的社会保障系统,让老年人有机会在晚年获得更专业的照料,而不至于为此搭上毕生积蓄。
尽管仍在起步阶段,但类似的社保理念已经开始在小范围内落地。2020年开始,北京市石景山区——也就是乐龄目前所在的区——将推进失能老人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的全区覆盖,乐龄的经验,也正在更多地方获得引进和推广。

王艳蕊(右)与自己的母亲和女儿在乐龄活动中 / 受访者供图
而对王艳蕊来说,眼前仍是一条有关意义、价值和目标的漫漫长路。在日本照护所实习时,一位高龄失能老人的案例给她印象很深,这位被称为“多米桑”的老奶奶已经103岁,无法言语,无法进食,无法行动,也失去了全部亲人,没有人知道她是否还有感觉与思维,但她依然活着。
每一天早上,护理员会把她从床上唤醒,和她说话,把她抱下床,做晨间清洁,然后吃早餐。期间护理员会一直和她讲话。她只能吃流食,用管子推到嘴里,但每一天的流食也会安排好不同的味道。护理员会说:“多米桑,今天我们吃胡萝卜味的早餐哦”——她不会有反应,但这不是让她无尊严地活着的理由。
对她的照料也精确到了每一个细节:帮她清洁过手以后需要涂上护手霜,百岁老人的皮肤如此脆弱,护手霜不可以涂抹,而必须轻拍。每一周,会有另一家专业机构上门来帮她洗澡,她所在的照护所也有能力提供洗浴服务,但出于防范虐待、增强监督的考虑,她的照护计划被分配给了多家机构。
而多米桑已经不再会表达她的感受,也不再可能“好起来”,她的生活依靠着日本社会保险系统维持,这样大的精力和成本投入,值不值得?
这也是我们每一个个体,作为子女,作为将来即将老去的自己,都终将直面的终极追问:如果无论如何,终点都是一样的,为了过程中的不同而不问回报地付出,值不值得?
这是一个注定不会有统一答案的问题,而对王艳蕊和乐龄来说,考验仍旧接二连三。刚刚过去的这个六月,随着北京疫情的反复,原本已看到一线转机的行业再次遭遇沉重打击,服务中断使得不少机构的资金流状况愈发艰难,一如王艳蕊在6月初发布的乐龄2019年报序言中写过的句子,“真的是没有最难,只有更难。”

5月19日,乐龄站点迎来疫情以来的首批前来探望的家属,但不到一个月后,探视和入院就再次遭遇暂停 / “乐龄社区养老”公众号
但在从业十四年后的今天,回看自己为之投入无数精力金钱的养老事业,王艳蕊提起的是那个经典寓言:雨后的沙滩上,一个小男孩把浅坑中搁浅的小鱼一条一条扔回大海,路过的每个人都告诉他,他不可能在浅坑干涸之前拯救所有小鱼。
小男孩回答说:“能救一条也有意义。”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世界说(ID:globusnews),作者:李何,责编:谢雯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