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扫码打开虎嗅APP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看电影杂志(ID:moview_weekly),作者:东四环作家协会,原文标题:《情欲芬芳:色的绽放》,题图来自:《小姐》剧照
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文化,对情爱的态度也是千差万别。
在法国,浪漫渗透进人们的血液,他们以同样的执著对待着性和爱,渴望着一个超现实的归宿;日本的情爱追求极端,用常人难以想象的方式,寻求着近乎病态的满足;

美国则精熟旁敲侧击的艺术,在撩拨心弦方面已然登峰造极;意大利人,对展示女人第二性征的美,有一种特殊的迷恋;
而韩国的情爱,有虐心决绝时的狠,也有温存缠绵时的柔……
在遍览这些风格迥异的情色特点时,我们犹如走进一座充满奇情怪欲的博物馆,漫步其中,我们或许能够体会到,那些原本相似的欲望与情爱,是如何披上不一样的衣裳,潜进了不同文化所造就的电影里。

法国:浪漫的哀伤
有一个很经典的段子:某机构分别从英、法、俄、美四国抽取两男一女,分成四组各关进一间只有一个卧室的屋子进行观察,且看他们如何过夜。
夜幕降临,英国那边,两个男人睡在卧室外的地板上,将卧室让给了女人;
美国那边,年长的那个男人站在卧室外焦躁难耐,抱怨怎么还没轮到他;
而俄罗斯那边,两个男人正为了谁和女人共处一室而打得难分难解;
最后是法国,在卧室外不见一人,只听见从卧室里传来两男一女的欢声笑语。

这从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为什么当其他国家的情爱电影还在纠结于“这样拍是不是有伤风化”的问题时,法国人早就已经行动起来了。
法国电影的情爱,发生得相当自然,就像日常生活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贝托鲁奇的《巴黎最后的探戈》就是“说干就干,毫不手软”的经典之作。

法国人对性的开放态度举世闻名,而根据法国24小时电视台进行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法国人以每个月做爱8.9次的“成绩”排名第一。
“浪漫”的法国人,令其他国家的人民群众望尘莫及。不仅如此,在情爱电影里,法国人的“浪”和浪漫,也早已妇孺皆知。

六十年代对法国而言,是翻天覆地的岁月,经过性解放和新浪潮的双重洗礼,法国电影自由、随性的风格到达了一个史无前例的高度。
从《射杀钢琴师》里米歇尔·梅奇猝不及防的露点,一直到《阿黛尔的生活》中“毫无节制”的床戏,法国人也向来没有“露不露”的顾虑,只有“露多少”的思考。

1964年的《艳情轮舞》一片里,更是将换妻、偷情等婚姻奇情一网打尽,尽显法兰西民族“博爱”的本色。
也难怪法国人经常感叹,在美国因为性丑闻被“喷到死”的克林顿总统,如果换了在法国,“算得上哪门子事儿嘛”。

值得一提的是,《艳情轮舞》的导演是声名远播的罗杰·瓦迪姆,他在五十年代末期为碧姬·芭铎打造的一系列软色情电影,对上了市场的口味,也影响了后世一大批卖弄风情的情爱电影。
许多人坚信,性与爱是两码事,或者要先有爱才有资格谈性。但法国人的认识却不这么“狭隘”,他们用电影表明,性也可以反过来催生爱。

《巴黎野玫瑰》里,贝蒂完全被桑格所征服,由性生爱,继而为爱陷入癫狂,酿成悲剧;
《钢琴教师》虽然充满了压抑和束缚,但女教师在自虐的过程中,的确品到了爱的甘露;
《浪得过火》里的妓女和流浪汉之间,也是先有床笫之欢,才有了感情上的依偎。

或许因为普通的性太过稀松平常,法国情爱片里的主角,往往会追求一种精神上的极致浪漫,但同时又对现实产生了背离。
《O娘的故事》里,对“主人”绝对臣服的O娘,最终掌握了“虚假才是现实”的无情法则,抛弃了自己曾经对爱的追逐;
《艾曼纽》里的人们,都是浪漫的化身——崇尚自由的妻子,放纵的游客和“通情达理”的丈夫,但即便如此,幸福和满足依旧只是个遥远的梦;
《浪得过火》中妓女为爱人倾尽所有,却同样为这种不计后果的奉献付出了代价。

在纵欲的狂欢中,还能挤出一丝伤感,这是法国情色最独特的气质。
日本:颓废的绚烂
日本既不像西方许多国家那样,受着“性与罪难脱干系”的宗教熏染,也不似中国这般,有一套根深蒂固的道德规范。
日本的情爱文化和产业,就像一条在没有阻力的波涛中加速前进的蓝鲸。情爱电影在日本的崛起,得追溯到战后时期。
当时的新东宝将“海女”这一古老的行当,搬上了大银幕。这些衣着清凉、性格奔放的女子,让广大的观众在电影院内乐不思蜀。

而另一家大公司日活,则拍出了《太阳的季节》,将一群放荡不羁、追求性刺激的“太阳族”青年推到观众视野中来,日活凭此片狂捞两亿日元的票房。
性与暴力此后在日本大银幕上的泛滥,离不开“太阳族电影”的影响。

六十年代初,以暴露和挑逗为卖点的“粉红电影”应运而生。它们“低投入高回收”的特点,吸引了众多投资者的目光。
“情色电影教父”武智铁二的《白日梦》,在1964年“撬”开了映伦的铁闸,替“同胞”们申请到了一张通行证。
于是,情爱电影如决堤的洪水一般涌入电影市场,观众的激情都被彻底点燃。

大制片厂敞开大门,招徕有志之士的加盟。日本情爱片的“四大天王”(寺山修司、神代辰巳、大岛渚、若松孝二),也都成名于这个时期。
现今司空见惯的情爱题材,比如囚禁、虐恋、“禁断之恋”等等,在当时几乎被拍了个底朝天,若说现在的日本情爱片基本在吃老本,一点也不为过。

《悲情城市》里的吴宽荣讲过一个故事:
“明治时代,有一个女孩跳瀑布自杀,她不是厌世,也不是失志,是面对如此灿烂的青春,怕它一旦消失,不知如何是好。不如就像樱花一样,在生命最美的时候,随风离枝。”
日本文化崇尚这种“开到最满最美的时候飘落入土”的“樱花精神”。
而日本的情爱电影,同样继承着这种精神。

《感官世界》里,阿部定在高潮来临时割下了情人的阳具,然后将其勒死;
21年后的《失乐园》里,一对出轨的中年男女,则在双双性高潮的同时服毒自尽,以凄美的方式作为对这个世界的回应。
在日本情爱片中,我们常常会感受到一股死亡气息的笼罩,将情欲带来的温度,降到最低。

在鲁斯·本尼迪克特的《菊与刀》一书中,她分析了日本民族“爱美而黩武、尚礼而好斗、勇敢而懦弱”的特点,这种精神分裂式的人物形象,在日本情爱电影里,比比皆是。
比如在《东京新爱人》里,女主角白天是勤勤恳恳的剧团小演员,而晚上,则是声色场的万人迷。

此外,女性的物化,同样是日本情色文化里的一大特点。
官能作家团鬼六的作品里,女性如玩具一般任人摆布,以他作品改编而成的《花与蛇》系列,便是其中的代表。
如今日本的情爱电影,在越来越注重感官体验的同时,内容上却越来越苍白。曾几何时,在怪异甚至变态的日本情爱电影里,蕴藏着深刻的哲思和人文关怀。

《砂之女》中,导演用囚困沙下的密闭空间,完成了一番社会寓言,展示了环境对人的异化;《禁室培欲》则借用“囚禁”行为,来呈示都市人精神世界的干涸;
《铁男》里,被钢铁侵蚀的男主角,生殖器变成了金刚钻,工业对人体的异化似乎已经是不可避免的进程;
三池崇史的《拜访者Q》里,淫乱和虐待,同样是对现代家庭中扭曲关系的“地狱级”展示。

美国:暧昧的极限
美国情爱电影,始终受到社会舆论和法规的管控。但在长期的限制之下,他们也成了最会在大银幕上打擦边球的国家。
美国电影,经常会给人一种“分不清究竟是电影色还是观众色”的感受,所谓淫者见淫,它们就是不捅破这层窗户纸,让观众自行体会。
早期好莱坞的歌舞片,其实就可看做是美国情爱电影的先行者,人们在银幕上争相目睹袒胸露背的女舞者,满足了“看”的欲望。

高抬腿和黑礼帽,也成了一个时代的标志。在《芝加哥》里,蕾妮·泽尔维格和凯瑟琳·泽塔-琼斯,以放纵和挑逗的姿态,将旧时代的撩人演绎成新时代的魅惑。
在《海斯法典》监管电影行业的漫长岁月中,美国电影连对白里的用词都不能太过露骨。
然而,强压之下反倒催生了不少蒙混过关的小伎俩,编剧们发挥自己的想象力,费尽心机躲过法典条规的限制。

比如梅·韦斯特就在由她主演的《我不是天使》等片里讲了无数的荤段子(但未使用一个下流的字眼),她那口齿伶俐的“荡妇”形象,同时俘获了男性观众和女性观众的心。
在“禁欲”的社会大环境下,人们对那类大打擦边球的电影毫无抵抗力,在电影院用笑声发泄自己被压抑的欲望。
在这个时期,同样有许多创作者需要忍受“有招不能使”的痛苦。

比利·怀尔德当属其中之一,所以,后来在《七年之痒》里,他才会挑衅般地猛加狠料,造就了一部“在纯洁的观众和‘有经验的观众’眼里截然不同”的电影。
有人说,文明就是把真实给包装起来。而包装这件事,没有人能比好莱坞干得更加漂亮。

在《本能》里,保罗·范霍文巧妙地运用莎朗·斯通的身体,将观众的注意力拉离真相本身;
《大开眼界》中,淫靡的气息在黑暗神秘的聚会中漫溢开来;《脱衣舞娘》则一边播撒着香艳,一边驶向“大团圆结局”。
美国情爱片数量不多,但优秀的作品也不少,其中尤以文学改编为甚。
菲利普·考夫曼的《布拉格之恋》改编自米兰·昆德拉的《生命中不可承受之轻》;库布里克和阿德里安·莱恩分别在1962年和1997年将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的小说《洛丽塔》搬上了银幕。

除了改编文学作品,美国情爱电影多半会选择时下的热门话题作为素材。
比如1987年的《致命诱惑》,就将镜头对准了一个外表光鲜、内里溃烂的婚姻,让彼时深陷婚姻危机的社会哗然,电影上映后叫好又叫座。
而这一“踩点拍片”以迎合主流观众群体的传统,直到前几年的《五十度灰》系列依然没有改变。

不同于商业电影一贯的“政治正确”,美国的独立电影倒是对情色抱着大胆的作风。
大卫·林奇的《蓝丝绒》里,丹尼斯·霍珀饰演的变态狂加深了影片的神秘和诡异;

大卫·林奇的女儿詹妮弗·林奇也不遑多让,她的《盒中美人》融入了日本情爱中的异色之感,描绘出一个近乎变态的爱恋,制造了一个情色的噩梦;
大卫·O·拉塞尔的《打猴子》,则将儿子与母亲之间的乱伦意味,处理得极为自然,完美地把握住了情爱和色情之间的那条界限。

意大利:自然的春光
意大利人的豪放全球闻名,据美国一家男性时尚网站调查,60岁以上的意大利人里仍然有32%的人过着定期的性生活。
从这一点上,我们就足以感受到亚平宁半岛的男女身上,那旺盛的欲望。

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何从意大利这个国度里,走出了如此多善于拍摄情爱片的大师:
贝托鲁奇擅长将一段段的情色关系放置在大时代的背景中,比如《革命前夕》,比如《戏梦巴黎》。

帕索里尼则始终将情爱电影当做宣扬政治立场的武器;而安东尼奥尼更为注重内心的探索,越到后期他越喜欢用情色来抒情,如《云上的日子》。
当然,不能忘了丁度·巴拉斯,单从情爱片的领域来看,他无疑是意大利的第一人。

如果说性是人类永恒的话题,那么情爱便是意大利电影里的基本元素。而意大利的情色,离不开美丽的女性,她们或高贵或艳俗,但绝对不卑贱。
她们往往有着圣洁的面容和丰腴的胴体(符合意大利人的审美)。尽管,这一类的女性形象是情爱片里的常客,但这同样也是整个意大利电影的传统。

比起骨感美,意大利电影一直是“肉弹”的天下。
《西部往事》里的克劳迪娅·卡汀娜;《八部半》里的妓女……对了,费里尼的电影中,总会有一个丰满到夸张的女性,不是妓女,就是母亲。
意大利电影在表现这一女性时,通常采用柔和的光线,配上一段深情的凝视,为伟大的女性打上神圣的光晕。

丁度·巴拉斯说:“性不是畸形的疯狂,而是快乐的源泉。”
在他老人家的电影里,尽是些热情奔放的女郎,没有精神上的包袱,只顾追求性爱的欢愉。而意大利电影的情色,大致如是。

他们继承了文艺复兴脱离束缚的传统,很少有压抑或阴暗的主题,更多以赞美和讴歌的姿态呈现出女性的美、性爱的美。
比如贝托鲁奇在《偷香》里,将17岁的丽芙·泰勒,拍成了一朵娇艳欲滴的花,透着纯洁无邪的诱惑;

安东尼奥尼在《爱神》里执导了名为《危险关系》的短片,片中沙滩上起舞的女人,有一种满注生命活力的灵动;
托纳多雷的《西西里的美丽传说》中,马琳娜独守空房时的舞步,艳丽而动人;
费里尼的《甜蜜的生活》中,安妮塔·艾克伯格在特雷维喷泉中的一幕,早已成为永久的定格。

在这些段落里,观众欲望中容易引发邪念的部分,仿佛被剔除得一干二净。
在帕索里尼的一些电影中,也对自然美表示了向往,比如在《一千零一夜》中,那些传说中的主角们,一个个都是“天然去雕饰”的主,对情欲之事揣着最为原始的态度和冲动。
韩国:唯美的情殇
韩国的情色诉求,总在风雨飘摇中晃动着。在1978年,韩国有一部名为《O孃的公寓》的影片上映了,该片彻底引发了人们对“女招待电影”的疯狂,一共迎来28万的观影人次。
当时,韩国正处经济飞速发展的时期,都市娱乐产业的腾飞,导致了许多处于社会下层的女性投身声色场所。

“女招待电影”以善良、漂亮的农村女性沦为妓女的故事作为卖点,满足了大部分人窥视、猎奇的欲望。以此为根基的情色文化应运而生,大众的反响也的确十分热烈。
然而,好景不长,就像当年被无数粗糙制作毁掉的“通心粉西部片”一样。七十年代末期,一大批质量极其低下的“女招待电影”,在韩国接二连三地上映,之前那些若隐若现的现实主义血液,被金钱的欲潮所稀释,只留下对观众的迎合以及吸引眼球的女色。

到了八十年代,为了迎接1988年汉城奥运会的来临,并给全世界展示韩国人的开放姿态(同时刺激经济的发展),当时的韩国总统全斗焕提出了“3S政策”。
所谓3S,即(Sex),银幕(Screen)和体育(Sports)。
在此契机下,韩国电影的审查力度被极大削弱,大银幕上充满了目的纯粹的软色情电影。

香港前几年《3D肉蒲团》的火爆程度,恐怕也只是韩国当时电影夜市的日常状态罢了。
据一位韩国学者回忆,那时的大学生,“白天向全斗焕的暴压政治投掷石块,晚上则享受全斗焕的自由化政策,在电影院看情爱电影”。
随着《生死谍变》拉开韩国大片的序幕,韩国电影实现了工业化的腾飞,十多年来,各种类型的电影都得到了长足的发展。

而在这之中,情爱片无疑是极为重要的一环。涉性题材的电影层出不穷,有将目标观众设为青少年的《色即是空》《梦精记》等性喜剧;
有专为都市白领打造的《吝啬罗曼史》《偷情家族》;有模仿《本能》的《夏娃的诱惑》系列;也有走“神秘艳遇”路线的《爱人》《甜性涩爱》等。

韩国情爱片的主题,大多离不开伦理。
《夏日时光》里,少妇对性的渴求,冲破了道德的枷锁;
《密爱》中,背叛丈夫的妻子,被另一个擅长背叛的男人诱骗;
《绿色椅子》里,相爱的两人不顾世俗的羁绊,相互迷恋。
不过,其中真正对人性或者对欲望本身的探讨显得空泛,大多是关于现代人(大多为都市人)的情欲悲歌。

在这些电影里,除了中产阶级式的人物设定以外,秀美的男女演员,考究的室内布景,到古典音乐的选取,看得出,都做足了商业考量,以讨好主流消费群体。
与商业味道较浓的情爱片相对的,是金基德、朴赞郁这类更注重个人表达的导演。
在他们的电影里,情爱内容表现为对伦理关系更加激进的“触犯”:
《老男孩》里的父亲与女儿;《弓》里的老人与少女;《圣殇》里的“母亲”和“儿子”……

此外,在画面表现上,韩国情爱片总是力求在情爱场面中营造出一种唯美感。
比如在《美人》里,素色的家具和纯白的床褥,消解了性容易引发污浊联想的那一面,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具有毁灭气韵的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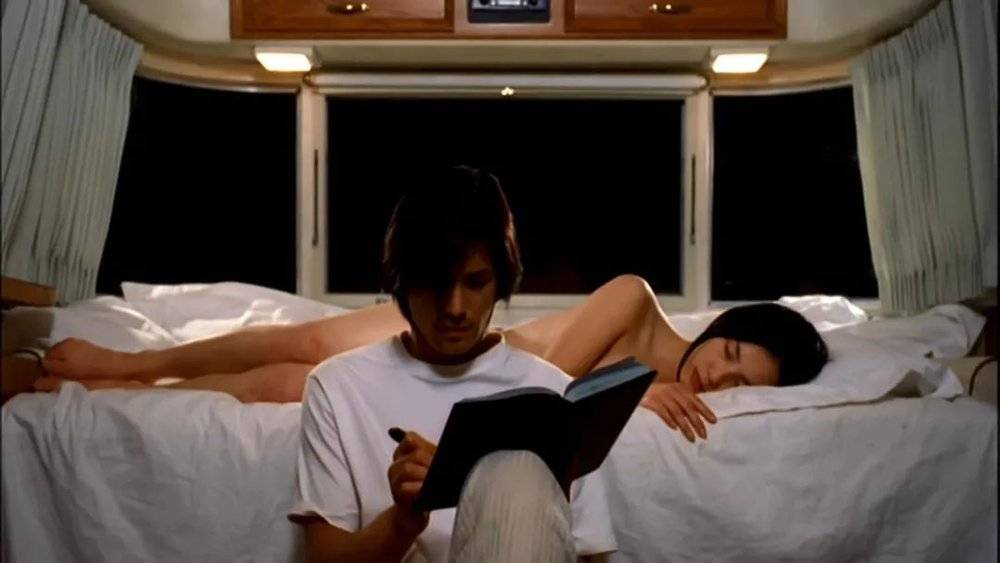
在大部分韩国情爱电影中,床戏拍得大胆又含蓄,大胆之处在于其特写和剪辑的凌厉,与男女急促的喘息相互映衬;
而含蓄之处,则在于大多数的情况下,他们什么都没露,但却能把观众看得面红耳赤、心跳加速。
各国情爱电影的魅力,在当下都能找到各自的观众。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看电影杂志(ID:moview_weekly),作者:东四环作家协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