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扫码打开虎嗅APP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经济观察报书评(ID:eeobook),作者:高广童,原文标题:《别无选择的辩护:律师为什么会占到“坏人”的一边?》,题图来自:《我们与恶的距离》剧照
律师为什么要替“坏人”辩护?可能每个刑事辩护律师都被问到过这个问题,特别是在故意杀人、性犯罪这类严重伤害民众朴素正义感的案件中,为嫌疑人或被告辩护的律师常常遭遇质疑、谩骂,甚至被叫作“魔鬼代言人”。
有人认为律师是为了赚取巨额律师费,在前不久的王振华涉嫌性侵幼女案中,王振华的辩护人被网友爆料称其收取了千万元报酬;不过同时有许多律师为被告提供法律援助,王飞律师就是其一,他不仅义务为被判故意杀人罪而遭羁押近27年、刚被改判无罪的张玉环申诉,而且承担了差旅费。也有人说律师是为了炒作、营销,以此拓展获客渠道,的确,时常有刑事案件成为舆论热点,比如近几年的“四川夹江公交车爆炸案”“杭州保姆纵火案”“于欢故意伤害案”,但实际上绝大多数刑事案件都是“不入流”的小案子,不会被媒体关注。
名与利,似乎无法为律师替“坏人”辩护提供足够的理由。那么,这个问题的答案是什么?辩护的正当性又在哪里?对此,英国刑事律师亚历克斯·麦克布赖德(下文称“作者”)所写的《律师为什么替“坏人”辩护:刑事审判中的真相与谎言》一书,通过他的切身经历为我们拉扯出一片现实而宽阔的思考空间。作者将自己作为菜鸟律师时经手的近30个刑事案件娓娓道来,通过呈现真实发生在律师事务所、刑事法庭和监狱的故事提醒读者,问题的答案并非如此简单。
“别无选择”的法律原则
根据英国的执业律师职业伦理,律师替“坏人”辩护是“别无选择”的。英国律师业标准委员会制定的指南规定了“不得拒聘”原则,这一原则要求执业出庭律师接到案件后,不得因当事人的身份和案件的性质而拒绝接受委托,也不得因律师本人对当事人的性格、名声、行为举止、是否有罪的个人看法而拒绝为其辩护。在“不得拒聘”原则指引下,律师在接受委托时,不需要考虑当事人是否可能有罪,作者和他的同事也不会因代理一个被指控杀人的客户而失眠。
在这种职业伦理的背后,有两个基本原则。一是刑事法中的无罪推定原则。每个人在被依法判决有罪之前都是无罪的。也就是说,直到经过一系列法定的刑事诉讼程序,才能作出被告是否有罪的判决。“律师为什么替‘坏人’辩护”这一问题提出者的一个预设是嫌疑人或被告事实上实施了犯罪行为,所以是“坏人”。
实际上,从实证主义的角度看,客观事实和法律事实是两个不同层面的问题。客观事实是不明确的,而法律事实则是一个关乎证明的问题。无论是警察、检察官、律师,还是陪审团、法官,没有人具备上帝般的全知全能视角了解客观事实是什么。因此,客观事实不是审判程序中讨论的问题。审判中关心的只是、也只能是证据呈现出的法律事实是什么,通过证据呈现的法律事实判断被告是否有罪。认定被告有罪适用的证明标准是“排除合理怀疑”,即只有起诉方提供的证据对被告有罪的事实的证明达到无合理怀疑的确定性程度时,方可裁判被告有罪。证明被告有罪的责任在控方。因此,审判的关键是控方提供的能够证明或不能证明被告是否实施了被指控的犯罪行为,如果能够达到“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标准,则被告在法律上是有罪的,反之则无罪。
另一个基本原则是人人平等原则。即便是实施了犯罪行为的被告也有权利聘请律师为其提供法律服务。根据宪法,被告有权获得律师的辩护,有权得到公平公正的审判。在对抗制的诉讼体制下,控辩双方都需要有人代表,从这个意义上看,代理刑事案件中的被告和民事案件中的被告没有什么不同。
防止无辜者蒙冤的关键制衡
在提出“律师为什么替‘坏人’辩护”这一问题的人看来,律师的工作可能就是为了把客户的有罪辩成无罪,帮助其逍遥法外。作者则通过讲述刑事法庭内外的一个个真实故事向我们展示了在对抗制的司法制度中,刑事律师的有效辩护有助于保证无辜者不会蒙冤。
在英国刑事司法制度中,警察、检方、法官、陪审团分别承担不同的制度角色:警察侦查犯罪、收集证据,检察署负责审查警察移送的证据并决定是否起诉至法院,陪审团或法官(非陪审团案件)根据法庭出示的证据作出有罪或无罪的决定。根据法律,律师的角色定位不是判断被告是否有罪,而是帮助法官和陪审团作出决定,确保被指控犯罪之人的宪法性权利和诉讼权利依法得到保护,其他各方正确地运用法律,防止无辜者蒙受冤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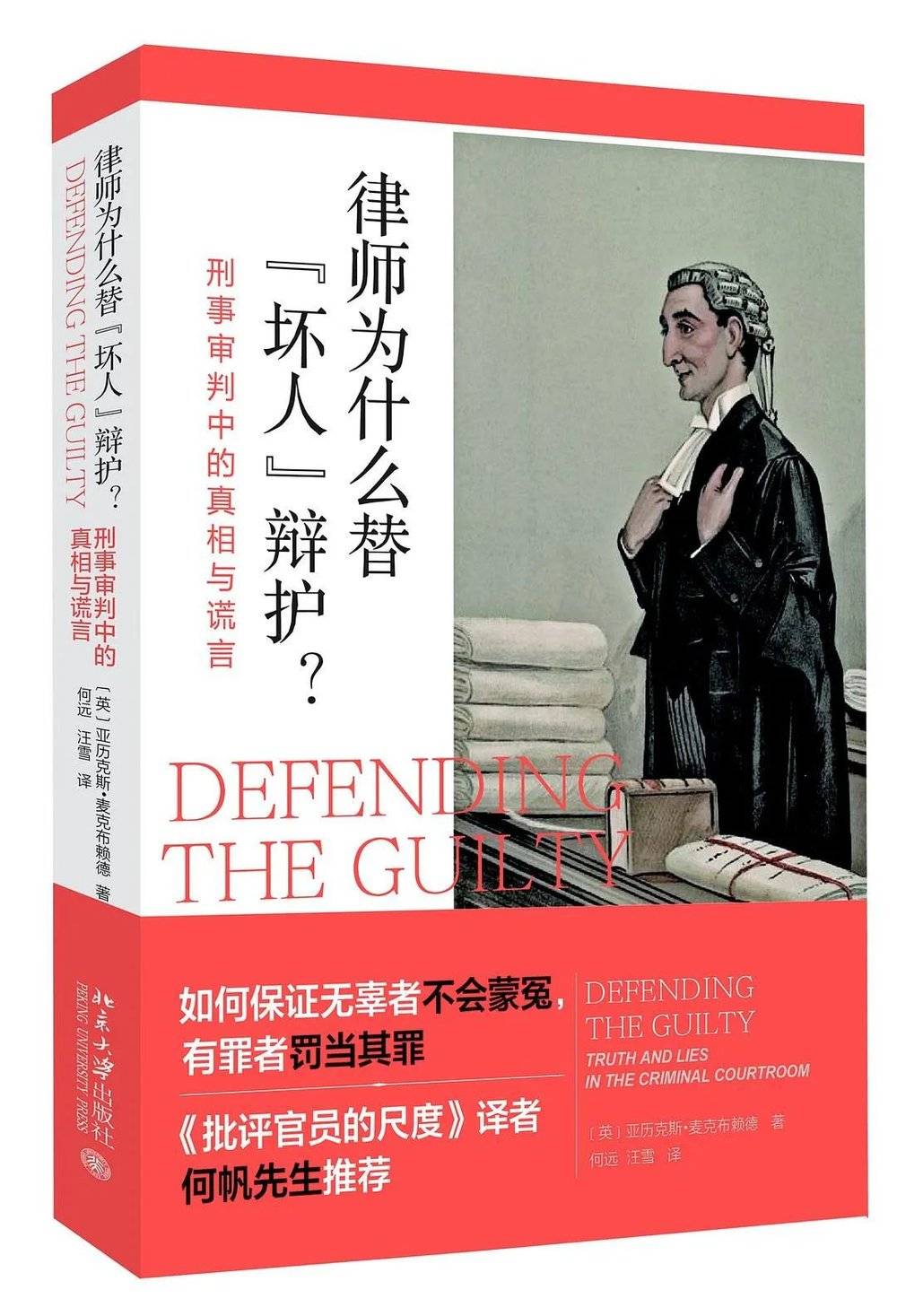
《律师为什么替“坏人”辩护》
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前大法官乔治·萨瑟兰曾说:“没有律师代理,被告就算完全无辜,也有定罪之险,因为他不了解证据规则,无法判断指控成立与否,也不懂得如何作无罪辩护。”司法实践中,无辜的被告被错误地定罪时有发生,作者认为这是最有悖于人的正义感的,是最典型的一类冤案。导致无辜者蒙冤的因素众多,比如警察非法取得的证据被采信,警察或检察官故意遗漏无罪证据,陪审团采信了虚假的证人证言。以检察官的滥用职权或失职为例。在英国,检察官的职责和动力是成功追诉。大量案例已经表明,检察官越是追求输赢而非公正,就越容易实施违法行为或者造成重大过失,但检察官很少因此受到惩罚,案件结果也常常不会受到影响。所以,防止冤案必须有对抗性的动力。
而最有效的对抗动力之一就是律师的辩护。作者的一位律师朋友有一次在开庭前接到指示,要求作为控方律师对一个涉及毒品和枪支的案子提起指控。在法庭上,这位控方律师却发现案卷中缺少证明被告有罪的最关键的物证——DNA证据和毒品证据,几经周折后终于在法院为皇家检控署设立的办公室里找到DNA证据和毒品证据,并立即提交到法庭。开庭后,辩护律师主张这些证据提交得太迟,不符合法律规定,如果允许提交则会导致审判不公正。结果是,辩护律师的意见没有被法官采纳,被告被定罪了。作者的朋友认为,这个案子的审判并不公正,因为当庭提交的证据导致被告没有时间指示辩护律师如何回应和质疑。尽管辩护律师已尽职尽责,但因为正义天平的指针天然地向控方倾斜,正义并没有实现。如果不存在律师为被告辩护,那么控方更没有动力把工作做好了。
“有罪者罚当其罪”的程序性角色
客户事实上有罪,并不意味着律师的工作就停止了。如果所有被逮捕的人、被起诉到法庭的人,在事实上都是无辜的,也就说明司法系统运转失灵了。事实上,许多嫌疑人、被告人在事实上和法律上都是有罪的。那么,律师的工作是什么呢?根据前面提到的人人平等原则,即使事实上实施了犯罪行为的人,也享有获得辩护的权利和其他诉讼权利,有权被依法认定准确的罪名,被合理地量刑,罚当其罪。但法律世界是经过复杂编码的,对于被隔离在刑事法律之门以外的普通人,又何以区分此罪与彼罪,何以了解正当防卫这类法定抗辩事由呢?受过专业训练的律师,可以结合证据、法律和客户的指示,依法进行罪轻辩护或者量刑辩护。
不仅如此,律师可以凭借其法律知识和技术帮助客户理解法律,通过分析各类行为的法律后果来帮助客户作出更合理的选择。在作者办理的一个性犯罪案中,被告赫伯特被指控性侵两名未成年女孩,赫伯特如许多性犯罪者一样,并不打算认罪。作者在审查了控方证据并考虑到赫伯特的犯罪前科等因素后,认为有罪证据难以削弱,赫伯特将会被定罪。会见时作者给出了自己的专业意见,对认罪与否的后果分别作出说明——若承认对女孩们实施了性侵行为,则构成供认,极有可能不会入狱,年幼丧母的女儿将有爸爸陪在身边;若不认罪,则入狱可能性极大,女儿也将被送去教养院,并可能无法通过即将到来的考试。经过考虑,赫伯特选择了后者。最后,他的认罪和他的女儿使他被定罪但免予监禁。
另一个问题是,律师的辩护会帮助罪犯逍遥法外吗?律师为事实上实施了犯罪行为的人竭力辩护,看上去似乎帮助了罪犯脱罪。然而律师的辩护是为刑事法律体系正常运转、实现正义的必要成本。因证据不足,逍遥法外的犯罪人总是存在的,在一些案件中,如果没有律师的介入,犯罪之人可能会被定罪。例如,警察闯入了某人的家,在他家中发现了一公斤毒品。律师提出,根据法律规定,非法取得的证据不能作为证据使用,而警察没有搜查证,所以这些毒品证据应当被排除,不能作为定案根据。结果,持有毒品者被判无罪。
这种情况下,律师的辩护是否促进了法治呢?作者的答案是肯定的。司法不仅应当保证有罪者罚当其罪,而且必须符合程序正义,判决一个人有罪必须符合正当程序,而律师的角色就是程序性的。警察的违法取证,侵害了被告的诉讼权利,违反了程序正义。所以,律师的辩护形成了对抗性的关键制衡力量,在诉讼制度层面抽象地促进了法治,使警察、检察官、陪审团、法官勤勉尽责,依法而高效地扮演自己的角色;警察依法全面搜集证据,检察官更加审慎地审查每一份证据,在下一个案件中不再放纵犯罪,也不再冤枉无辜者。
宁愿声名狼藉,也以刑事辩护为业
律师为包括“坏人”在内的人辩护不仅是职业伦理的要求,而且这种制度设计也是法治的成本,它不仅能够有助于正义的实现,而且能够促使正义“以看得见的方式”实现。这听上去像是一个标准答案,作者自嘲“虽然完全正确,却也十分平庸”。在这些标准答案之外,从作者对案件的讲述、办案的感悟以及穿插其间的英国刑事诉讼制度史片段的回顾中,其实还可以读出作者比较私人化的解释,这些真实、诚恳的理由,也是作者做刑事律师的动力。
一些刑事律师为促进人权和法治而走上刑辩之路,作为刑事律师,作者也因能为弱者发声、帮助正义的实现而感到欣慰。在作者代理的沃尔特案中,19岁的被告沃尔特自从9岁母亲离开后就进入福利院生活,挣扎在生活的边缘。作者在庭审交叉询问环节犀利地攻击了控方证人证言的可信度,有效削弱了证言的证明力,最后沃尔特被认定无罪。作者感慨道,“有生以来第一次,他赢了。他没有失去理智,获得了信任。他现在是否终于发现了一些自我价值,即使只是持续一个下午的时间?这会激励他扭转自己的人生嘛?我不知道,但是,我相信,我不仅仅看到了正义的实现,而且为此提供了帮助。第一次,我觉得这或许是我终究还是有能力从事的一份职业。”
尽管如作者所说,出于“职业荣誉感”,律师们往往偏爱报酬更高、更受关注、更臭名昭著的案件,但和刚提到的沃尔特案一样,作者经手的案子大多缺少扑朔迷离的案情,也没有声名显赫的被告,案子多数都是很普通的,被告也几乎都是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甚至是边缘人。用作者的话说,“不入流的律师,为不入流的罪行辩护。”没有人是天生犯罪人,一些犯罪人本身就是社会不公正的受害者。
书中写到,在监狱服刑的大多数罪犯就是从社会裂缝中不断下落的失败者:65%的人阅读水平低于11岁儿童的平均水平,2/3的人在入狱前无业,1/3的人无家可归,66%的人吸毒,63%的人酗酒,接近3/4的人患有某种心理健康疾病。
这些普通的刑事案件,关涉的是普通人甚至底层人的命运和自由。尽管在收入不菲的商事律师们看来,刑事律师只会处理低端业务、工作内容和性质低劣,但于作者而言,能够有机会走进被告纷繁各异的人生是刑事律师职业的独特迷人之处——“吸引我的,是从旁听席上发出的大声呐喊,是道破内情的沉默不语,是激烈的情感爆发,以及出示证据时的目瞪口呆,而这时候的一波三折着实会令人瞠目结舌。刑事法庭令人迷恋不已,因为充盈其间的是人的境况。他们要穿过半真半假的陈述、各式各样的悲剧、苦不堪言的厄运、倒霉透顶的谎言、不堪忍受的愚蠢、无边无垠的贪婪和极度缺乏的自控,用敏锐的目光捕捉揭露实情的细节”。
虽然关注这些底层人的命运,但作者也坦言,他的认识仅局限于刑事法庭。对律师来说,有期徒刑显得抽象。作者为此拜访了专门帮助刑满释放的罪犯重新回归社会的慈善机构负责人博比·卡明斯——一名已刑满出狱的职业杀手、持枪抢劫犯。卡明斯在监狱中的经历让作者感受到,威慑、剥夺再犯能力和矫正这三个监禁最基本的功能在实际运作中全部收效甚微。监狱的环境容易让人变得残忍,监狱对犯罪人施加的伤害可能比犯罪人对受害者施加的伤害更深。
在当前的政策之下,监禁更强调惩罚,而如果不向出狱的犯罪人提供更多的谋生技能和机会,监狱和再犯罪之间的循环则难以被打破。因此,使客户获得减轻量刑的判决,以避免陷入这个恶性循环之中,也成为律师辩护的一种动力。
作者毫不掩饰地说“胜利会让人上瘾,你不仅想获胜,还想赢得惊世骇俗。激发律师积极性的既包括献身正义的理念,也包括击败对手的喜悦。”
像其他出庭律师的日常工作一样,作者根据法律、案情和客户的指示,从实体和程序上去质疑、动摇控方的有罪证据体系,为客户提出每一个法律上的辩护理由。作者有案子时的状态也会像英剧《皇家律师》的女主玛莎所说的“律师就是不睡觉,不微笑,不拒绝”,能赢得胜利并不容易。
在英国基层法院审理的案件中,68%都以定罪结案。刑事律师的手中没有国家公权力和国家资源,与警察、检方、法院相比天然地处于弱势,他们“整天生活在焦虑不安之中”,在只身与之对抗时唯一的依靠是专业技能和智慧。另外,不能忽略的一点是,律师也会出现失误。
与公众印象中所向披靡、似乎永远无所不能的律师形象不同,书中展示了律师的另一面:作者在第一次庭审中表现糟糕,糟糕到被同事称为“失败者”,作者也因此怀疑自己能否胜任刑事律师工作;即使在执业一段时间后,作者也曾判断失误,一次失败的辩护策略选择导致了一名客户被判有罪。刑事诉讼中,审判结果永远无法预知,而获胜会让律师感觉良好,成为律师的动力补充剂,为下一个案件寻求一线生机储备能量。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经济观察报书评(ID:eeobook),作者:高广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