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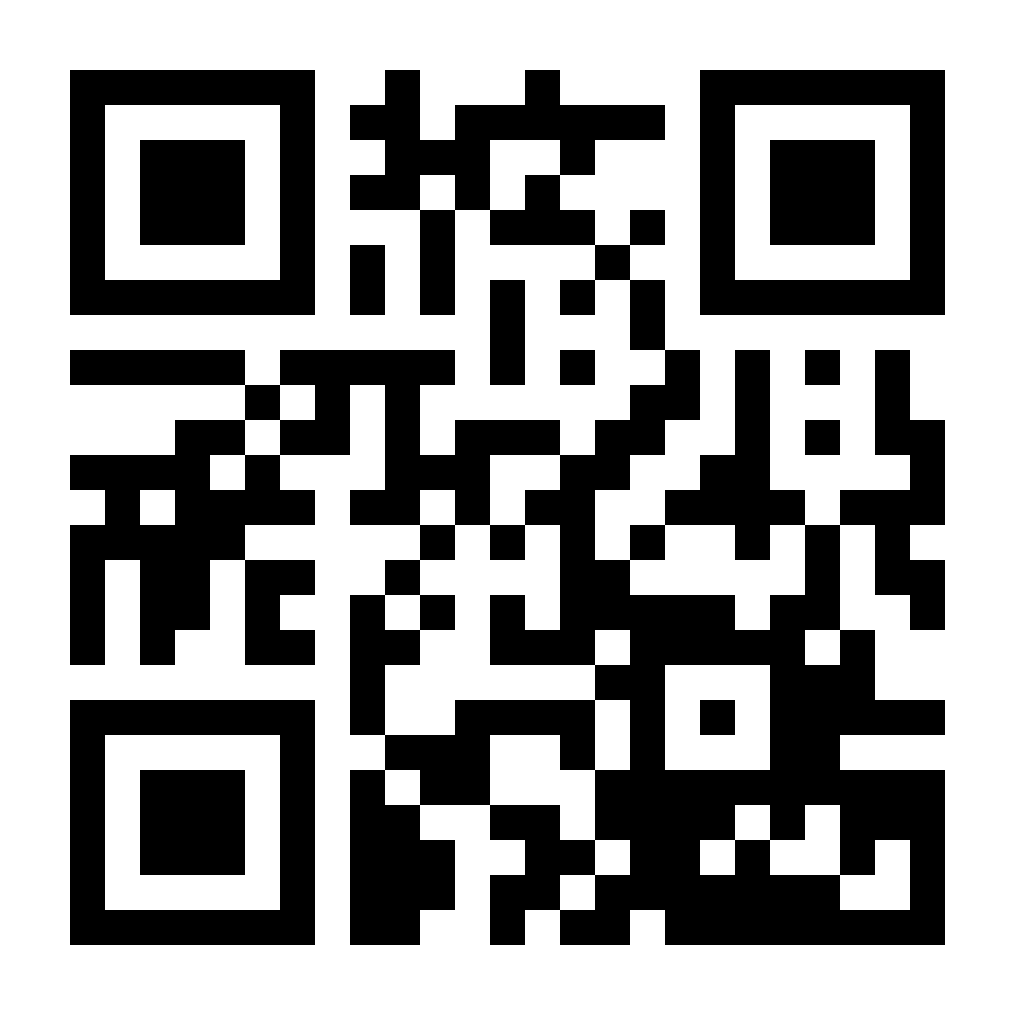
扫码打开虎嗅APP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经观书评,作者:邓安庆,题图来自:电影《赎罪》剧照
“可是这年代什么叫有罪呢?这个问题已经没有意义了。每个人都是有罪的,每个人都是无罪的”。
一
很多小说家的文学生涯开始于写自传。毕竟我们最熟悉的就是自己,以及与自己相关的家人和朋友,写起来也得心应手。等积累到足够的写作经验后,才慢慢地把笔触伸到其他人的身上。这个过程就像是学骑自行车,一开始需要有人在后面扶着你往前骑,等掌握了技巧后,扶的人松了手,你也可以自由地骑行了。而麦克尤恩,这位写了一辈子别人人生的小说家,在创作生涯的末端把目光投向了自己的人生,出版了《钢琴课》。

虽然他在采访中表示“《钢琴课》不是自传”,可他也承认“攫取了自己的人生片段”,“关于家庭生活、我失散的哥哥、寄宿学校等等”,毫无疑问是最具自传色彩的一部作品了。就感觉是一位一开始就能潇洒骑行的自行车手骑了一辈子,到了晚年突然需要有人在后面扶着往下骑。这种反差感,饶有意思。
熟悉麦克尤恩作品的读者都知道,2001年他出版了《赎罪》,这是一部时间横跨了60年之久的长篇小说,篇幅在其作品系列中是最长的。之后的这些年,他一直着力于写10来万字左右的小长篇,而《钢琴课》一出手就是近30万字,以男主人公罗兰·贝恩斯的一生为主线,通过他的视角,串起了二十世纪一系列影响深远的重大历史事件,包括美苏冷战、古巴导弹危机、撒切尔夫人上台、福克兰群岛战争、柏林墙拆除、切尔诺贝利核泄漏、工党当选以及英国脱欧等,时间跨度同样是60年之久。

《赎罪》是一部成长小说,《钢琴课》也是如此,只是这一次我们可以看成是麦克尤恩本人的成长史。在此,我们不必拘泥于小说中写到的事件是否真的发生在作者的生命中(很显然,我们不能把小说当成自传),而应该看到小说主人公罗兰·贝恩斯各个人生阶段的经历与麦克尤恩本人是高度契合的,甚至你完全可以把作者的形象投射到罗兰身上。不妨大胆地说,那个在后面扶着车座的人,就是麦克尤恩本人,他对自己人生的回望,全都融入作品中去了。
是什么契机让麦克尤恩决定写这本书?答案就在此书看起来平常无奇的献词里:“献给我的姐姐马琦·霍普金斯/献给我的哥哥吉姆·沃特和大卫·夏普”。马琦·霍普金斯和吉姆·沃特,是麦克尤恩的母亲罗丝与其前夫欧内斯特·沃特所生。
欧内斯特参加二战期间,罗丝与大卫·麦克尤恩相爱,1942年生有一子,随即送人领养,即献词中的大卫·夏普。1948年,已经结婚的罗丝和大卫·麦克尤恩生下伊恩,也就是作者本人。2002年左右,大卫·夏普发现自己与著名作家伊恩·麦克尤恩是同父同母的兄弟,两人随即相认,此事还被媒体报道过。
大卫·夏普出版有回忆录《完全放弃》,由麦克尤恩做序。回头再看《钢琴课》,主人公罗兰的父母同样是在二战期间相遇,罗兰母亲同样与前夫生有一儿一女,与后来的丈夫在罗兰之前育有一子,刚满6周就被送走。母亲临终前,罗兰与失散多年的同胞哥哥罗伯特相认……麦克尤恩几乎照搬了现实中的人物关系。
不过通读完作品,我们会发现“兄弟相认”并非整部小说所要书写的重点。或许一开始麦克尤恩就想写一个围绕“母亲为何要送走哥哥”的故事,可是构思到后面,便逐渐发现了宏大的历史是如何具体地影响到个人的命运,包括他的母亲,他被送走的哥哥,也包括他自己。
具体到作品里,罗兰·贝恩斯作为一个普通的英国公民,有意无意地参与和见证了二十世纪至二十一世纪的大部分重大历史事件,他的人生在其中被影响被改变被形塑。
重大历史并非遥不可及,它就是能以巨大的能量辐射到一个个微小的个人,并以各种偶发事件改变人的一生,正如书中所写:“罗兰偶尔会想,哪些大大小小的事件改变、决定了他的存在呢?个人的、全球的、微不足道的、惊天动地的——他的存在并非例外,一切命运都是这样构成的。”
二
全书塑造了一系列形象鲜明的女性形象:钢琴课女教师米里亚姆、前妻阿丽莎、阿丽莎的母亲简·法尔莫、罗兰的母亲罗莎琳德,以及挚友兼伴侣达芙妮。麦克尤恩以罗兰的人生为主线,以这些女性的命运为支线,回过头来再让这些女性对罗兰产生影响,其中影响最深远的有两位,一位是钢琴课女教师米里亚姆,一位是前妻阿丽莎。
先来说米里亚姆。在情窦初开的少年时代,罗兰在学校遇到了钢琴老师米里亚姆·康奈尔。这是一位严格的老师,而罗兰也会是一位优秀的学生。如果没有出现后来的事情,罗兰本来可以成为一位杰出的钢琴演奏家。
他跟米里亚姆一起演奏莫扎特和舒伯特二重奏,《东部日报》上有人发表评论文章,“我预测,十年之内,罗兰·贝恩斯将会成为古典音乐圈鼎鼎大名的人物。他风华正茂。观众知道他的才华,喜爱他的才华,起身向他致敬。整个集市广场应该都能听到观众的掌声”。
可是,米里亚姆引诱了罗兰,“他年纪还小,并不懂得什么是占有……她二十五岁,也很年轻,但他才十四,怎么能知道这一点呢?她的聪明,她对音乐文学的知识与热爱,他安全地位于她掌控中时她所表现出来的活力与魅力——这一切掩盖了她的绝望”。
这就是不可饶恕的罪行。而罗兰在当时并未意识到自己是个受害者,“他为此高兴,他受到了额外眷顾,感到很骄傲。他的朋友们只能做梦、打趣,而他已经把他们抛在身后,跨过了地平线,到了看不见的天边,然后又跨过了天边之外的地平线。他相信自己进入了某种超凡脱俗的状态,其他人恐怕永远也不会达到”。
米里亚姆妄图控制和占有他,把他关在自己的房子里,不让他去学校,只许他穿着自己准备的睡衣,“我爱你。我非常爱你。你属于我,不属于任何其他人。你是我的。你要一直是我的。你明白吗?罗兰”?到后来,米里亚姆甚至提出要跟罗兰结婚。
如此疯狂的行径,把罗兰吓坏了,他忍不住反抗,最后被赶出去时狼狈不堪。结果,罗兰的大好前途被毁了,“大多时候在小建筑工地上干活,同时还在罐头加工厂做事、当游泳池救生员、遛狗、还在一家冰激凌仓库上过班。酒店大堂琴手、网球教练、休闲指南杂志评论员,这些都是后来的事”。
麦克尤恩太擅长写人与人之间的情感幽微处了,并从其中呈现出人性的复杂。在一个细节中体现得尤为明显——到了晚年,有警察上门,希望罗兰能出来揭露老师的恶行,他也真的找到了老师的家,“在对峙过程中,他们不敢谈论将他们连接在一起的东西,那令人痴迷、将人吞没、重重叠叠、无穷无尽的快乐,尽管那既不合法律又不合道德,能叫人万劫不复。……爱的记忆一直与罪行无法分割。不能去报警”。
这段关系终结了他的学校学习,扭曲了他和女人的关系,最后以荒唐的终曲收场。如果再重来一次,他是否希望那一切都不曾发生,他也没有现成的答案。这就是伤害的程度,且是终身伤害,哪怕到了人生的末尾,还没有完全愈合。那段经历一直跟着他,他无法割舍。
三
另外一段无法割舍的情感,存在于他与前妻阿丽莎之间。这也是全书写得最精彩的部分。小说一开始,罗兰的形象就是一个被妻子抛弃还手忙脚乱带着孩子的可怜男人,他甚至还被警察怀疑是嫌疑犯。而他妻子阿丽莎抛弃他的理由后来也知晓了,她受不了这种庸常的婚姻生活,“我上了楼,躺在床上,太累了,根本睡不着。
这时候我突然想到,我在过我母亲的生活,一步不差地重复她的道路。有一些文学上的抱负,然后恋爱了,然后结婚了,然后生了孩子,旧时的梦想破碎了,或者遗忘了,未来能一眼看到底。还有怨恨。她的怨恨,我会继承下来,这让我感到惊恐。我能感觉到她的生活跟在我身后,死死抓住我,要把我和她一起拖下去。这些想法挥之不去”。
她决定离开,去成为一个作家,“我这辈子总得创造点什么,而不仅仅是造个孩子”。面对被抛弃的丈夫罗兰,她认为,“你是个好父亲,劳伦斯还很小,我知道他会没事的。他也会没事的,迟早会没事的。我那时候有事,但我已经做了选择,做了我该做的事”。
如果站在婚姻的角度,我们当然可以指责阿丽莎是一个不负责任的妻子,也是一个失败的母亲。这就涉及了性别的议题。在现实中,我们见识过很多男性艺术家如何对待妻子、情人,以及他们共同带到这个世界上的孩子们。
在晚年,罗兰参加了一个讲座,活动结束,有个读者认为,“男人们有了正当理由,以他们的艺术、他们的更高追求为幌子,抛弃责任、发生私情,或者酗酒、使用暴力。历史上,女人为了艺术而牺牲别人的情况很少,而且他们很可能会受到严厉谴责。为了成为艺术家,女人们更可能让自己妥协,放弃生孩子的权利。人们对男人的评判更加温和。在艺术领域,无论是诗歌、绘画还是别的,这不过是常见男性特权的一个特殊例子而已。男人们什么都要——孩子、成功、女人对男性创造力的无私奉献”。
到了罗兰这里,性别发生了翻转,他成了被牺牲的那一方。在他看来,妻子阿丽莎,“你想要谈恋爱,你想要结婚,你想要孩子,全部都如你所愿。然后你说你要别的东西”。这对罗兰来说,太过残忍。而阿丽莎,在后来的见面中反问他,“要创造,要当艺术家、科学家,要写作、绘画,历史上对女人有多难,你能有哪怕一丁点儿的理解吗?我的故事对你没有任何意义”?这让罗兰无言以对。
更让罗兰难受的是,如果阿丽莎抛弃了自己和孩子,结果只写了一部平庸的小说,那事情要容易得多。那他就可以尽情地释放鄙夷。可是,他看到阿丽莎的《旅程》这本书,意识到这是一本杰作,如果还让她困在婚姻和那栋小房子里,不可能写出来的,“没有人能在那样的房子里构思如此宏大而又如此精巧的作品。除非房子里就她一个人。……为了她的美妙文字,他必须原谅她。这和不原谅她一样令人难以忍受”“危险的是,事情说白了就是:他已经爱上了她的小说,而且因为她写了这部小说而爱她”。
阿丽莎从《旅程》之后,佳作不断,逐渐成为了世界知名的大作家。阿丽莎每本书出来,罗兰都会去读,“他对前妻的怨恨藏在思想的地下室里,与对她作品的崇拜之情缠斗厮打”。他发现前妻在小说里从来没有写过他,哪怕是以变形的方式都没有,“他们的共同经验从她的想象世界中被彻底推平,包括她自己的失踪。他被抹去了。劳伦斯也是——她的小说里没有孩子”。
绝情如此,让罗兰难以释怀。由此引申出一系列疑问:艺术家和小说家往往无情,我们该不该为了他们的艺术,而原谅或无视他们的任性与残酷?他们的艺术成就越高,我们是不是就更加宽容?对阿丽莎抛夫弃子行为的看法,该不该因为其写出一系列杰作而更加温和一些呢?对读者来说或许无所谓,而对当事人,残酷的行为本身不会改变。罗兰最后得出结论:阿丽莎的小说精彩绝伦,她的行为不可饶恕。
不可饶恕,我愿视为隐藏在全书内里的一个关键词:童年的伤害、婚姻的破碎、情感的背叛,乃至更宏观的,战争的残暴、政治的无情……都是不可饶恕的。《钢琴课》的原著书名是Lessons(教训、经验),直译过来书名可以是《教训》,这教训既是主人公罗兰这一生经历的一个又一个教训,也可以是动荡不安的历史带给人类的一个又一个教训。
这些教训,无一不是惨痛的,哪一个是可以轻易饶恕的罪行?麦克尤恩曾在《赎罪》里发出的质问,同样适合放在这里,“可是这年代什么叫有罪呢?这个问题已经没有意义了。每个人都是有罪的,每个人都是无罪的”。
年轻的时候,麦克尤恩曾被许多读者称为“恐怖伊恩”,因为他惯于用冷峻幽暗的笔法来勾绘现代人的恐惧和不安。到了这一本《钢琴课》,看起来柔和了不少,甚至有不少温情脉脉的描写,但其底色是苍凉的。真正恐怖的不是怪力乱神之事,而是透过这寻常人生看到了让人难以忍受的真相。从这一点来说,麦克尤恩从来都是一个毫不留情的小说家。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经观书评,作者:邓安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