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扫码打开虎嗅APP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陀螺电影(ID:toroscope),作者:徐若风,头图来自:《天桥上的魔术师》剧照
《天桥上的魔术师》,也许是今年以来我国台湾声势、阵仗最为浩大的剧集。
不过在内地,它却几乎没有什么讨论的声量。
就个人对前六集的观感,可以下的判断是:你可以错过去年金马奖的任何一部台片,却不能错过这部台剧。

《天桥上的魔术师》海报
剧集改编自吴明益的同名短篇小说集,以他小时候成长的八十年代台北西门町中华商场为背景。
小说将众多人物的成年追溯视角视作起点,“移步换景”式地拉扯出他们曾经的记忆。
转换视角间,便是真真假假的记诉、虚构与现实的分野,从而轻巧地带出时间流逝之感。

《天桥上的魔术师》剧照
此书在台湾的文学界本就引发过诸多的讨论,又在《血观音》《女朋友,男朋友》的导演杨雅喆的执导下,斥巨资耗时五年改编。
其一经开播,自然能在台湾影引发巨大关注。

杨雅喆
简单地总结,《天桥上的魔术师》中的每个短篇都会换一种样貌,吴明益通过魔幻现实主义的风格,才能统摄起书中冗杂分立的多种小说类型。
无论是梦幻细碎的都市怪谈“外包装”,还是这些断裂分散、以一个个“记忆体”呈现的故事,亦或者是其中影影绰绰的隐喻……它们的影像化难度都很高,更难以被剧集这种方式所结构。

《天桥上的魔术师》剧照
看完小说,我更要惊呼的,是杨雅喆的改编之妙。
相对而言,剧集非常注重类型化与结构上的“移花接木”,呈现出的是一个主支线分明,如一幅散点展开又能相互咬合的拼图。

《天桥上的魔术师》剧照
开篇两集,故事从孩童视角出发,对商场中的几个主要家庭与魔术师的整体形象进行铺陈。
在台湾庶民剧的外壳之下,魔术师的介入,轻松打破了整体风格的界定。
传说中,在99楼,人可以看到自己曾经失去的最爱的东西。
在那里,一切曾经消失的东西都会回来。掌握上楼途径的,就是由庄凯勋饰演的魔术师。

《天桥上的魔术师》剧照
这位魔术师的形象,在每个角色的眼中都不尽相同。
他能猜测人的内心、预知未来,甚至将现实翻手为云覆手为雨。
他像是流浪汉,又有点像死神,或者是心灵读测者。
但无论他是谁,他总是能改变人的一个生活瞬间,将角色引向命运的岔路口。

《天桥上的魔术师》剧照
而从第三集“水晶球”开始,杨雅喆则显示了他“出人意料又在情理之中”的一面(毕竟是拍《血观音》、《女朋友,男朋友》的导演)。
剧集犀利地揭开戒严时代的恐怖与伤痛,是如何持续地影响着每个人;同时又将解禁开放后,那种“由冷到热”的动荡感与压迫感倾泻而出。
不由地感慨,片头罗大佑的一曲《之乎者也》,配以八十年代台湾的新闻老照片,其中的寓意,就是将民众的沉默与爆发,以及随之而来的一片虚无,给刻画出来。
第三集中的两个奇幻之物,分别是猫妖与水晶球。
前者是寄居在唐先生西装店天花板的猫,能听懂人话,更能召集群猫,幻为男性的形态。
后者是魔术师卖给锁匠家的大儿子阿派的宝贝,转到某个角度,就能看到人心中的“至尊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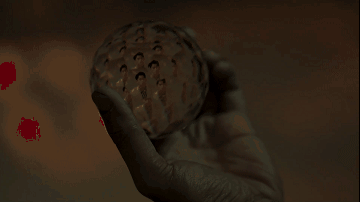
这两件奇物都与这一集的主角阿派息息相关。
他陷入进了一场三角恋,与衣店的实习生阿猴共同追求眼镜店家的女儿,却在追求失败后逐渐发现,让自己怦然心动的实际上是阿猴。
而令人意外的是,原来阿派的心里住着的也是一只猫。
一个人要如何定义“喜欢的原因”?
在杨雅喆这里,答案是:“不单是那个人,还包括了与对方相处的时间以及场域的氛围。很多人在青少年时会有个要好的朋友,那个人让他心动过,可是除此之外,他这辈子可能不会再遇到同性有那样的感觉。我不觉得剧情应该被写成同性恋,我觉得它应该更模糊。”

也就是说,杨雅喆并没有以同志题材先行切入处理,同理于第六集中鞋店家庭的哥哥Nori的女装倾向。
魔术师给了他一盒心愿火柴,有些像安徒生的《卖火柴的小女孩》——
在火柴里,Nori能看到自己渴求的人生,那绝不是自己每天都要在人前伪装成“直男学霸”。
阿派与Nori两个男生所要面对的,是青春期模糊取向。性取向的不固定,随着他们人生的改变而产生波动。

而他们引出的,则是当时社会压迫下,性取向固定者所遭遇的矛盾与纠葛,也就是另外两个被留白的“幕后故事”——
袁富华饰演的西装定制店老板唐先生,猫妖即是他对男生情欲的投射。
而商场中唯一的一间需要推门方可进入的店面,也说明着这个角色日常的封闭状态。
被大家发现怀有女装倾向的小八,他的身份是无法结婚的迁台老兵的养子。
 《天桥上的魔术师》剧照
《天桥上的魔术师》剧照
岁数可以当他爷爷的老兵都可以接受他的倾向,但他却被一群不谙世事的年轻人霸凌致死。
隐匿自我所带来的窒息感,在第四、五两集中迎来了更高潮。
第四集“石狮子”开篇,就以荒腔走板的儿童舞台剧形式,暗示这集将涉及戒严末期白色恐怖的留存。
当时,有关人等通过搜查、禁止自由书籍,并派驻监察队对商场进行监视,对违规者予以制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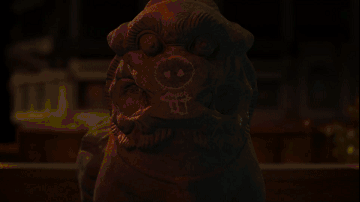
阿派的弟弟阿盖,被锁匠爸爸送了一把“神奇钥匙”,而这钥匙竟在自己的恶作剧下,可以打开庙门口石狮子的内部。
这让阿盖可以躲进它的身体中,暗中监视商场的各个角落。也就是在监视的过程中,他发现了监察者正在监视私下印制进步刊物的书店一家。
会移动、监视人的石狮子,实则是阿盖自己的梦游幻症。

现实揭晓之时,也是监察队的迫害与书店一家人的倾覆之时。
一场大火夺走了书店一家四口中三口人的性命,唯一幸存的女孩佩佩,还要独自面对无法走出的阴影和监察队的持续监视。

《天桥上的魔术师》剧照
“生老病死,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
取自《金刚经》的这句话,也即是剧中“时间”的替代密语,成了治愈在高高悬置的时代恐怖中留下来的人的“药引”。

越往后看《天桥上的魔术师》,越会发现这部剧集与小说的核心,在于“消失”。
消失的物,消失的人,消失的情感与记忆。
因为消失,才变得更加刻骨铭心。
反观中华商场,它实际上一体两面,同为“记忆模型”与“田野现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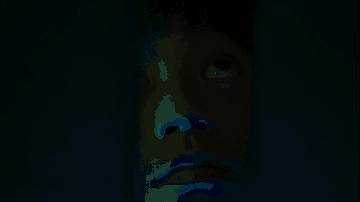
这座即将消失的商场,看似是所有故事发生的背景舞台,是魔幻发生的特殊地域;
但它并不是真正的幕后对象,因为它本身也是台北的缩影,更进一步说,它其实成为的是“台湾之于世界”的隐喻。
正如小说开篇所引述加西亚·马尔克斯的话语——
“我真正想当的是魔术师,但我变魔术的时候会很紧张,只好避难于文学的孤独中。”
换言之,许多无法明说的情感和记忆,作者将用“文字的魔术”把消失的过往给“变回来”。

《天桥上的魔术师》剧照
因此,《天桥上的魔术师》并不只是一部简单的、复刻这种末代商场情怀的“怀旧小说”。
它是通过集结这一个个似幻似真、消失又存在的年代故事,见证台湾自戒严时期之后,社会整体的遗存与变迁过程。
在这个过程中,虚幻的魔术达成了对现实的隐喻,而可爱又残酷的叙述质感,则勾连起故事与记忆之间的鸿沟。
小说对时代背景中高悬的恐怖给予适当的留白,也并不对具体的社会议题进行深入探讨。

而与之不同的是,创造一个时代暮色下,更显残酷的“梦游世界”,是杨雅喆的野心。
当时,社会看似即将翻开新篇章,但这种过往遗留的毒害与面向未来的希冀,仍旧持续地对抗着,隐秘在日常生活里,令人感到“忽冷忽热”。
当梦游将醒,就会发现,原来我们的这个世界仍是如此冷酷,容不下多元与真实的声音。
现在台湾的发声环境虽已截然不同,但那个残酷时代的影响却从未消失。
“消失”的另一层面,则在于故事、记忆与现实世界之间的关系——消失,才是真正的存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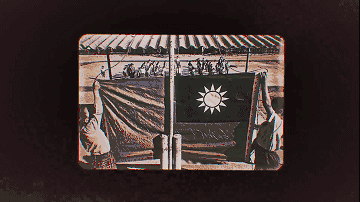
吴明益把自己写作的秘密,藏在了这部短篇集的最后几段话中:“故事并不全然是记忆,记忆比较像是易碎品或某种该被依恋的东西,但故事不是。
故事是黏土,是从记忆不在的地方长出来的。
故事听完一个就该换下一个,故事会决定说故事的人该怎么说它们……只有记忆联合了失忆的部分,变身为故事才值得一说。”

魔术师真的存在吗?
如果仔细阅读过原著,你可能会得出这样的答案:同时存在与消失。
所谓的“魔术师”,就是每个人对于逝去往事的记忆。我们都会长大,渐渐遗忘自己小时候为之激动的一个个“魔法时刻”。
但是,那些在幻想中产生的幻象,它们并没有在我们的身体里消失。

《天桥上的魔术师》剧照
在一次访谈中,杨雅喆说了一个很有趣的改编历程:编剧团队在改编原著的过程中,书写了非常多全新的细节与桥段,渐渐地,又把这些当做是原著里本来就有的内容。
而这其实是反复阅读原著从而产生的幻觉。
“一如小说里面长大的童年伙伴聊着往事,却总是无法拼凑成同一个故事。
原来记忆会随着时间过去,产生不同版本的‘真实’……发酵出了另外一个版本的‘八十年代台湾众生相’。

《天桥上的魔术师》剧照
那时我忽然明白:每个人心中都有属于自己的独一无二的魔术师,因为感动,所以执着地相信自己的故事才是真实的。”
这种虚实相间的创作历程,启发杨雅喆将整部作品的核心找到一个安放的地方:“那个当年商场孩子们幻想出来的‘九十九楼’,消失的、欲望的东西都在那里。

《天桥上的魔术师》剧照
消失的人和事随时可以存取,即便来自不同时空的人,也可以因此交换生命经验而发生共感。”
也许,不同时代的人,都能从《天桥上的魔术师》的时代暮色里,发觉一些模糊的身影。
他们与自己的成长历程息息相关,或是恰巧就存在于我们记忆的角落中。疑幻似真。
也许,我们真的活在一个梦游的世界。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陀螺电影(ID:toroscope),作者:徐若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