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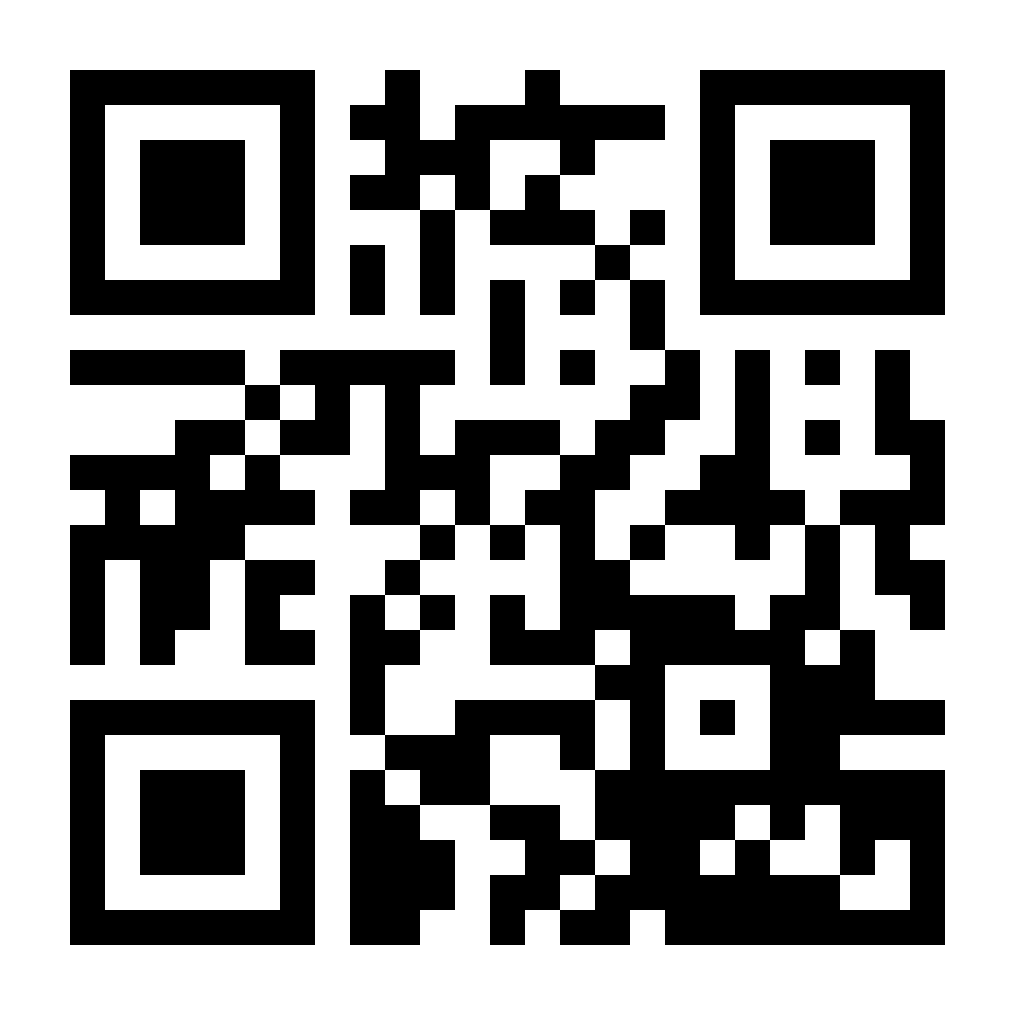
扫码打开虎嗅APP

当选择自由攀登者这个身份的时候,他们就注定选择与风险,甚至与死亡并存。这似乎成了他们内心中最挣扎、最撕裂、最矛盾的地方,也成为了他们永远无法与自己和解的原罪。但大多数成熟的自由攀登者不会回避或漠视这种原罪的存在。他们就像背负荆棘一样,清醒而痛苦地背负着它去攀登。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一席 (ID:yixiclub),演讲者:宋明蔚,策划:阳子,剪辑:chaos,原文标题:《到底是选择极致的生活,尽情地追求自由意志,还是远离旷野与高山带着遗憾过完此生?|宋明蔚 一席第1103位讲者》,题图来自:AI生成
比山更高
2025.3.1上海
大家好,我是宋明蔚。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关于中国自由攀登者的故事。
提到攀登或者登山,我相信大部分人会联想到的肯定是那些成功人士站在世界最高峰的励志故事。然而我想要讲述的故事主角恰恰相反,从世俗的角度来看,他们大多都是失败者。他们有些大学肄业,高中辍学,有些人成长在一个并不幸福的家庭,甚至有些人终生居无定所。
这是一群二三十岁的年轻人在死亡的悬崖边寻找自由与自我的故事。就是这些所谓的世俗意义上的失败者,我心目中真正的中国登山者,在中国这片大地上,书写了一部最隐秘但却最壮丽的登山史诗。
️初闻严冬冬
这一切的开始应该溯源到2008年的那个春天。
2008年中国发生了许多大事件,北京奥运、汶川地震等等,而那时我只是一个坐在辽宁省鞍山市高中教室里的高二学生。我清晰地记得,5月的一天中午,老师走进教室对我们说,为了激励大家的高考斗志,学校请来了两位成功的校友,一名是北京水立方的设计专家,另一名是刚登顶了珠峰的奥运火炬手,严冬冬。
当时我对登山也没有太多概念,跟现在主流对登山的一些刻板印象差不多,都离不开这些关键词。

我认为那些专业的登山者,首先肯定登的都是珠峰,而且他们肯定都是一些企业家,有钱又有闲,可以花费不菲的金额去攀登这座山峰。即便不是企业家,那也一定是一些专业运动员。无论如何,他们登顶珠峰之后,都离不开那些关于自我、关于征服的叙事。
只不过那一年,我记住了另一个跟登山绑定的关键词“严冬冬”。
第二年,我考到了广东的一所大学,阴差阳错地加入了学校的登山社团。登山指导老师在给我们普及国内登山历史时,非常向往地谈到,当今国内有两名最顶尖的青年攀登者,一个叫周鹏,另一个叫严冬冬。
我心里一惊,严冬冬?那是我第二次听到这个名字。要知道我几乎是从东北小城考到了祖国对角线的一个大学里面,却无意中在一家小众的登山社团里再次听到了高中学长的名字。那一刹那我甚至觉得可能是重名,但我知道就是他,因为他的名字跟登山绑定在一起。
只不过社团登山老师称呼严冬冬的时候,不再是登顶珠峰的火炬手,而是国内顶尖的阿式攀登者。
到这里,我想先给各位普及下两个关于登山的术语:一个叫喜马拉雅式,一个叫阿尔卑斯式。
️两种登山流派
其实这两种风格和流派,本质上并没有高下之分。只不过,喜马拉雅式这种攀登风格在国内要么过度商业化,要么过度政治化了。之前我对登山的刻板印象,也大多数都是基于喜马拉雅式的。
接下来,我用几组图片帮大家直观地了解两种攀登风格的区别。

这是喜马拉雅式,一个登山向导带着一个客户。在商业的喜马拉雅式攀登里面,只要你交纳足够多的费用,便会获得一个一对一的向导。他会像保姆一样全天候地保障你,必要的时候帮你穿鞋,照顾你的起居,甚至在你非常累的时候,手拉着手带你向上攀登。

这是阿尔卑斯式,其中两个攀登者在交替地开辟新路线。他们两个人之间不存在向导与客户的身份区别,是绝对平等的。

这张照片拍摄于尼泊尔一侧的珠峰南坡,牦牛驮着大量的物资,在夏尔巴人的赶往下往营地走。
这是喜马拉雅式攀登最显著的特点——出动大量的人力物力来建立非常齐备的营地,然后把这个营地一直推到尽可能的最高处,保证所有攀登者安全无虞地冲顶。

这张图中的两个人是我的朋友阿楚和小刘,他们也是当今国内顶尖的阿式攀登者。在这张照片里,他们各自背负各自的装备,往登山大本营走去。
他们的背包可能有十几公斤,甚至几十公斤沉,但那是他们未来一周所有的装备物资。

上图是喜马拉雅式攀登营地里一个公共的厨房帐篷,在这里,你能吃到热乎的食物,这在雪山上是一件非常奢侈、非常幸福的事情。
而饭饱之后,你可以走到属于自己的一个卧室帐篷。甚至当你爬了几天浑身臭汗的时候,还可以洗到热水澡。

而在阿尔卑斯式攀登中,没有厨房帐篷,没有卧室帐篷,他们可能很多天都吃不到热乎的食物,甚至像图片里这样,必须要在雪山上露宿。
如果你仔细看的话,可以从他们的脸上推测出来,头天晚上,他们一定经历了极度的寒冷、狂风,还有种种饥饿的折磨。
在阿式攀登中,与痛苦为伴是一个很常见的事情。

这两张图片都是喜马拉雅式攀登。如果你报了一个珠峰的商业攀登旅行团,无论是交纳28万元的基础攀登费用,还是最顶格的48.88万元,到了冲顶那一天,你还是要老老实实地排着队,沿着同一个路线、同一根绳子慢慢地往上爬,一直通往世界最高点——珠峰的顶峰。
如果你仔细盯着这两个图片,可能会感觉很熟悉。因为本质上来说,这跟十一黄金周的5A景区没有任何区别,你都是需要排队的,而且只有那么几分钟的时间来打卡拍照——举着一个事先准备好的小旗子,然后说“我登顶了珠峰”,甚至是“我征服了珠峰”。

有意思的是,阿式攀登者都不屑于爬珠峰。与那座世界最高峰相比,他们更想爬的是海拔只有五六千米的,不知名但难度更大的山峰。他们想在这些山峰上开辟全新的、只属于他们自己的新路线,甚至想开辟那些还没有人类登顶的未登峰。这对他们来说是更有成就感的事情。
但就是这样的一些新路线和未登峰,导致了他们可能时常会面对有暴露感的地形,面临着坠落的风险,甚至冰崩和雪崩的风险。
而更常见的,是一个人暴露在无垠旷野之中的永恒的孤独感。

一个真正的阿式攀登者,是不会为了崇高的国家荣誉而去攀登的,也不会为了个人利益而去攀登。
他们攀登只是为了自己的内心感受而攀登,或者也可以说,是只为了攀登而攀登。在我看来,这才是登山文化中最有魅力的部分。
在中国的语境下,那些活跃的阿式攀登者,我们也称之为“自由攀登者”。
️“自由之魂”
就像珠峰是喜马拉雅式攀登的代表型山峰一样,在中国,也有一座阿式攀登的代表型山峰——位于四川的四姑娘山主峰幺妹峰。它的海拔只有6247米,但是殿堂级的技术型山峰,有极高的攀登难度。

▲幺妹峰
事实上,2009年严冬冬就是因为登顶了幺妹峰,一跃成为国内顶尖的阿式攀登者。
那时,严冬冬还有诸多其他耀眼的光环在身上。他是我们辽宁省鞍山市的理科高考状元,考入清华大学,成为了同学、老师和父母眼中的天之骄子;他是翻译了几十本英文专著的英语学霸;同时他还作为奥运火炬手登顶了珠峰。

▲由严冬冬和孙斌共同翻译引进的《极限登山》
但是这些在他看来通通没有意义。他多次说过,进入实验班、名列前茅无法让他感到生命的热烈,高考状元、清华学子的身份也无法让他感受到存在的价值。
是的,就算上了清华大学又如何呢?那里挤满了来自全国各地的高考状元,所以严冬冬的成绩到了大学后只能算是平庸。他为了登山逃了很多课,以至于最后没有拿到清华大学的学位证,即使他对这个学位证也并不感兴趣。他那时已经认定,以后要干的工作就是跟登山有关的,而他所学的生物专业无法帮助他实现这个理想。
他想攀登,只不过是想通过攀登来获得自由。
自由是一个复杂又抽象的概念。但是对于严冬冬来说,他所谓的自由很简单——在想爬山的时候就去爬山,想爬什么样的山就去爬什么样的山。但就是为了实现这样看似简单的自由的生活状态,他付出了太多代价。

▲严冬冬
大学毕业之后,严冬冬租住在清华大学西门外一个简陋的平房里,付着低廉的房租。他每个月的伙食费只有不到30块钱,相当于每天不到一块钱,是一个非常夸张的数字。但就是在这样一个生存状态下,每次要买装备的时候,他甚至连几千元的价签都不看,毫不犹豫直接入手。
凭着英语的天资和聪明才智,他明明可以寻找一个按部就班的工作,用工资来养活爱好,为什么严冬冬不这样做呢?事实上他也尝试过。他去了北京的一家英语报社,一周只需要上三天班,在我看来是非常幸福的。但他完全受不了坐班这种形式,上了12天班,每天度日如年。
他也曾受到中国登山协会的邀请,有机会进入体制内,拿着铁饭碗,过一种相对安逸的生活,但也被他委婉地拒绝了。用他自己的话说,如果陷入了那种按部就班、循规蹈矩的生活漩涡中,他怕以他当时的心力,再也逃脱不出来。
你可能会想,这样一个对登山如此痴迷的青年一定非常擅长这个事情吧?甚至你可能会觉得他是一个体育特长生。恰恰相反,他是个体育特差生。
严冬冬的体育差到什么程度呢?他的肌肉力量和耐力是非常薄弱的,引体向上做不了几个,但这些好在可以通过后天的训练来加强。而先天的身体条件,比如平衡感、协调性,是无法短时间内提高的。
我举个例子,他在北京周边的一些小山上,从比较陡的斜坡上下去的时候,他会觉得害怕,因为他的协调性很差,所以必须半蹲着身子,一点点挪移着下山。
而且他的攀岩水平也不怎么样。攀岩了五六年后,严冬冬的攀岩水平还处在从初学到进阶的过渡阶段。所以他的身体在山野中会有一种极度的不自由感,这种不自由感与他对登山的热情,形成了一种强烈的不对等的反差。
也许他曾一度感到痛苦,但这丝毫不妨碍他对山野的痴狂。
直到2009年的秋天,他和他的黄金搭档周鹏经过三次尝试之后,终于登顶了四姑娘山幺妹峰南壁的一个中央路线。这是一条全新的路线,他把这条只属于他们俩自己的路线命名为“自由之魂”。

这是一个划时代的攀登成就。可以说中国的阿式攀登者开始闪耀在国际的登山舞台上,就是从这一刻开始的。
之后,严冬冬和周鹏两人开辟了一系列高难度的攀登路线,也拿到了很多非常有含金量的攀登奖项。比如2011年的时候,他们开辟了四川贡嘎山域嘉子峰西壁的一条高难度路线,这个路线比“自由之魂”难度更大,是这个组合有史以来最高难度的攀登,他们把这条路线命名为“自由之舞”。

但我想说的是,这位学长带给我的激励与其说是攀登上面的,不如说是人生上的。他让我意识到,一个人为了自己热爱的事情,到底可以付出到什么程度。以及一个人一旦实践了他的自由意志,同时也必须清醒地认识到这个自由意志的后果跟代价,必须甘愿承受这个自由生活的甜美和痛苦。
免责宣言
几年的攀登之后,严冬冬也经历了数次山难。他多次与死亡擦肩而过,也多次与死神正面交锋。他参与过很多救援,也见到了许多血淋淋的尸体。他见证了一个登山者的遇难会给他的搭档、给幸存者、给他的家人带来怎样的痛苦。
所以严冬冬也开始一而再、再而三地思考登山中的死亡。直到有一天,他意识到死亡的另一重本质——责任。
严冬冬所谓的“责任”,更多是针对攀登中的搭档关系而言。在阿式攀登中,我们习惯把这样的攀登搭档称呼为“生死搭档”。这是由阿式攀登的技术原因所决定的——两三个攀登者在搭档攀登时,需要一套结组操作,把彼此通过绳索穿在一起,就像字面意义上的“一根绳上的蚂蚱”。
一旦一个攀登者发生意外,比如掉入裂缝、坠入悬崖的时候,另一个攀登者必须及时通过一套制动手段来提供保护。这也意味着,他会承担相应的风险。

▲严冬冬(右)和周鹏(左)
因此这对搭档必须充分信任,甚至生死相依。所以如果有一天万一不幸遇难,严冬冬不希望人们把所有的问题、责难归咎于他的搭档身上。
2012年,经过多年多次的思考,严冬冬发布了著名的《免责宣言》:
我,严冬冬,现在清醒地宣布:
我理解登山是一项本质上具有危险性的活动,可能导致严重受伤或死亡。我认为,选择参与(包括发起)登山活动,意味着选择接受危险发生在自己身上的可能性。在做出所有跟登山有关的决定时,我都会把这种危险性考虑在内,这样的决定包括选择什么人作为同伴一起登山,以什么形式攀登什么样的山峰和路线,等等。
我清楚,在我与我选择的同伴一起登山时,我的生命安全许多时候取决于同伴能否在有风险的情况下做出恰当的反应和举动。我也清楚,登山是一件具有挑战性的事情,登山者(包括我自己和我选择的同伴)在面临这种挑战的时候无法保证总能做出恰当的反应和举动。
我认为,如果在我自愿选择参与的登山活动过程中,我因为任何并非我自己或同伴故意制造的原因(包括但不限于我自己不恰当的反应和举动,同伴不恰当的反应和举动,意料之外和意料之中的山区环境客观风险等)而发生严重受伤或死亡的情况,那么我的同伴不应当为此承担任何责任(包括但不限于解释和赔偿的责任)。
2012年4月28日
你可以看到,他的描述方式是非常清醒冷静的。事实上《免责宣言》并没有任何法律效力,但它的作用、它的影响力,对于之后10年的自由攀登者而言,远胜于任何律例。
️陨落
就是在《免责宣言》的同一年,我成为了我们学校的登山队队长。2012年2月,我带着登山队前往四姑娘山双桥沟攀冰训练。也就是在这次训练中,我终于有机会近距离地接触到了这位高中学长。

▲严冬冬(右三)
图片里歪着头、戴着眼镜、穿着红黑色羽绒服的这位,就是严冬冬。
我们俩简单地寒暄了一下,碰了一杯酒,并没有说太多话。因为我知道我们来自于同一个普通的高中、同一个普通的城市,也都有登山的爱好,我相信我们一定有很多共同语言,日后也一定会有更多的交流。
所以那次碰杯之后,我们就走在各自的人生道路里。我继续我的学业,他继续追逐他想要的自由的生活。只是我没想到,我们唯一一次近距离接触,却不幸成为了最后一次。
仅仅不到半年,2012年的7月份,严冬冬和周鹏在新疆的西天山深处登顶了一座未登峰。那又是一次了不起的、非常有技术含量的高难度攀登。只不过在下撤的路上,严冬冬不幸掉入冰裂缝里。他的搭档周鹏多次尝试救援,最终失败。
严冬冬卡在了冰裂缝里,最终他的遗体也留在了里面,永远地与大山住在了一起。
这个噩耗在几天内迅速传遍了整个登山界,所有人都不敢相信这件事真的发生了。我还记得,听到严冬冬遇难时,我呆坐在电脑前,感觉内心深处有某种东西被彻底撼动了。虽然我说不好那是什么,但我清楚地知道,我将永远记住他的名字——严冬冬,以及他所代表的自由登山精神,和“自由之魂”“自由之舞”。

▲严冬冬一生共翻译了35本书。西天山山难一个月后,严冬冬生前翻译的最后一本书《天生就会跑》上市了。许多读者通过购买、阅读这本书的方式来缅怀他。这部畅销书后来间接推动了中国越野跑运动的发展。
之后的几年里,我依然保持着登山的爱好,每年都会攀登几座雪山,也尝试过各种攀登风格。然而,我始终与最极限的攀登方式保持着一定距离,没有开辟过任何新路线,也没有登顶过未登峰。

▲攀登中的宋明蔚
与此同时,我进入了一家媒体工作,做了很多户外类的深度报道,也见识了更多自由攀登者的故事。
无论是作为爱好者在山上攀登,还是作为一名媒体工作者来到新闻现场,我发现这些自由攀登者的故事都深深打动着我。
这些故事最有魅力的部分,不仅仅发生在山上,更发生在山下,发生在自由攀登者的内心深处。我非常好奇,是什么原因让他们在年少时一步步走进了山的世界?他们为登山放弃了什么,又获得了什么?他们如何平衡攀登与家庭生活,又如何面对时常发生的死亡与事故?
我也听过一种说法,认为这些自由攀登者之所以选择极限的生活,是因为他们在郁郁不得志的生活中试图把登山当作一种寄托、一种出口,或者是在高压的现代生活中寻找一种解药、一种治愈的手段。
还有人试图用心理学的方法来分析他们,说这些人心里一定有某种缺失,所以想在登山中寻找人生的代偿,在另一个擅长的领域获得尊严感。但我并不这样认为。至少在我的观察里,自由攀登对他们来说,不是寄托、解药,更不是人生路上的代偿。
登顶狂热
以活跃在2000年初的自由攀登者王茁为例,他说登山对他而言是一种“消遣”,只不过是最严肃的消遣。这种严肃的消遣能让他的生命具有意义,也能让他的头脑保持敏锐。
王茁是活跃在北京地区的一个自由攀登者,技术相当不错。2004年,他和搭档伍鹏尝试攀登四姑娘山的婆缪峰,那是一座锥子一样尖锐的山峰,难度极大。最终他们攀登失败,从山里出来后,在垭口与这座山峰合影,并约定来年继续攀登。

▲王茁(左)与伍鹏(右)
几个月后,王茁带着新婚妻子攀登婆缪峰附近的一座雪山。不幸的是,就在2004年的最后一天,他和妻子遭遇了大雪崩。王茁遇难,他的妻子先被宣布失踪,后来奇迹般获救。
这是一个令人感慨又悲惨的故事,因为王茁一向以理性著称,但就是这样一个理性的登山者,最终在事故里遇难了,不禁让人感叹生命的无常。
而他的搭档伍鹏,也是一个理性严谨的攀登者。除此之外,他还是一个浪漫的人,网上的ID叫“自由的风”。他说过,在工作和自由之间,他总是喜欢选择自由,因为人生中最美好的记忆在办公室里是等不来的。
伍鹏有一个小女儿,他开辟了一系列全新的攀登路线,都是以女儿喜欢的动画片角色来命名的。他有一个幸福的家庭,也有一个不错的工作。其实在所有自由攀登者里面,他的生活算非常美满的。
只不过在这个美满之外,稍微有一点不如意,那就是没能实现和王茁的约定。
所以从2004年之后,伍鹏每年都关注婆缪峰的每一则攀登信息。直到2014年,他终于来到了婆缪峰脚下。

▲婆缪峰
伍鹏再次攀登这座山峰的念头,与其说是想实现自己的攀登理想,不如说是他非常渴望替搭档完成这个遗愿。他还说过,如果完成了这次攀登,开辟了一条全新的路线,他会把这条路线命名为“十年”,来纪念这十年当中发生的所有事情。
2014年,伍鹏已经快40岁了,女儿也快两岁。这次攀登并不顺利,他们遭遇了极端天气,伍鹏的身体在攀登过程中被极度耗竭,最终停在了距山顶100米的地方。
100米,大家可能会觉得很近,但在高难度的地形中,这100米可能需要攀登半小时。此时伍鹏面临两个选择:一个是理性地下撤,或许能全身而退。事实上对于自由攀登者而言,哪怕你离顶峰再近,选择下撤都是一件很普遍的事情。
而另一个选择,是冒着风险冲顶。
正常情况下,伍鹏肯定会做出那个理性的选择,只不过这次有些不一样,他太渴望攀登婆缪峰这座山峰了。十年来,种种微妙的情绪叠加在他心里面,产生了化学反应,他陷入了所谓的“登顶狂热”之中。
在那一刻,登顶似乎成为了伍鹏生命中唯一的意义。他的搭档说,还剩100米,其实我们已经算登顶了,在这下撤吧。伍鹏回答,都到这了,不登顶就白活了。
所以最后伍鹏选择了冲顶。他真的站在了婆缪峰的顶上,也开辟了那个“十年”的路线。只不过最后冲顶那段路耗光了他的体能,在极端的天气下,他开始失温,他的意识逐渐模糊。紧接着,他犯了几个连续的致命错误,最后从婆缪峰的山下坠落了下去。伍鹏遇难了。
后来,伍鹏的妻子在他兜里发现了他们一家三口的合照,上面还有女儿的小手印。显然伍鹏在冲顶时也将这张照片带在身上,或许是想提醒自己吧。但在最后时刻,登顶狂热让他忘了一切。
我知道你们可能会觉得无论是伍鹏、王茁还是严冬冬,他们是不是太自私了?虽然作为成年人,他们能勇于为自己的选择负责,甚至也能号称接受最坏的后果。但当他们离开后,死亡的痛苦却落在最爱他们的人身上。
那么,到底是选择极致的生活,尽情地追求自由意志,同时却刺伤身边最爱的人呢,还是远离旷野与高山,带着遗憾过完此生?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人生观的博弈,就像两种攀登方式一样,没有高下之分。但对于自由攀登者来说,没有中间地带,他们必须做出其中一个选择。
当选择自由攀登者这个身份的时候,他们就注定选择与这种风险,甚至与死亡并存。这似乎成了他们内心中最挣扎、最撕裂、最矛盾的地方,也成为了他们永远无法与自己和解的原罪。
但我想说的是,大多数成熟的自由攀登者不会回避或漠视这种原罪的存在。他们就像背负荆棘一样,清醒而痛苦地背负着它去攀登。也许有人会说,这是另一种自私,但我认为,这也是一种勇气。
与时间赛跑
在2021年年初,我终于决定把中国自由攀登者的故事完整地写下来。他们的人生是那么的精彩,他们的思想是那么的深邃。而在此之前,从来没有人完整地书写过他们的故事。
他们都是小人物,正常情况下,他们没有机会出现在正式的历史记忆中,即使在官方媒体中出现,大概率也是一则负面新闻,甚至评论区会有很多网民在不解中嘲弄、嘲讽甚至谩骂他们。
这些小人物,有些已经不在了,有些还在活跃,有些是我素未谋面但惺惺相惜的前辈,有些是我的朋友。福楼拜曾经说过,当你在为朋友立传时,应该写得像是在为他复仇。因此在执行这个写作计划的时候,我的复仇计划也开始了。我想利用我的采访和写作技能,替他们把最真实的人生和最跃动的心灵谱写下来。

这个写作项目也连接了我过去十多年来的人生。当我决定全力以赴辞职写这本书时,我突然明白了,2012年7月,当我听闻严冬冬遇难的噩耗时,我内心深处被撼动的到底是什么——那也许就是写作这本书的精神源头,是一种夹杂着好奇之心、悲悯之心与孤高之心的倾诉欲。
这也是一场与时间的赛跑。书里的大部分自由攀登者都活跃在15年甚至20年前,他们有些已经失联,有些已经不在人世,而那些幸存者脑海中的记忆,已经开始模糊了,我必须及时把这些记忆打捞出来。
我相信,只要有人还记得他们,他们就还没有真正死去。而我想通过文字,让他们永远活下去。
于是,我开始大量走访,马不停蹄地走访。在两年半时间里,我走访了100多位自由攀登者,积累了数千万字的素材。之后我花了半年多时间开始高强度地写作,终于在2023年3月的一个上午,完成了这本书的初稿。
看着电脑里的文字,我长舒一口气。我知道,要把这些文字变成一本出版物,可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至少,当自由攀登者的故事变成文字时,他们的人生印记,就不会那么容易消散了。
这就是今天我要分享的关于中国自由攀登者的故事。我是《比山更高——自由攀登者的悲情与荣耀》的作者,宋明蔚。谢谢各位。

《比山更高——自由攀登者的悲情与荣耀》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一席 (ID:yixiclub),演讲者:宋明蔚,策划:阳子,剪辑:cha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