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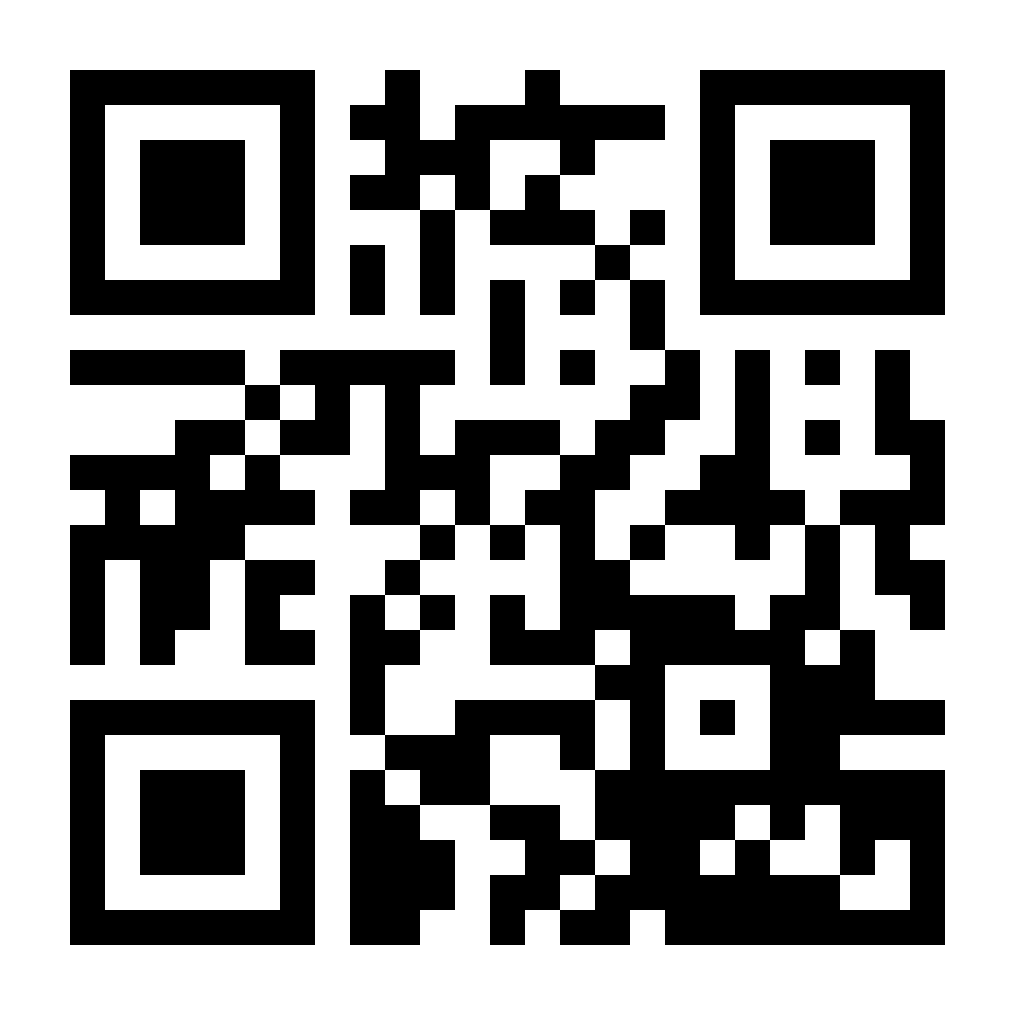
扫码打开虎嗅APP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新周刊 (ID:new-weekly),编辑:朱人奉,作者:谭山山
“咱们别什么都扯女性话题啊。来,现在下单这本《看不见的女性》,限时八五折!我们还送一本《她们不是唠叨,只是受够了》……导播准备好了没有?三二一,上链接!”
电影《好东西》中直播卖书这一幕,是很多出版从业人员近年来再熟悉不过的日常。而这只是《好东西》提供的“彩蛋”之一。让图书编辑们振奋的,还有女主角王铁梅家里那个“不会让人出戏的真书架”——导演邵艺辉曾表示,书架上的书都是她精心挑选的,因为“铁梅看什么书是很重要的”;以及,通过9岁的王茉莉之口所说的那句“正直、勇敢,有阅读量”——这是一个读者的自我追求,同时也是一份通过阅读保卫生活的宣言。
对于王铁梅书架上的书,虽然邵导并没有公布具体书目,但自有自媒体、网友拿出侦探般的劲头,辨别、整理出一份份“《好东西》书单”:既然“前夫哥”问出一句“你看过几本上野千鹤子?”,那么上野千鹤子、铃木凉美合著的《始于极限》一定会入选;廖一梅的“悲观主义三部曲”即《恋爱的犀牛》《琥珀》《柔软》的入选也毫无意外,按照王铁梅的人设,她应该会把廖一梅视为值得学习的大前辈;村上春树的《世界尽头与冷酷仙境》2023年新版、穆齐尔的《没有个性的人》等上海译文出版社的经典文学书打包出现;绘本《史塔克的世界》应该是给王茉莉准备的……
有人会按照书单一本本补课,也有人在收藏书单之后就没有然后了——在他们看来,“收藏就等于(意念上)读过”。这也是当下读者的一种普遍心态:追剧、刷短视频、网购、玩游戏,要做的事情那么多,阅读并不是优先项。而且,现在有了好用的AI,当年伍迪·艾伦需要花20分钟才知道《战争与和平》写的是什么,如今AI只需要几秒就能输出答案。
被王铁梅催促“别看书了,快去玩!”的王茉莉,可能是出版从业者梦寐以求的那种理想读者:有阅读习惯,而且年纪还小,未来可期。在阅读这件事上,很多大人都不如她。
“出版是为了继续出版”
出版行业整体低迷,这是不少业内人士的共同感受。最直观的表现是销售量的下跌。北京开卷2025年1月发布的《2024年图书零售市场趋势洞察报告》显示,2024年总体图书零售市场码洋同比下降1.52%,码洋规模1129亿元,恢复到2019年的88%。
码洋总体下降1.52%看似不多,但从细分市场来看,可以看到一些新变化:生活类图书码洋同比增长率达25.70%,是成长性较好的类别;文学类图书则同比下降15.14%。开卷认为,前者的快速增长主要源自大众对健康关注度的提升。在内容电商渠道,这类图书的码洋同比增长率高达161.58%,其中中医保健和食疗类图书表现亮眼。也就是说,在身体健康和心灵健康之间,人们首选的是身体健康。
在编辑间流传的则是这组开卷数据:2024年,近85%的新书上市半年销量低于500册,只有不到4%的新书半年销量超过5000册。在“做书”公众号上,一名编辑发表文章,称自己策划的一本新书上市半年只卖了151册。
如今,大部分图书的首印量为5000册左右,小众学术书的首印量更低,只有一两千册。出版社要盈利,主要看图书的重印情况。出版品牌“新行思NeoCogito”编辑王如菲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新书首印量逐年下降,这意味着编辑需要做更多的书,生产任务不断加重;即便如此,经营状况也只能维持在基本“过得去”的状态。这让“出版是为了继续出版”的说法成为她和其他同行的共同感受。
关注热度有时候可以转化为销量,有时候则不然。前者的例子是在《好东西》中出镜的《看不见的女性》。据其出品方新经典文化的营销编辑张小莲介绍,电影上映前,这本2022年出版的书的销量已经回落到每月一两千册左右;电影上映后,通过与片方的联动,这本书的销量增长了几倍。后者的例子来自2024年度刀锋图书奖推委、译者陈以侃。他发现,由群岛图书策划的《乔瓦尼的房间》出版半年来仍排在豆瓣热门图书榜的前列,但群岛图书负责人彭伦表示,热度并没有转化为销量。
那出版从业者应该怎么办?王如菲提出了维护“阅读共同体”的说法,即留住那些“不读书就过不下去的人”,做他们需要的书。陈以侃有类似看法:“我还是幼稚地相信,一个写作者用很自我、很细腻的方式去描绘一些似乎和你根本不相关的心思,总还是会有一些人需要这样的阅读体验。”
一端是历史,一端是纪实
“我们生活在不确定的时代”,这是联合国开发计划署2022年发布的《2021/2022年人类发展报告》得出的结论。报告指出,“不确定性层层叠加、相互作用,以前所未有的方式扰乱我们的生活”,并形成一种新的不确定性复合体。
2021年,有研究人员分析了过去125年以英语、西班牙语、德语这三种语言出版的超过1400万本书籍,发现世界许多地方的出版市场中,关于焦虑和担忧的表达正在急剧增加。其他时间尺度较小的研究报告显示,自2012年以来,远在新冠疫情暴发之前,人们对不确定性的担忧就已经逐步增加。理解和应对这一现实,是当代人的必修课。
体现在创作上,有些人把目光投向过去,试图在更广的历史维度中寻找答案;有些人则关注当下,希望从他人的真实故事中得到共鸣。这也是近年来以历史写作、纪实写作为代表的本土原创作品崛起的原因。
书评人萧轶表示:“近些年来本土原创作品的崛起与社会情绪的自我放置有很大的关系,在认知视野不断全球化的同时,越来越多的读者同样希望通过阅读来理解自身面临的困境和认知自身所处的现实。”
萧轶注意到,近年来不断涌现的本土原创历史研究著作,“终于在汉学著作长期把持关注度和认可度之下获得了自身所该拥有的地位”。一方面,读者对海外作者日渐祛魅,对本土原创作者的接纳度提升;另一方面,本土原创作者努力在学术性和通俗性之间寻求平衡,交出满足读者期待的文本。
以独立学者孙立天为例,在用英文写作的博士论文《奴才的特权》、专著《耶稣会士的使命与效忠》基础上,他通过再创作,完成了他的第一部中文著作《康熙的红票:全球化中的清朝》。在写作时,他秉持的是产品思维而非学者本位思维——他把书当成“商品”,最关心的是写出来之后读者能否读下去,“既要保持原创的观点,同时又要让更多人看懂”。包括他在书中不用脚注而采用尾注的做法,也是希望读者不受注释干扰,一口气把故事读完。
纪实写作方面,陈冲的《猫鱼》、胡安焉的《生活在低处》等书备受关注。而李颖迪的《逃走的人》能引起年轻人的广泛共鸣,就在于她“以自己为方法”,试图把握“鹤岗”作为一个指称背后所隐藏的集体性情绪:承认自己弱,满足不了社会的期许,那就找个地方躲起来。这些“逃走的人”,既不回望过去,也不会想太远的事。对他们而言,至少在目前,除了躲起来,“没有别的选择了”。就像余华所说:“现实的差距,将同龄人分裂到不同的时代里去了。”
旅行写作也是近年来的一个热潮。在豆瓣2024年度中国文学非小说类top 10榜单中,有4部旅行类作品——刘子超的《血与蜜之地:穿越巴尔干的旅程》、库索的《离岛:于偏僻之地重建生活》、杨潇的《可能的世界》和柏琳的《边界的诱惑:寻找南斯拉夫》。入选2024刀锋图书奖“年度重版作品”提名名单的班卓的《陌生的阿富汗:一个女人的独行漫记》,也属于这一类。
“不去读的书是最贵的”
把书买回来,塑封都不拆开,直接摆放在书架上或展示柜里,那叫“晒”书——书变成了装饰品。同理,收藏诸如“×本你不得不读的书”“《好东西》书单”等链接时,你带着一种“以后有时间再看”的心态完成“收藏”这一动作,就去忙别的事了,之后就再也不会打开它们——这叫囤积,满足的是你的搜集癖。
加拿大作家大卫·凯恩提出,人们买书而不读,是因为没有意识到,我们购买大部分东西,都需要支付两次才能真正拥有它们。第一次是货币支付,你付了钱,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比如一本书、一个App;而你必须支付第二次——也就是投入时间和精力,才能有所收益。
就像买一本新小说,你第一次支付的是书的价钱,第二次支付的则是数小时的沉浸式阅读。而我们经常犯的错误就是,只完成了第一次支付,却没有进行第二次支付,即过于看重物品的经济价值(或曰符号价值),而忽视了实际体验和结果。没有读的书、没有玩的游戏、没有使用的会员卡,等等,实际上都是一种浪费。
也因此,王如菲表示,就书而言,你对它的投入程度——无论是感情、精力还是头脑,决定了你能从中获得多少东西。“我们总说,书越来越贵了,但暂且不谈图书定价的大难题,事实上,不去读的书是最贵的。”
早在“前AI时代”,就有人为那些不愿花时间读书的人提供了极简版名著缩编。加拿大漫画家约翰·阿特金森就是其中一个,来看看他是怎么忽悠人的:《战争与和平》——“每个人都很悲伤。老下雪”;《堂吉诃德》——“一个人攻击风车,还有,他疯了”;《尤利西斯》——“都柏林,这事那事,不分段的长句子”;《瓦尔登湖》——“一个人在户外坐了两年,什么也没发生”……
这就是一个个段子,跟名著毫无关系,而且一点都不好玩。习惯性一键分享的你,和同样习惯性一键转发的别人一样,某种程度上成了无情的转发bot。现在,有了AI,你更是心安理得地接受AI投喂的二手乃至N手结论,并自动放弃了思考,就像动画电影《机器人总动员》中丧失自理能力的人类那样。
由此,“正直、勇敢,有阅读量”这句话的含金量还在上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