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扫码打开虎嗅APP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燕京书评(ID:Pekingbooks),作者:杨靖(南京师范大学教授),主编:萧轶,排版:韩楚衣,原文标题:《病态社会与贫困文化:社会制度畸变下的边缘“隐形人”》,头图来自:视觉中国
上世纪六十年代,美国作家凭借对社会贫困隐形人的书写,撼动了政府对畸形制度的改革。美国总统就此发动了“向贫困宣战”的脱贫攻坚战,不仅要治疗经济贫困,更要改变心理贫困,告别“病态社会”。
1962年,美国专栏作家迈克尔·哈林顿(Michael Harrington)的《另一个美国:美国的贫困》(The Other America: Poverty in the United States)出版后引起轰动。据作者本人在自传《世纪的碎片》(Fragments of the Century,1973)中回忆:本书的雏形,是他此前在《评论》杂志发表的文章——“我们的5000万穷人”(“Our Fifty Million Poor”)。
麦克米伦出版社对此话题很感兴趣,决定预支500美元,让他奔赴美国各地调查研究,结果这部“改变历史进程的小书”很快面世。短短两三个月,本书销量高达7万册(其后累计销量超过100万册),作者也由此摆脱经济困窘的freelance身份,潜心著述(平生著作多达20余种),成为纽约大学政治学教授和著名社会学家。
通过实地走访和数据分析,哈林顿在书中宣称有5000万美国人,即全美四分之一人口处于贫困之中,这一结论令社会各界大为震惊。哈林顿认为,造成这一现象的根本原因,并非自然法则的作用,也不是穷人“懒惰”的结果,而是“社会的冷漠和急功近利”。
正是由于社会制度的“畸变”,迫使数千万底层民众成为“隐形人”:他们既没有经济力量,也没有政治地位,没有谁愿意为他们代言,在现实生活中也很难发现他们的身影。更为可悲的是,除了一时难以摆脱的经济贫困,他们更身陷“文化贫困”(a culture of poverty)的泥潭——相对而言,后者的伤害性更强:他们不仅终身难以脱贫,而且会出现“代际传承”。
哈林顿大声疾呼,在美国社会花团锦簇的背后,“另一个美国”的穷人被隔离在主流社会之外,除非联邦政府和正义人士出手相助,否则他们的处境将日益恶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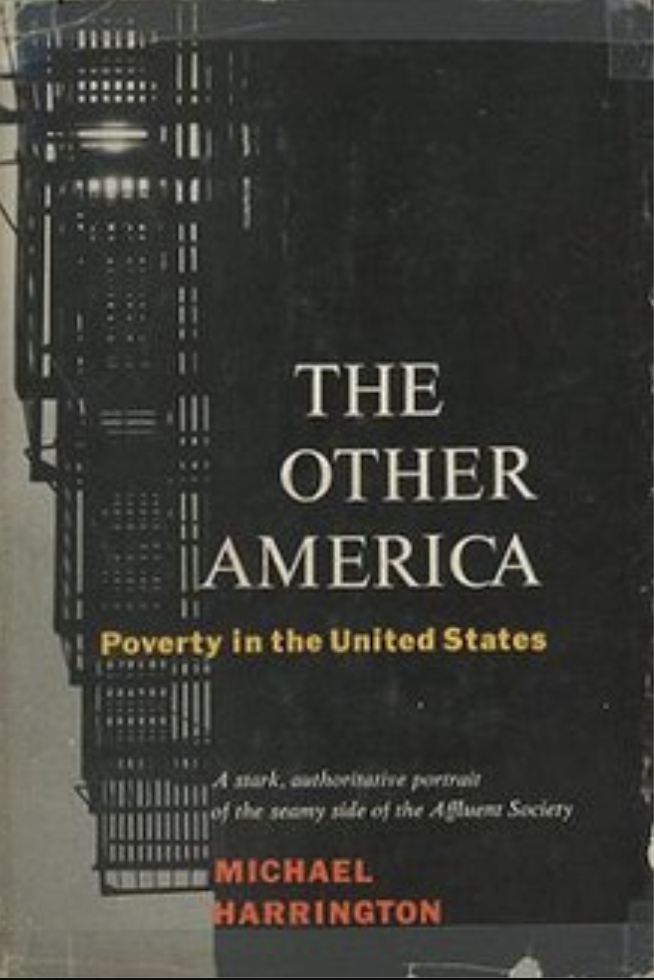
《另一个美国:美国的贫困》第一版,麦克米伦出版社
除了贫富分化,哈林顿在书中对美国社会不公以及侵害人权等“病态”现象也进行了全面归纳和分析,并建议除了完善福利保障制度和提供更多就业机会,政府更应该让底层民众接受教育,改善环境,提振信心,从而尽早摆脱贫穷“恶性循环”的怪圈(vicious circle)。
肯尼迪总统在阅读本书后受到极大的触动,率先倡导在美国发动一场反贫困战争。肯尼迪遇刺后,继任的约翰逊总统受本书启发(“反贫困运动”正是哈林顿在本书最后一章提出的口号),宣布无条件“向贫困宣战”直至彻底“消灭贫困”,同时提出建设“伟大社会”计划,致力于从根本上改变美国社会的面貌。
作为这场史无前例的反贫困战争的直接推动者,哈林顿《另一个美国》被学术界和普通读者一致赞誉为“当代的耶利米哀书”——其“愤怒的呐喊,良心的呼唤”堪称是温斯罗普“山巅之城”布道文的翻版。正如美国著名作家德怀特·麦克唐纳(Dwight Macdonald)在《纽约客》书评“我们隐形的穷人”(“Our Invisible Poor”)中所说:
“在不到200页的篇幅中,哈林顿提纲挈领地描述了贫困问题,概述了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的最新发现,以富有想象力的方式详细描述了贫困的现状,并分析了大规模的贫困之所以能在普遍繁荣中持续存在的原因……尽管本书缺少脚注,其重要性却无与伦比。”
半个多世纪后,本书与弗洛伊德《文明及其不满》等并列为美国公民必读书,足见其影响之深远。
隐形的国度
20世纪60年代是美国文化革命(或反文化革命)的年代,一大批社会文化学著作相继问世,其中包括雅各布斯《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1961)、蕾切尔·卡森《寂静的春天》(1962)、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1964)等,它们都从不同侧面(如民权、环保、城市化等)反映出美国社会急剧变化的时代主旋律,其共同特征是对传统社会文化的反叛。
对哈林顿而言,在这一时期的文化研究著作中,著名经济学家加尔布雷斯的《富裕社会》(1958)最富启迪。加尔布雷斯乐观地认为,尽管美国社会存在贫困现象,但经济增长与社会富裕一定能够很快消灭贫困。哈林顿对加尔布雷斯的“预判”表示怀疑,并通过全面揭示美国的贫困对这一乐观结论做出了回应。
与加尔布雷斯相比,《另一个美国》不啻为一剂清醒剂,将沉醉在“富裕社会”美梦中的中产阶级及上流人士唤醒,让他们看到与他们所处环境迥然不同的“另一个美国”,并意识到采取行动的必要性和迫切性——哈林顿在书中对富裕阶层“喊话”:帮助穷人就是帮助你们自己,因为社会长期分化和对立必将引发震荡和危机。
据研究,本书第一章的标题“隐形的国度”,是两个文学典故的“合体”。其直接源头是美国黑人作家拉尔夫·艾利森创作的长篇小说《隐形人》(Invisible Man,1952)。小说讲述一位出身贫寒的黑人青年在白人主导的社会里饱受种族歧视,不断寻找民族文化和自我身份的过程。后来他参与街头黑人骚乱,以失败而告终。小说最后,在警察大搜捕中,他不得不隐居地下,成为名副其实的隐形人。
哈林顿在本书第四章“如果你是黑人,请莫上门”中引用小说中人物对话,正是要借此凸显贫困问题背后复杂的种族和阶级矛盾。
此外,“隐形的国度”这一标题也指向著名英国作家本杰明·迪斯雷利(BenjaminDisraeli)。两度出任英国首相的迪斯雷利在小说《西比尔》(Sybil,1845)中,借激进分子杰拉德(Walter Gerard)之口宣称:
“世界上有两个民族。在他们之间,并不存在交流,也不存在同情。他们对彼此的习惯、思想和情感都毫不关心,似乎他们是不同区域中的定居者或者两个不同星球上的居民。他们是在不同教养中形成的,吃的是不同的食物,遵循不同的命令和秩序,由不同的法律支配和统治。其实就是一个是富人,一个是穷人。”
——本书第九章题为“两个国度”,更明确表达出哈林顿的愤慨之情。

企鹅版《另一个美国》封面图
仿效迪斯雷利冷隽的笔法,哈林顿在本书开篇写道,“世上有个人们熟悉的美国。各种讲话、电视和杂志的广告,都在为它歌功颂德。在这个国家里,人们的生活水平达到了史无前例的高度。”紧接着,作者揭示了美国战后经济繁荣表象之下的隐性群体贫困,尤其是那些城市边缘人群所经历的贫困,以及边远农村地区的贫困。
“穷人越来越从这个国家的经验和意识里消失了……最终,穷人在政治上看不见了……作为一个群体,他们被分为一个个的原子。他们没有面孔,没有声音……四五千万穷人越来越淡出了人们的视野。”为此,哈林顿宣称美国的贫困人群构成了“另一个美国”:尽管它被隐藏、被忽略,但它的存在恰恰证明美国社会的病态。
哈林顿认为,从历史来看,社会上存在贫困本身并不可怕,可怕的是贫困在社会上的隐形。穷人的贫困并不可悲,可悲的是世人对穷人贫困的冷漠。由于美国政府成天满足于宣传“纸面上的胜利”,由于美国富裕阶层沉迷于“富裕社会”的神话,二者的合力最终导致穷人的隐身。
同时,由于穷人没有自己的声音和自己的代表,他们没有办法让政府的政策方案符合自己的利益,由此导致大量“扶贫”资金没有落实到真正的穷人身上——比如,最低工资并没有适用到真正需要最低工资保障的行业,政府的大量农业补贴并没有惠及农村穷人,城市的住房改造项目让更多的贫民窟居民居无定所。
事实证明,以上各项政策出发点无不“善意满满”(good intentions),然而在具体实施过程中产生了严重偏差,其效果往往适得其反。以最低工资为例,芝加哥等地“内城区”的黑人,本来可以通过餐馆洗碗、商店打杂之类的微薄收入谋生,但在最低工资保护法令之下,人力成本攀升,工作岗位减少,以至于若干黑人青年沦落为无业游民——不仅造成家庭危机,此后更进一步引发社会问题。
再以历届政府津津乐道的福利制度为例。哈林顿承认这一民生工程的确“惠及”(trickledown)千家万户,但它的负面影响也不容小视。哈林顿对福利机构的“文牍化”倾向表示强烈质疑——通常情况下,人们希望在社会中展示自己的特长,而负责福利发放的官员却希望申请者展示自己的短处:填表、面谈、核对、申诉、评估、咨询,然后是更多、更复杂的表格……每宗援助申请都附带一套自贬身份的程序,最终令人失去耐心而走向崩溃——
“它以一种福利系统以外的人无法想象的方式,践踏了隐私和自尊。”正如女权作家丽贝卡·索尔尼特(RebeccaSolnit)在《黑暗中的希望》(Hope in the Dark)中简明评述的那样,在实施这一民生工程的过程中,政府及其雇员“自我标榜的成分多过努力做事的成分。”这样一种福利制度,救助的只是物质的温饱,摧残的却是人性的尊严。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不是在消灭贫困,这是在消灭穷人。”
贫困的文化
1959年,人类学家刘易斯(OscarLewis)在《五个家庭:贫困文化研究的墨西哥案例》(Five Families:Mexican Case Studies in the Culture of Poverty)中首先提出“贫困文化”的概念。刘易斯把贫困文化描述为:“在一个阶级分层化而又高度个人化的资本主义社会中,穷人对他们的边沿地位的一种适应和一种反应。”
并且他相信,贫困文化一旦形成,就会对孩子产生影响——贫民窟的孩子到了六七岁,“他们通常就已经吸收了他们亚文化的基本价值观念和态度,因而终其一生,他们都不能在心理上做好准备,以充分把握和利用处境的改善所带来的机遇。”在此理论基础之上,哈林顿通过调查访谈也得出结论:贫困人士“从内部成为局外人,在与主流社会完全不同的文化中长大”,正是这种贫困的“亚文化”,将他们与主流社会隔离开来。
与刘易斯的学说相比,哈林顿更强调穷人的社会环境,即“社会底部的无序”:那里存在普遍的无知和麻木,社区缺少积极榜样,社会治安紊乱,犯罪率居高不下。在他看来,经济贫困只是一时,心理贫困才更为致命——这使得穷人在心理上很难接受外部的发展条件与机会,从而陷入贫困代际转移的困境,即所谓贫困的“恶性循环”。
正如其他文化一样,贫困文化也自有其特质:如因持续的贫困和生存压力而产生的与世无争和消极被动,自轻自贱和悲观绝望,以及麻木不仁。而这样的文化一旦形成,它又会生成自我延续的机制,即便外部环境已经发生变化。
根据哈林顿的考察,“贫困文化”并非古已有之,而是晚近(尤其是19世纪中期以来)才凸显的社会现象。事实上,直至南北战争以前,贫困在美国并不被视为一种社会问题,而仅仅被视为市井常态。英国早在伊丽莎白女王时代就颁布《济贫法》(Poor Law,1601),但是由于美国历史文化的独特性(或“例外论”),长期以来,美国社会流行的观念却认为贫富仅关乎个人能力(以及道德素质),与社会制度无关,自然也无需借助立法改变现状。
最早抵达殖民地的清教徒奉持加尔文教义,坚信贫困乃个人懒惰的必然结果;相反,要成为上帝“选民”,个人必须自立勤奋(即富兰克林所谓“天助人自助”)。所谓美国梦,很大程度上是指积累财富和事业成功——通过“事功”荣耀上帝。从这个角度看,创造财富是受到上帝鼓励和嘉奖的行为,而懒惰和贫穷则要受到上帝的斥责和惩罚(即所谓“马太效应”)。
这种突出个人自立和竞争的生活法则在19世纪后半叶得到进一步强化,主要由于英国哲学家斯宾塞“社会达尔文主义”(SocialDarwinism)学说的影响。斯宾塞断言,人之受穷,乃因为他缺少一种内在的生存能力。换言之,贫困是大自然“排除那些弱智迟钝、不健康且无主见之人”的手段,以便为天生有能力享受财富的“适者”保留足够的生存空间。
时至20世纪,人种论和智力量表(Intelligence Scale)等“伪”科学大行其道。前者主要论证黑人天生顽劣,不配和白人享受同等权利;后者从生物学角度测量人的智商,结果“发现”穷人(包括黑人在内)大多智力低下,缺乏学习能力,只适合从事简单劳动。
这一派的代表人物是哈佛大学教授、著名心理学家赫恩施泰因(Richard Julius Herrnstein),他长期致力于社会收入与智力差异的关系研究。他的结论是穷人总体能力较差,其中的智力因素具有遗传性,因此贫富悬殊不可避免。
对于底层社会贫困文化现象的根源,哈林顿的同时代人也提出了种种“假说”。第一种假说,认为家庭是祸根:在底层社会家庭中,传统大家庭结构早已解体,尤其是黑人社区,单亲家庭数量超过半数——子女的抚养及教育问题都面临严峻考验——“正在解体的家庭”是贫困文化的发源地。
第二种假说,将这一现象归咎于社会变迁:由于经济发展和环保主义兴起,制造业被迫从城市中心地带迁往郊区。内城区的劳工阶层不愿外迁,城市却不再为他们提供机会,失业加剧家庭解体,导致社区环境恶化,于是昔日城市的中心一变而为贫困的中心。
第三种假说,将畸形的福利制度视为病因:在“高福利”诱惑之下,穷人不愿外出工作,女人通过生育(尤其是婚外生育)获得的津贴甚至超过劳动所得,也失去工作的动力,久而久之则形成一个“自我摧残”的贫困陷阱。

黑豹党的报纸
在上述观点中,美国社会学家莫伊尼汉(Daniel Patrick Moynihan)针对黑人社区的调查报告最具代表性。凭借事实和逻辑论证,该报告指出黑人社区状况持续恶化:依赖福利救济过活,离婚率比白人高40%,私生子数量骇人听闻,占黑人婴儿比例高达1/4。
与此同时,1960年代民权运动兴起后,黑人的政治地位提高,自我意识增强,尤其是“黑豹党”(Black Panther)等组织建立之后,将马丁·路德·金等人倡导的和平斗争方略改造为武装夺取政权模式,由此形成“贫困—暴乱—更加贫困”的恶性循环。
莫伊尼汉的调查报告,被政治保守派解读为黑人社会的“病态”:黑人家庭衰败,只是由于黑人不能适应变化的环境,以及自身的道德败坏。善意的福利制度破坏了黑人的工作积极性,鼓励黑人妇女生育子女、黑人男子逃避家庭责任,最终导致家庭破裂——
很显然,当有人宁愿坐享其成,却不愿去找工作时,福利制度就走向了它的反面:它不是在消灭贫困,而是在纵容甚至制造贫困,并使得原本暂时的贫困变为持久的贫困。因此,保守派的结论认为,福利制度必须摒弃——黑人族群内部所具有的适应性和调节能力,“足以使其保持原状,用不着白人世界去帮忙”。
正是在这一点上,作为“新左派”代表人物的哈林顿与保守派产生了重大分歧。哈林顿认为,贫困文化的真正根源,在于社会阶层的固化和社会制度本身。过去的穷人只是在经济上贫困,在精神上一直奋发向上,因为生活中充满机遇和挑战——西进运动,城市开发和社区建设,等等。他们相信只要把握机会,努力拼搏,就一定能实现美国梦。
然而,随着时间推移,他们却痛苦地发现周围的环境变得越来越“陌生”,制度越来越“不友好”。以选举投票权为例,冗长的程序、大量的文书工作以及繁琐的身份(及住宅)证明材料,有效阻止了大多数底层民众(尤其是黑人)取得投票登记权——用哈林顿的话说,结果是,“‘另一个美国’在美国政府里系统性地没有得到充分代表,它不能为自己代言”。
尽管美国社会在高速发展,穷人却惊恐地发现他们与报刊杂志、广播电视上宣扬的舒适的生活无缘。他们既不懂得储蓄,也不懂得如何规划自己的未来,结果成为美国社会“成功”宣传的牺牲品。这一种成功学宣传的不是传统的劳动价值观,而是新兴的“财富神话”。
根据这一“话术”,产业劳动(者)是身份低下的标志,因此成功人士应当力求避免——如果一位金融高管或外科主任的儿子不幸成为一名“打工者”,整个社区都应对他的悲惨遭遇深表同情。在哈林顿看来,这一种成功学可以称之为“掠夺文化”——它倡导劳动低人一等,劳动者智力低下,因此理应世代遭受剥削和压迫。
哈林顿认为,掠夺文化的泛滥说明现行制度亟需改变。当社会制度以“严格规范”为名日益完备之时,必须考虑到大量底层的“零余者”或边缘人跟不上时代前进的节奏,因此必须预留时间和空间,让他们逐步适应。比经济贫困更可怕的,是心理贫困:穷人日益感到孤寂无助——在这样的制度中,每个无助之人都成了病人——生理的或心理的。
在哈林顿看来,贫困文化的真正根源乃是存在一个“病态社会”。在这样的社会中,福利救助制度固然必不可少,但说到底它只是授人以鱼(a handout)的权宜之计,而他所主张的是授人以渔(a hand-up)——即通过教育从根本上改变“5000万穷人”的命运。
这一主张与哈佛校长科南特(James Bryant Conant)的设想不谋而合。科南特在《贫民窟与城郊》(Slums and Suburbs,1961)一书中以贫民区黑人家庭为例,指出黑人父母由于自身缺乏良好教育而历经生活艰辛,同时他们自身对教育的漠视又大大限制了他们的子女获得成功的机会,于是导致恶性循环。
这位20世纪著名教育家在演讲中宣称,“许多世纪前,阿基米德曾告诉我们‘给我一个支点和足够长的杠杆,我就能撬动地球’。今天我们终于拥有了足够长的杠杆和足够强的支点。”——他认为,这个杠杆就是教育,支点就是联邦政府财政资助。
哈林顿高度赞同科南特的观点,认为贫困问题的根源在于国家经济制度和社会制度,而不单单是教育体系本身——归根结底,教育机会的平等取决于经济和社会制度的合理和平等。而一旦这样的平等得以实现,贫困文化问题自然迎刃而解。
从这个意义上说,正如社会学家威尔逊(William Julius Wilson)在《真正的穷人》(The Truly Disadvantaged)一书中所宣称的,教育乃是“社会缓冲器”(social buffer),因此决策者应当最大限度发挥其缓冲效用,弱化社会矛盾,减少贫富差距,唯其如此,方有可能根除贫困文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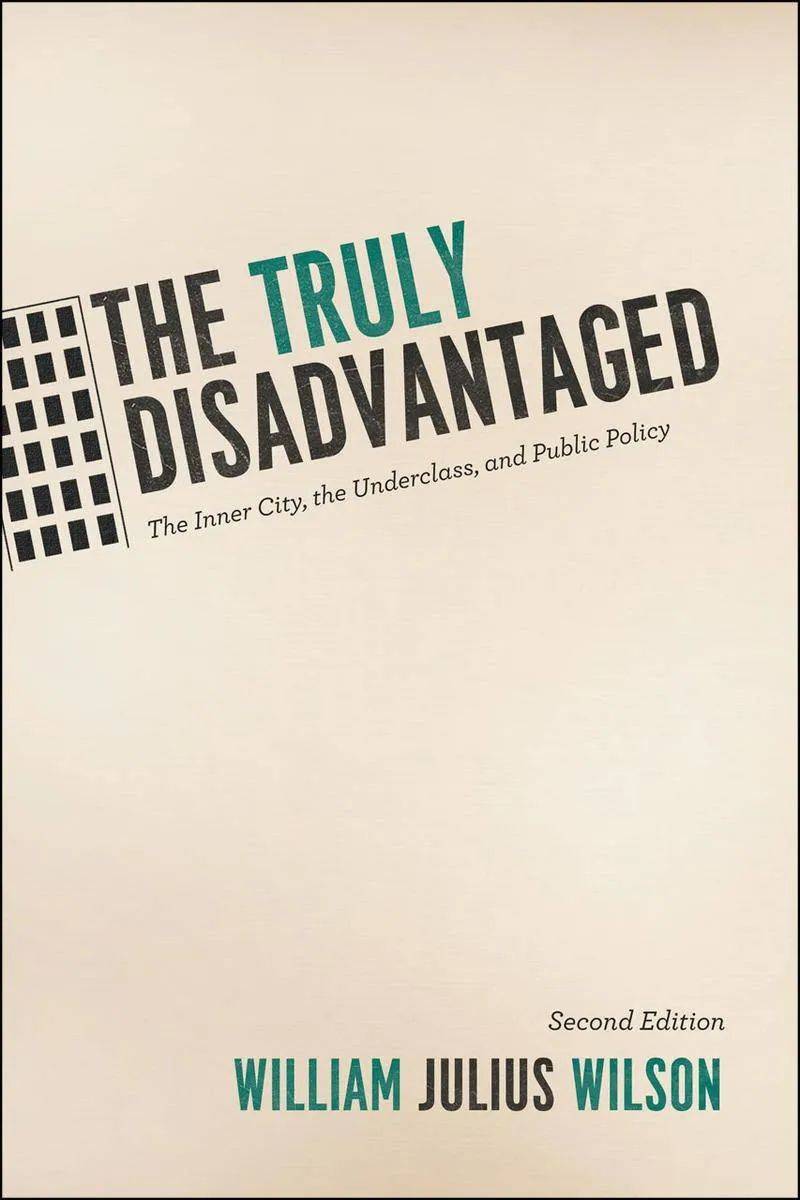
威尔逊的《真正的穷人》
“伟大社会”计划
面对严峻现实,约翰逊总统提出了“伟大社会”(Great Society)计划纲领。1964年,国会通过总统提出的有关城市公共设施、农村卫生中心、公共教育基金等改革计划。1965年,为穷人提供医疗保障服务的法案更成为里程碑式的标志(相应的,美国政府的财政年度支出也由1965 的81亿美元飙升到1966年度的114亿美元)。
在直接救济层面,约翰逊主张通过增加低收入人群金钱收入或物质补助满足其最基本生存需求。在提高薪酬方面,约翰逊制定了最低工资保障法,并真正将1964年的最低小时工资1.25美元提高到1967年的1.60美元。
对于美国社会的“痼疾”种族歧视问题,约翰逊总统深知仅仅通过提高“政治地位”远远不够,更需要从经济和文化层面给予帮助和扶持,否则他们根本没有能力和白人竞争——照他的说法,我们追求的不仅是人身的自由,而且是机会的平等;不仅是权利和理论的平等,而且是事实和结果的公平。
正是从这一点出发,约翰逊又推出“肯定行动计划”(Affirmative Action),通过落实一系列经济民权政策,帮助那些美国历史上长期受到体制性歧视的贫困群体在政治、经济和文化地位等方面迅速改变劣势地位。
响应科南特等人的倡议,“伟大社会”计划将教育问题摆放在突出位置。其中最富有革新精神的内容是“启智计划”(head start),旨在帮助贫困儿童上学,使其在身体和智力两方面同时获得发展。这一计划前后投入高达15亿美元,保证低收入家庭的学生能够完成小学和初中学业,并通过向贫困生发放贷款最大限度保证中学生升入大学。同时,借助建立新图书馆、实验室和特殊训练中心等设施,满足不同人群的教育需求。
此外,针对哈林顿等人呼吁的(再)就业问题,约翰逊也出台了有关职业教育和工作培训的计划,借助半强制性手段让失业青年参与职业训练方案,增强他们的自主性和工作机遇,促使其由“食税者”向“纳税人”转变。

《权力之路:林登·约翰逊传》,[美]罗伯特·A.卡洛著,何雨珈译,猫头鹰文化丨四川文艺出版社2018年5月版
约翰逊“伟大社会”计划期间,共推出社会改革计划近五百项,试图解决包括贫困问题在内诸多庞杂的社会问题,但由于部分顶层设计的偏差,以及意想不到的越战升级,并未能取得全面预想的成效,有若干政策在实施过程中甚至走向了它的反面。
以该计划的核心“经济机会法”为例:法案致力于通过提供工作训练、职业教育等措施解决贫困和失业问题,其中规定:私营企业每接受一名培训人员,能够获得联邦政府高达2900美元的财政补贴——然而,在执行过程中,谎报人数骗取津贴的丑恶行为却在各地层出不穷。
再比如各地纷纷上马的内城区改造工程,使得城市中心贫困居民损失惨重,政府的拆迁和补偿费用只能暂时缓解他们的生活窘境,但并不能让他们真正分享到改革的“红利”,相反却使他们对政府补贴产生依赖心理。
尽管“伟大社会”计划遭到其政治对手的调侃——“我们向贫困宣战,结果赢得了贫困”,但毋庸置疑,约翰逊总统的改革取得了显著成绩:在60年代的整整10年中,穷人的数量在逐年减少;到1969年,贫困者下降到2500万人,即减少了一半。
哈林顿在本书《后记》部分以“20世纪70、80年代贫困问题”为题,对这一场反贫困战争进行了概括和反思。他一方面表彰肯尼迪、约翰逊(以及继任的尼克松)等领导人的人道主义情怀以及在社会进步方面作出的努力,另一方面也指出了存在的缺点和不足。
政治保守派曾经诋毁“贫困只是知识分子用‘人为的统计数据’造出来的概念”,但反过来,由于迎合领导人(约翰逊最喜欢别人当面奉承)意旨而“粉饰太平”、“报喜不报忧”,则是更为错误的作法——在数据满天飞的时代,哈林顿这位政治学教授告诫他的同胞,数据并不必然代表“中性、客观和科学”。即便对于总统国情咨文和政府工作报告中的数据,民众也要详加辨别。因为,“如果玩弄文字游戏,总统可以宣称美国压根就没有穷人。”
同时,哈林顿对约翰逊本人的某些做法也提出批评。这位总统坚信,社会投资最好的办法是企业与政府“搭档”——其结果是,私营部门可以通过建造政府补贴的住房、或提供享受政府补贴的教育产业,大挣一笔;政府也可以借此获得民众的感恩戴德,实现“双赢”——一个“伟大社会”似乎便由此建成。但哈林顿认为问题远非如此简单——历史经验表明,反贫困之战“道阻且长”;而进行这样一场漫长的反贫困运动,也是“我们肩负的道德职责”。
此外,在贫困问题依然如此“刺眼”的时候,某些政府机构却摩拳擦掌准备为“消灭贫困”庆功嘉奖。在哈林顿看来,这只能说明政府部门近年来的“自我膨胀”,导致“官僚集体主义”盛行——“联邦政府近三分之一个世纪的集权造成了一个官僚化的怪物,它臃肿笨拙,不理会民众的需要,也没有什么效果。”
对于这样一个列维坦式的怪兽,美国民众需要加倍小心,如同哈林顿在本书结尾告诫的那样,“如果要消灭贫困,政府需要比罗斯福新政还要大胆的创举”,但与此同时,更要像美国政治评论家提醒的那样时刻保持警醒:政府不可能解决所有问题;许多时候,政府本身就是问题。
作为“贫穷再发现”之书,《另一个美国》在美国政治思想历史上产生了深远影响。书中定义的“贫困文化”、贫穷“恶性循环”等如今既是学界术语,也成为民众的日常语汇。不仅于此,本书在社会实践中也同样发挥了重要作用,正如英国思想史家彼得·沃森(Peter Watson)在《现代心灵:20世纪思想史》一书 (The Modern Mind: An Intellectual History of the 20th Century,2001)中所说:“如果从其有效地激发起了政治法案的通过来判断,《另一个美国》必须被视为有史以来最成功的著作之一。”
哈林顿在本书开篇曾经展望:当下社会需要一名“爱之深责之切”的“美国的狄更斯”,来记录人民的苦难——这位1950年代就被列入FBI黑名单(后来又被胡佛列入中情局黑名单)的美国学者,通过毕生不懈的努力,最终践行了自己的理想。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燕京书评(ID:Pekingbooks),作者:杨靖,主编:萧轶,排版:韩楚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