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扫码打开虎嗅APP

本文摘自《我们星球上的生命:我一生的目击证词与未来憧憬》(经中信出版集团授权),原章节标题:《未来憧憬:如何重新野化世界》,作者:大卫·爱登堡(“世界自然纪录片之父”,英国杰出的博物学家、探险家,BBC电视节目主持人、制作人。),头图来自:视觉中国
该如何促进野生世界回归,使地球恢复一定的稳定性呢?许多人在苦苦思索,试图找到通往另一个更野化、更稳定的未来的路径,这些人在一个方面不谋而合,都认为我们的征程必须由一种新的理念来引领——实质是回归老的理念。全新世初,尚未发明农业之时,生活在地球各处的几百万人以狩猎—采集为生。那种生活方式是可持续的,与自然世界保持着平衡。它也是我们的祖先当时的唯一选择。
农业使人有了更多的选择,人与自然的关系也随之发生了变化。我们开始把自然世界视为驯服、压倒和利用的对象。无疑,这种对生命的新态度使我们获得了巨大的收益,但随着时间的流逝,我们失去了平衡,从归属于大自然变为独立于大自然。
如今,我们需要扭转这个变化的方向。可持续的生存又一次成了我们唯一的选择。可是,现在世界人口达到了几十亿。我们不可能,也不会愿意重拾狩猎—采集的生活方式。我们需要找到一种新的可持续的生活方式,使今天的人类世界再次与大自然达成平衡。只有这样,我们造成的生物多样性的损失才能转亏为盈。只有这样,世界才能重新野化、恢复稳定。
在通向可持续未来的征程中,我们已经有了罗盘。我们计星球界限模型,就是为了不走弯路。它告诉我们,必须减少世界各地的温室气体排放,以立即阻止气候变化,最好是将其扭转 ;必须停止过度使用化肥 ;必须停止把荒野变为农地、种植园和其他用地的做法,退耕还野。它还警告我们需要注意其他问题,包括臭氧层、对淡水的使用、化学品和空气污染,以及海洋酸化。
如果这些都能得到控制,生物多样性的损失就会放缓、停止,然后开始自我修复。换言之,如果我们用以判断自己行动的首要标准是自然世界的重生,我们就会做出正确的决定。我们这样做不仅是为了大自然,也是为了我们自己,因为大自然在保持地球的稳定。
可是,我们的罗盘缺少一个重要的因素。最近的一次研究估计,人类对生命世界的冲击几乎有一半是由最富有的 16% 的人造成的,最富有的人在地球上惯常的生活方式是完全不可持续的。我们在筹划通往可持续未来的路径时,必须处理这个问题。我们必须不仅学会在地球有限资源的范围内生活,还要学会如何更均衡地分享这些资源。
牛津大学经济学家凯特·拉沃斯(Kate Raworth)给星球界限模型加了一个内环,详细说明了这个挑战。新加的内环代表了人类福祉的最起码要求,包括体面住房、医疗服务、清洁饮水、安全食品、能源使用、良好教育、足够收入、政治声音和公平正义。这样,星球界限模型就成了有两套界限的罗盘。
模型的外环是生态界限,若想维持一个稳定安全的地球,就绝不能越过这个界限。模型的内环代表着社会基础,若想实现公平公正的世界,就必须努力使所有人达到这个水平以上。这样得出的模型被命名为甜甜圈模型,它代表着一个诱人的前景 —人人享有安全正义的未来。
“万物的可持续性”应该成为我们人类的理念,甜甜圈模型应该成为我们前进征程的罗盘。它摆在我们面前的挑战简单而严峻 :改善世界各地人民的生活,同时又大大减少对世界的冲击。在试图应对这一巨大挑战时,应该向何处寻求灵感呢?只需看看我们眼前的生命世界即可。一切答案都在那里。
重新野化大地
古时候,欧洲大部分土地上都覆盖着黑压压的密林。一个个小小的新生农业社群分散在欧洲大陆各地。对那时的农夫来说,森林是对头,是他们种田糊口的阻碍,是游荡着精灵和野兽的恐惧之地。
他们在夜里给孩子讲童话故事,告诫孩子们千万不要独自走进森林。狼会吃掉他们当晚餐。森林会施魔法惑他们,让他们永远回不了家。巫婆会在森林里等着。征服森林的伐木人和猎人被奉为英雄。大林莽里锁着沉睡的公主和空无一人的巍峨城堡,它是永远的恶棍。
农夫们拼了命和森林斗争。他们焚烧砍伐一排排的栗树、榆树、橡树和松树,把森林从河边推上河谷的山坡。他们杀死林中的野兽,砍下兽头挂在墙上做纪念。他们学会了修剪树木,把白蜡树、榛树和柳树劈到根部,令其长成树干细长的树丛,好用来做栅栏、屋椽和床柱。他们的农庄扩大,人口增长了。他们的恐惧消退了。森林被驯服了。
砍伐森林是我们人类干的事。它象征着我们的统治地位。人类进步与森林消失的关系如此紧密,甚至出现了一个体现这种关系的公认模型。森林转型指的是一个国家先砍伐森林,然后森林回归的过程,这个过程往往发生于发展中国家。
当人数量少,并分散为各个自给型小农业社区的时候,人的力量仅能把森林分割成块。不过,这使得风和光得以进入林地,改变森林的内部环境,影响林中的物种组成。森林被分割得越碎,就越难以维持原有的生态社群。
农夫彼此间交换产品,引入了市场经济,农场变成了企业,田地的数量和规模开始增加。耕地价值迅速上涨,于是人们把目光投向了剩下的森林。大林莽很快被削减为一块块林地和田地间零散的矮树丛。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农业技术提高了产量,城镇吸引大批乡村人口流向城市,粮食和木材越来越地从国外进口,结果,对农地的需求减少了。边缘农地首先被弃,森林开始回归。
第二次世界大战打响时,欧洲大部已经进入了这个转型期的森林回归阶段,森林净覆盖面积开始增加。在美国东部,欧洲人到来后森林以异乎寻常的速度飞快减少,但到了 20 世纪上半叶,也开始了森林回归。
从 1970 年至今,美国西部、中美洲的部分地区和印度、中国、日本的一些地区也进入了森林回归阶段。必须说明,所有这些国家和地区进入森林回归阶段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由于全球化,它们越来越多地从不发达国家进口粮食作物和木材。因此,热带地区的森林砍伐至今方兴未艾毫不奇怪。
许多热带国家靠着向比较富裕的国家出口牛肉、棕榈油和硬木来赚取收入,它们正在砍伐最深、最密、最天然的森林 —热带雨林。那么,应该鼓励它们尽快完成森林转型吗?可惜我们等不起。如果任由热带地区自然完成森林转型,释放到空气中的碳会多到不可承受,许多物种以后就只能在历史书中才看得到 ;这对整个世界来说不啻大灾难。现在就必须停止世界各地的一切森林砍伐,通过投资和贸易来支持那些尚未砍倒森林的国家在保住森林资源的同时从中获益。
然而,知易行难。保护野生土地和保护野生海洋完全不同。公海不属于任何人。领海由国家所有,政府能够在权衡利弊后做出广泛的决定。但土地是我们居住的地方。它分成数十亿大小不同的地块,被众多不同的商业团体、国家团体、社区团体和私人团体拥有和买卖。它的价值由市场决定。
问题的核心是,今天我们无法为自然荒野及其为全球和当地环境提供的服务计价。在账面上,100 公顷热带雨林的价值比不上一个油棕种植园。因此,砍掉野树被认为是划算的。改变这种情况的唯一切实办法是改变价值的含义。
联合国的 REDD+ 方案就是这样一个尝试。它是一种按照世界上硕果仅存的雨林所储存的巨量的碳来为雨林确定合适价值的方法。确定了碳的价值,就有可能使雨林所在国的人民和政府因保持雨林的野生状态而得到报酬,报酬的部分资金来自碳抵消。
理论上,REDD+ 是可行的。然而在实践中,土地所有权和土地价格所涉的各种复杂因素造成了重重困难。原住民抗议说 REDD+ 贬低了森林的价值,使之仅仅成为一种货币符号,还鼓励了一种新形式的殖民主义。赚钱的机会引来了其他国家的所谓碳牛仔,他们随着雨林价值的升高蜂拥而至,争相在雨林里大肆圈地。另一些人担心,如果创立一个可以在热带抵消碳的制度,大型产业会用 REDD+ 作为继续使用化石燃料的申辩理由。
什么东西一值钱,就会引动人的贪心,这是可悲的现实。REDD+ 目前在南美、非洲和亚洲执行项目的经验表明,人们期待它找到自我改善的方法。
我们的确需要 REDD+ 这样的制度。它是一个勇敢的尝试,试图解决大自然的价值被低估这一根本性问题,因此必须坚持下去。我们都本能地明白基本的道理。地球上尚存的森林、雨林、湿地、草原和林地其实是无价的。它们储存的碳一旦释放出来,我们将无法承受。它们为我们提供的环境服务必不可少。它们蕴含的生物多样性我们丢失不起。怎么能将这一切反映在我们的价值体系中呢?
也许我们需要改变货币。仅仅根据大自然捕集和封存的碳量来为大自然定价有一个危险,那就是碳成了我们唯一重视的东西。这过分简化了大自然对人类的价值。更糟的是,它可能会使我们误以为生长迅速的桉树种植园和生物多样的森林具有同等价值。我们可能会决定在不再需要用来种粮食的农地里种植单一的生物能源作物,而不是退耕还林。碳捕集与封存极其重要,但不是全部。它并不能阻止第六次大灭绝。
要创造一个稳定健康的世界,需要珍视爱护的是生物多样性。毕竟,如果增加了生物多样性,自然就能实现最大限度的碳捕集与封存,因为一个栖息地的生物多样性越丰富,捕集和封存碳的能力就越强大。如果我们的世界给生物多样性确定合适的价值,鼓励土地拥有者在任何地方以任何方式增加生物多样性,那会怎么样?
那将产生神奇的效果。原始雨林、原生温带森林、未经人力侵扰的湿地和自然草原突然间将成为地球上最宝贵的不动产!拥有这类野地的人会因为继续保护它们而得到奖赏。森林砍伐将立即停止。人们很快会认识到,种植油棕或大豆的最佳地方不是原始雨林占的土地,而是多年前已经把树木砍光了的土地——反正这样的土地有很多。
我们会鼓励人们想办法在利用纯粹的自然荒野时不降低它的生物多样性或碳捕集能力。这样的办法确实存在。本着尊重大自然的精神在原始雨林里寻找未知的有机分子,以求找到治疗疾病的新方法,或制成新型工业材料,或做出新型食物——这样的做法可以接受,条件是当地社群同意,而且做出的发现所产生的商业效益要给守护森林的当地人带来收入。
只砍掉选定的树,小心地按照森林自然淘汰的速度将其去除——这种可持续伐木是允许的,因为事实证明这样做可以维护生物多样性。生态旅游让大家亲身体验受到保护的大自然奇景,可以给自然野生风貌区带来巨大的收入,又不对环境产生重大冲击。的确,将来野趣盎然的地区越多,能去旅游的地方也就越多。
我们还会做出巨大的努力去扩大与纯粹的荒野相邻的土地,并使其恢复自然状态。对于这些努力,最合适的领头人是生活在受人力干扰最少的荒野地区之内和周边的当地原住民社群。生态保护项目的经验表明,只有在当地社群充分参与增加生物多样性的规划并直接从中受益的情况下,积极的变化才长期维持下去。
发生在肯尼亚的一个故事是个很好的例证。马赛人以放牧为生,数百年来在塞伦盖蒂大草原上带着他们的牛羊和野生动物一起吃草。他们不吃四周的野生动物。他们甚至容忍野兽每年把他们的牛吃掉几只。随着肯尼亚的发展,马赛人的人口也增多了。后来,家养牲畜的过度放牧开始成为问题。在它们附近生活的野生动物开始消失。
为应对这个问题,马赛人各家联合起来创建了保护区,以促成野生动物的回归。他们同意在放牧时注意保护多种植物,这吸引了很多不同种类的食草动物回归。当然,食肉动物也随之而来。保护区重新野化后,他们给对环境影响不大的观赏野生动物的观光小屋发放了许可证,允许其在他们的土地上营业。这个模式开始日见成效。回来的野生动物越多,来旅游住宿的人就越多,马赛人的收入也越多。
仅仅几年后,一些马赛人已经开始减少自己的牲畜数目,好进一步增加野生动物的数量。我在 2019 年访问这些保护区时,年轻一代的马赛人争相告诉我,他们现在重视野生动物更甚于自家养的牲畜。邻近的马赛社区看到他们的成功,现在也采用了保护区模式。通过成立用野生动物走廊连接起来的保护区网络,不出几十年,就有可能使得野生草原从维多利亚湖的岸边一直延伸到印度洋。原因很简单——人们发现生物多样性有真正的实际价值。
就连欧洲很久以前就得到开垦的土地也有希望重归自然。随着对产粮地需求的下降,欧洲国家的政府表示,它们可能会改变给农民的补贴,转而鼓励农民在使用土地时尽可能地增加生物多样性和碳捕集。
这种新制度可能在欧洲千百万公顷的农地上引发惊人的反应。我们很可能会看到灌木重新长起来形成树篱,取代人造栅栏。在林下种庄稼的复合农林业将呈现炸式增长。农场上会重现池塘和河道。对生物多样性有害的农药和化肥将渐失吸引力。农民可能会转而种植可以把害虫从庄稼那里引开的作物,并采用有助于再生的技术使土壤自然而然地肥沃起来。
最热心提倡这种野化种田方式的也许是肉类生产者。人们采纳了以植物为基础的饮食后,买的肉少了,可能也会更加挑剔,更重质量而非数量。他们可能会特意去买使用能够捕集碳和促进野生动植物生长的方法饲养的牛、羊羔、猪和鸡的肉。
为满足顾客需求,养殖农也许会放弃原来的密集型围栏育肥技术,不再使用进口饲料喂养层架式鸡笼里的家禽,而是转用别的方法,如林牧复合,即长年在林地里放养畜禽。用这种方法饲养的禽肉产量比密集型喂养低得多,但其无害地球的生产方法提高了肉的售价。树木把动物排放的废气完全抵消后仍有多余作用,还可以为动物遮蔽烈日和风雨,这对改善动物的健康和产肉量都很有必要。反过来,动物则为土壤施肥,并吃掉不受欢迎的杂草。
林牧复合大获成功,就是因为它复制了自然状态。史前时代,欧洲成为大林莽盘踞之地很久以前,是一片有树的草原,草场上分散着一片片野树林。这种风景是各种野生动物游荡进食造成的,那些动物中有体形巨大、性情凶暴的古代欧洲原牛,有现已绝种的欧洲野马,还有成群的欧洲野牛、驼鹿和野猪——所有这些动物在法国的史前洞穴岩画中都有描绘。
英格兰南部两位大胆创新的畜牧者正在努力重建这类天然的动物种群2000 年,查理·伯勒尔(Charlie Burrell)和伊莎贝拉·里(Isabella Tree)决定在他们 1 400 公顷的农庄克内珀庄园(Knepp Estate)放胆一试。
农机和农用化学品价格的不断上涨把他们土地贫瘠的农场推到了破产的边缘。于是,他们决定放弃干了一辈子的商业耕种,让农场回归自然。他们把所有田地整成一大片开阔地,选择品种与数千年前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动物最为相近的牛、矮种马、猪和鹿,让它们混在一起,一年到头随意游荡,没有人工喂养。食草动物这样自然而然的共同生活方式复制了大自然中动物的互动。在大自然中,斑马和角马一起吃草。斑马吃较硬较高的草,留下的是角马消化得了的比较柔软的叶片肥大的草。
研究显示,用这个方法让牛和驴混在一起吃草的时候,它们比分开喂养增肥快得多。在野生环境中,这个措施以及许多其他互补性措施的效果显而易见。这一切对于确定土地的未来发展方向起到了重要作用,并开始给克内珀庄园带来全新的面貌。放养的各种动物像史前英格兰的野生动物群一样共同活动,开始把千篇一律的农田变为新的沼泽、树丛、灌木林和林地。结果,农场的生物多样性出现了炸式增长。短短 15 年内,这里成了在英格兰寻找各种罕见的土生植物、昆虫、蝙蝠和鸟类的最佳地点之一。
查理和伊莎贝拉的野地农场仍在生产食物。每一年,他们都对农场中不断变化的植被能养活多少动物做出估算,然后把多余的宰杀掉。事实上,他们扮演了顶级掠食动物的角色。克内珀不是保护项目,因为它没有目标,也并不特意偏向某些物种。它不过是让动物来决定地貌,而动物们干得好极了。
克内珀庄园不仅拥有破纪录的生物多样性,它的肥沃土壤还吸收数以吨计的碳,农场地上河道的改变也在减轻下游的洪水。可以说,克内珀庄园这个运营良好的畜牧场现在是最接近不列颠古时自然状态的地方。热情前来的参观者络绎不绝。农场除了肉类收入和得到的补贴外,还能通过生态观光游和野生世界宿营增加收入。
在生物多样性得到适当回报的时代,野地农场会普遍存在。只要模仿自然状态中动物群体的组成来混养动物,就能使环境回归自然状态。如果无法靠旅游来补充收入,也许可以从事其他副业,如清洁发电。
今天制造的巨大风力涡轮机可以竖立在开阔的草场上,甚至像德国正在做的,安装在森林上方,这样就不会打扰下方的野生状态。未来的畜牧场主如果能得到合适的支持,可以不仅生产食物,还能修复土壤、从事碳贸易、做护林员、当导游、生产能源、照料大自然 —总而言之,做善于发掘土地的自然潜力、利用其可持续价值的土地监护人。
可以想象,有了合适的动力,野地农场可以扩大规模,改变土地的全貌。就生物多样性而言,地区大了,回报总会更大。如果相邻的土地拥有者同意共创收入,他们可以联起手来创建没有边界的广大园区,在很多方面类似马赛人的保护区。
目前,一些土地拥有者已经组成了群体,开始把几十万公顷的土地连成一片,在北美大平原上和欧洲喀尔巴阡山脉覆盖着森林的陡峭山谷里执行增加生物多样性的项目。这是有可能做到的。
一旦工作大规模铺开,就有机会实现重新野化最激动人心也最有争议性的雄心——重新引进大型食肉动物。在生物多样性和捕集碳得到回报的世界里,如果有足够的空间,就应该这样做,因为它会带来所谓营养级联效应的好处。
最出名的例子是 1995 年美国黄石国家公园重新引进狼的举措。狼群回来前,大群大群的鹿在河谷和峡谷处长久驻足,啃食长在那里的灌木和小树苗。狼来了以后,鹿群不再这样做了,不是因为狼群吃掉了很多鹿,而是因为狼把所有的鹿都吓跑了。鹿群的日常活动发生了变化。
现在,它们频繁移动,不再在空阔处长时间停留。没出 6 年,树长了回来,浓荫遮住了水面,鱼可以躲起不被发现。谷底和坡上长出了一丛丛大齿杨、柳树和三角叶杨。林间鸟类、河狸和野牛数目大增。狼群也猎杀郊狼,致使野兔和田鼠有所增多,于是狐狸、鼬和鹰的数目也随之增加。
最后,就连熊也增多了,因为它们可以捡食狼群吃剩的动物尸体。秋天到来后,熊还能大嚼长在树和灌木上的浆果,以前这些树和灌木得不到机会长出果实。
结论十分明显 :在黄石公园这样的地方要增加生物多样性,要捕集碳,只需把狼引进来就可以了。
欧洲大陆的森林转型进程预计到 2030 年会产生 2 000 万到 3 000 万公顷的废弃农地,现正规划如何处理这些土地的欧洲人在积极探索这个思路。空出来的农地面积等于一个意大利。若想要森林通过自然成长回归农地,最好尽可能地增加它们的生物多样性和碳捕集效率。对于懂得大自然的真正价值及其对稳定与福祉的贡献的政府来说,野生世界的回归正在成为一个切实可行的政策选项。
所有刺激措施都是为了在 21 世纪末实现一个比世纪初更自然野性的世界。谁若心存怀疑,只需看一看哥斯达黎加这个国家,就会明白正确的鼓励措施能够取得多大的成果。
一个世纪前,哥斯达黎加 3/4 以上的国土都覆盖着森林,很多是热带雨林。到 20 世纪 80 年代,毫无节制的伐木和对农地的需求使该国的森林覆盖面积缩小到仅占国土的 1/4。政府担心继续毁林会减少野地提供的环境服务,于是决定采取行动,拨款给土地拥有者,让他们重新种植当地的树木。
短短 25 年后,哥斯达黎加的一半国土就再次为森林所覆盖。现在,哥斯达黎加的野地创造的收入是国家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该国身份特征的核心因素。
想象一下,如果我们在全球规模上做到这一点会是怎样的情形。
2019 年的一份研究提出,理论上,重新长起的树木可把人类活动排放到大气中的碳吸收 2/3。土地的重新野化是我们力所能及的,无疑也是很有价值的。在地球各处让土地重回自然野生状态将促成生物多样性的回归,而生物多样性将发挥它最拿手的作用——稳定我们的星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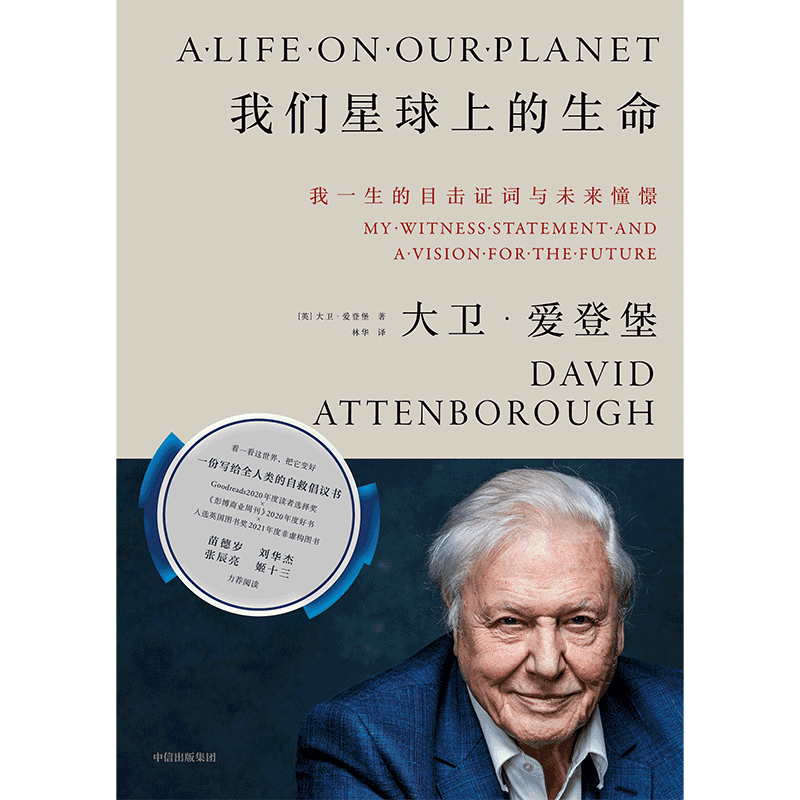
书名: 我们星球上的生命 : 我一生的目击证词与未来憧憬
原书名:A LIFE ON OUR PLANET:My witness statement and vision for the future
作者:[英]大卫·爱登堡(David Attenborough)
译者:林华
定价:65.00元
出版时间:2021年6月
出版社:中信出版集团
本文摘自《我们星球上的生命:我一生的目击证词与未来憧憬》(经中信出版集团授权),原章节标题:《未来憧憬:如何重新野化世界》,作者:大卫·爱登堡(“世界自然纪录片之父”,英国杰出的博物学家、探险家,BBC电视节目主持人、制作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