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扫码打开虎嗅APP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信睿FM(ID:thethinkerFM),作者:张慧(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黄剑波(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人类学研究所),编辑:蓦然,头图来源:IC photo
2022年的春天,我们仍然处于新冠疫情的长期影响之下。随着深圳、上海等城市先后进入大范围检测和封控的紧急状态之中,最初的那种焦虑和恐惧仍旧普遍,与此同时,还有一种无以名状的疲倦感,在新日常中弥漫开来。
我们或许可以称之为“倦怠”。作为一个近两年十分流行的词汇,倦怠既是一种个人感受,也是医学描述中的“突发应激能力”被掏空之后的状态,更是一个社会结构性的症结。倦怠的背后,是对秩序和确定性的期待,以及优绩主义的陷阱。
除了学会与风险和不确定性共处,我们应如何以一种更积极的姿态应对?今天的文章由两位人类学者张慧和黄剑波共同撰写,讲述新冠疫情时期的倦怠,并呼吁一种有“痛感”的关系。在此分享给大家,以期带来些许思考和慰藉。
——编者按
焦虑是否一定是一个时代病症或现代性问题,我们难以确定,但是我们大概可以确定我们确实生活在一个焦虑的时代,一个焦虑无所不在、全面覆盖、深度渗透的时代。这是我们的日常生活经验。
焦虑是否是一个中国特色问题或发展阶段问题,我们也难以确定,但生活于当下中国的我们大概也可以确定这是一个全民焦虑的时代:几乎每个个体都能感受到不同程度和类型的焦虑。
而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更为关注的显然是社会性的焦虑和结构性的焦虑,尤其是其具体的生成机制和文化逻辑。确实,焦虑的生成和强化有着其具体的社会性和文化性,观念性和处境性。
一年多来,因为新冠疫情,我们被笼罩在一种全方位的焦虑和全新的不确定性之下,习以为常的生活模式似乎也很难回到从前,比如不戴口罩出门。在一个习惯了每天都有to do list(待办事项),年终要盘点总结,去到每一个餐厅、景点、国家都要打卡的时代,这种无法做(长远)计划、无法预知未来半年、一年甚至更久的生活无疑给习惯了全球化与流动性(无论是货物、人员还是信息)的我们带来了对不确定性的新体验。
我们对新冠疫情暴发初期的紧张、焦虑都不陌生,无论是不停地刷手机、看新闻,还是对身处其中的风险的切实恐惧;我们对发生如此大规模疫情蔓延的无助和恐慌也并不陌生,无论是抢口罩、无数次地洗手,还是需要就医的等待及信息不对称带来的“病急乱投医”;愤怒和悲伤也不少见,正如美国人类学家罗纳托·罗萨尔多(Renato Rosaldo)所描述的,悲痛之中隐藏的难以名状的愤怒甚至足以使菲律宾的伊隆戈人去砍下敌人的头颅……[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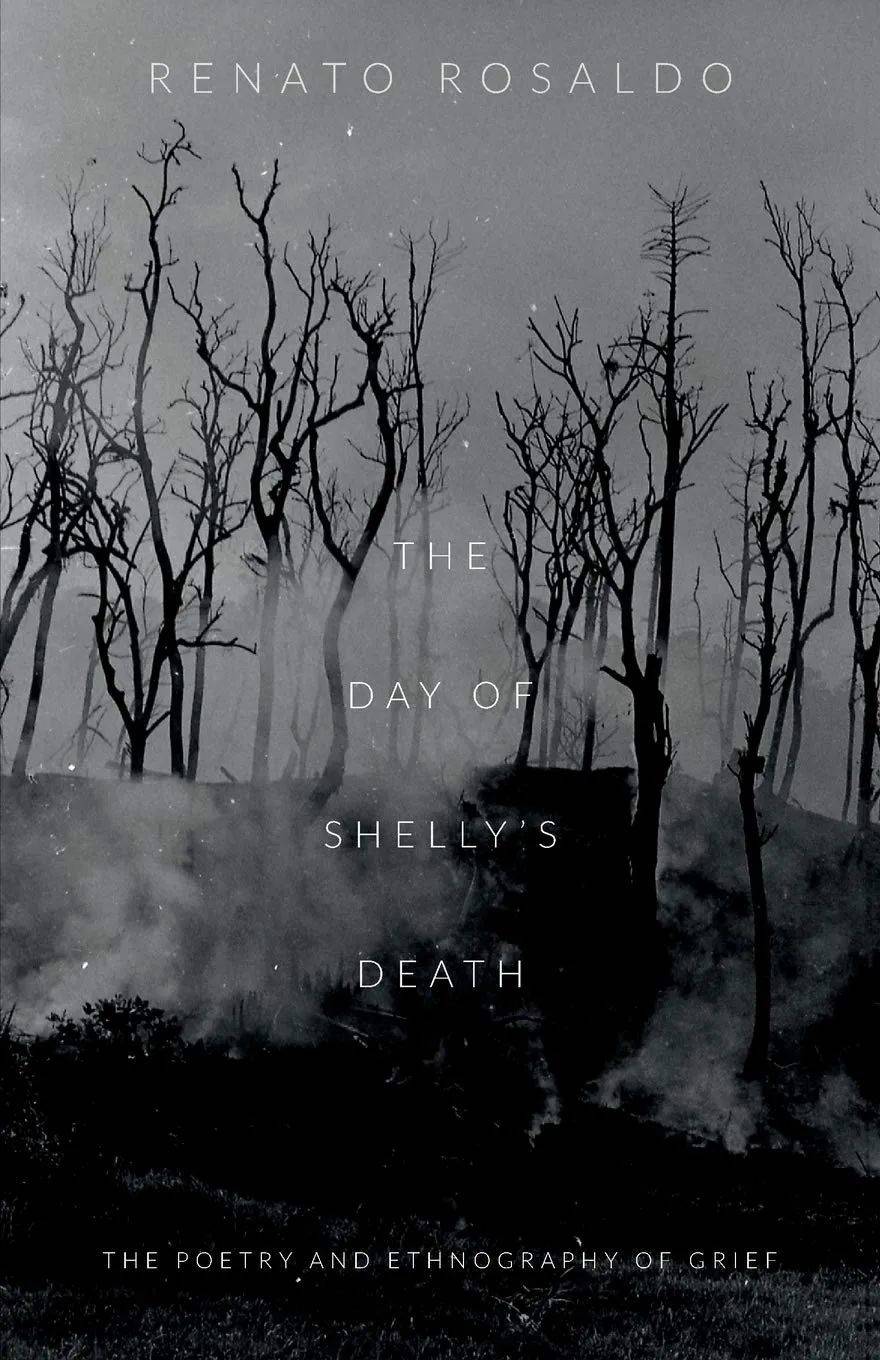
The Day of Shelly's Death
Renato Rosaldo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13
无以名状的“倦怠”
除了这些可以被“命名”的情感,似乎还有许多无以名状之物,说不清的“累”“提不起精神”“无所适从”及“效率低下”。
科学记者塔拉·荷利(Tara Haelle)在一篇题为 Your “Surge Capacity” Is Depleted —— It's Why You Feel Awful (《你的“突发应激能力”已经耗尽——这是你感觉糟糕的原因》) 的文章里提到了一个医学词汇——Surge Capacity(突发应激能力)。其指代一系列心理和身体的应激系统在人类面对极端压力(比如自然灾害等极端状况)下的短期生存机制——但自然灾害往往在短时间内发生,即使灾后重建非常漫长。
而这次疫情不一样,这场“灾害”到底什么时候能结束还是未知数。荷利的文章指出,这种短期的应激能力在帮人类度过灾难之后就会被耗空,需要时间才能恢复,让人类有可能面对下一次的灾难。但在一个长期的疫情状况下,应激机制并没有一个结束、恢复、重建的过程,所以突发应激能力被掏空之后的状态就变成了荷利所描述的一种“焦虑似的抑郁加上赶不走的倦怠”(anxiety-tainted depression mixed with ennui that I can't kick)[2]的复杂混合体。
在全球不同地区都经历了或多或少、或长或短、或紧或松的隔离、禁足、封城的背景下,澳大利亚天主教大学的乔纳森·泽克博士(Jonathan L. Zecher)在Acedia: the Lost Name for the Emotion We're All Feeling Right Now(《倦怠:我们目前感受到的那种失去的情感的名字》)一文中提出了一个用来描述古希腊人的情感的词汇——Acedia(倦怠)——来描述当下的状况。
Acedia的古希腊文原义是指一种无痛无感的迟钝状态,是对任何事物的漠然,是根本上的不在乎。在公元5世纪记述了这一感觉的神学家约翰·卡西安(John Cassian)如此描述这种感觉:“像是经历了长途旅行或是持续很久的斋戒之后,身体的无精打采,以及疲惫的饥饿感……下一秒他开始左顾右盼,然后抱怨没有人来看他。他不断进出房间,不断向上看,好像觉得太阳落得实在是太慢……”[3]
在当时,人们认为Acedia不会影响城市人或是生活在群体之中的修士,只有那些独自修行的人才会因为空间和社会的隔离而产生这种感觉。按照泽克的说法,很多政府对疫情的应对在很大程度上复制了独自修行的修士的状况:社会隔离限制了社会交往,封城导致了活动空间的限制,在家工作或失去工作使我们日常工作和生活的界限被打破,或完全改变了此前建立的生活秩序和节奏。
被“悬置”的时间
14天的集中隔离、7天的居家隔离,封城第XX天……疫情自发生开始也引入了一套新的时间叙事。这套时间叙事有其流行病学依据,但也切实地改变了我们习以为常的日常生活安排。在不能出门、不能聚会、不能旅行的时间里,时间感被重构,我们也生活在一种不能确定未来日期的“悬置”之中。
在人类学研究中,时间本就是一个相对之物:中国的农历是一个以耕种为中心的农业时间表,“三十而立,四十不惑”是古人对人生历程的期待……在人类学中,时间的另一个重要面向是针对暂时性(temporality)的研究。
正如一个关于“暂时性”的民族志研究中所提到的,“无聊、等待、无事可做、线上活动以及不作为,是人类学探讨时间的重要维度。因为恰恰是在这些时刻,时间流动的规律性被打破”[4]。当习惯的时间安排和时间感受到限制和挑战,我们对既有生活的理解也不得不相应被打破和重建。

《世界上最糟糕的人》
“不确定”和“失序”
无论是个人层面上感知到的焦虑,还是社会结构意义上的焦虑,都有着某种对于失序或出位的强烈感知和反应。而这正好表明人类对于“应当如此”的向往,对秩序或在位的想象。对秩序的预期可以是航班按时起飞、快递当天送达、商场正常营业……这种秩序可以是个人设定的、习以为常的,也可以是社会文化所安排的、约定俗成的,当然也可以是更为宏大的全球政治经济结构的产物。
与失序对应的是关于“不确定”的研究,无论是针对doubts(某种信仰或信任崩塌所导致的怀疑),还是uncertainty(人类所认知的、定义的或试图控制的不确定),都在试图发现和理解当某种秩序被破坏之后人类的社会文化应对策略。
正如学者常常论证的,在风险中存在客观和主观的区分。客观的风险可以是真实的威胁,而主观的风险则更多地基于文化的观念、信仰,甚至针对这种风险的知识和认知也是可以协商和改变的。基于这一本质,所谓的失序和不确定可以既不完全是客观的,也不完全是主观的,而是在一个被认为有价值的东西受到威胁的情况下出现的。
这种“不确定”与人们如何确认、感知、理解和控制风险的一系列观念有关。比如,我们的时间焦虑可能与“与时俱进”“只争朝夕”的文化观念有关;我们常常提到的住房焦虑、教育焦虑,也许恰恰是因为住房和教育承载着我们认同的核心的内在价值体系——比如对家的依赖、“望子成龙”里隐含的对向上流动的期待……
当在追求这些核心价值时,人们面临巨大的经济压力和挑战,与此相关的焦虑也就不可避免了。
“秩序”与对生活的“掌控”
让人无处可逃的疫情使我们重新反思生活中的那些“确定”,并遭遇了更多的新的“不确定”。荷利在《你的“突发应激能力”已经耗尽——这是你感觉糟糕的原因》一文中提到,生活在“新常态”之中的应对方法之一就是:接受不完美、降低对自己的要求。以前两周能做完的工作,现在花一个月才完成也没什么;当你什么都不想做的时候,就给自己放两天假。
事实上,这种焦虑和倦怠在成就高、成绩好的人身上表现得更为明显,也更难克服。而在时间的“悬置”之中,我们也可以重新思考,哪些价值是对我们最为重要的,哪些又是可以被舍弃的?
显然,人类面对和应对不确定时的身体和心理反应既是个人的,也是社会文化的。如何重建自身的“秩序”,如何重建社会对于“确定性”的需要,是我们需要共同面对的问题。正如那句著名的引文所说,Uncertainty is the only certainty there is, and knowing how to live with insecurity is the only security(唯一确定的是不确定,与不安全共处是唯一的安全感)。这也许是新冠疫情给我们上的重要一课。

《世界上最糟糕的人》
回到合宜的位置:在关爱中活下去
不过,在新常态的情境下接受不完美,降低预期,并不意味着“放弃治疗”“认命”“投降”。事实上,这些描述虽然都是斗争式的语言,但指向的是战败之后的沮丧和绝望。长久以来,我们已经习惯了这种“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的思考方式。
如前文所述,焦虑指向的除了恐惧和愤怒,还有可能是倦怠、失去活力。倦怠的根本在于无望,这是在“空虚混沌”状态下无法逃避的处境——“渊面黑暗”之际,还有什么可期待的呢?摆脱这种混沌或失序的出路,或许正在于修复和重建各种合宜的关系:天与人、地与人、人与人及人与自我的关系。
换言之,回到合宜的位置,在彼此的关爱中勇敢地活下去——尽管我们面临的是“血淋淋的现实”。我们需要找回“痛感”,找回对人、事、物及世界的真切的关怀和在乎。毕竟,有痛感,有在乎,表明还有盼望,有活力,生命仍然在运转之中。
我们无须完全同意人类学家阎云翔对于中国社会正在全面且快速个体化的判断,但他所描绘的一些现象至少让我们心有戚戚。我们大概可以说,正是孤零零的个体在一个强大的、充满了危险或风险的外部社会中的这一意象,日益强化了作为个体的人的恐惧和无时不在的焦虑感。
问题在于,这并不仅限于自我关系的纠结,我们的经验现实似乎是,每个人都成为别人的威胁,每个人都不在其当在的位置上或关系中。作为群体的人似乎也在以彼此为敌,生活在一个充满敌意的竞争性的族群关系、地区关系或国际关系中。
文明的冲突不仅是一种学术观点,在一些地方和人群内部更是一种立场和主张。进而言之,作为类别的人似乎同样也在与天地争斗,结果则是整个自然界似乎也在做出反抗,从食物,到土壤,再到空气、气候、宇宙……在当下,这也是一种“新型”病毒。
我们或许还可以从古希伯来人那里找到一些可资借鉴的思想资源。例如,“爱里没有惧怕。”这句看似鸡汤的话语在当下仍有直接的意义。不过,这里的“没有”不是有和无的意义上的“没有”,而是指“惧怕”可以被安置、面对和转换。更重要的是,在这个表达中,爱不仅仅是一种情感性甚至情绪性的东西,而是一种持久的、有深度的、恰当的关系。
换言之,在(爱的)关系中就有可能面对恐惧,面对无以名状的焦虑甚至倦怠。进一步,若处在(正确的或合宜的)秩序中,或许就可以免于过度的焦虑。个体的人之间如是,群体的人之间如是,作为类别的人与其生活的世界也如是。
人类学家和哲学家摩尔(Annamarie Mol)在The Logic of Care(《关爱的逻辑》)一书中也有类似的表达。尽管摩尔批评的主要是现代西方医学及现代西方社会的个体主义哲学和人际关系,希望在过度强调个体自主的“选择的逻辑”的这个时代,重新去寻找一种更健康、持久和深刻的“关爱的逻辑”,呼吁一种关系性的人类生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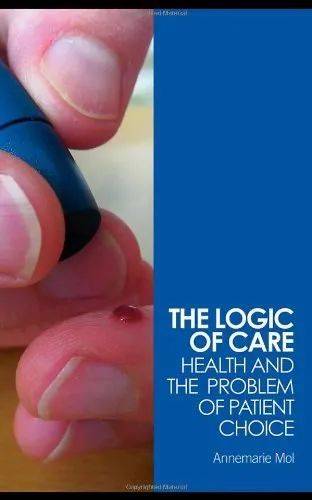
The Logic of Care
Annamarie Mol|Routledge 2008
或许更为重要的是,在指代深度关系的同时,“关爱”还是一个动词。甚至可以说,如果没有具体的行动或动作,所谓关爱的合宜关系是根本不存在的。只有当你真正投入了对某人或事物的关爱的行动,对其精心地照料(care for),才能说明你真的在乎(care about)。
而这种照料和在乎正是对那种无以名状的倦怠(Acedia)的回应和可能出路,是存着盼望的带有活力的行动,尽管这一过程可能非常艰难,常常伴随着眼泪与汗水。显然,不同于倦怠所描绘的那种根本上的冷漠,这是一种有痛感的关系:你痛,我也痛,因为我在乎你。
注释
[1] ROSALDO R. The Day of Shelly's Death: The Poetry and Ethnography of Grief[M].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14.
[2] HAELLE T. Your "Surge Capacity" Is Depleted- It's Why You Feel Awful[Z/OL][2020-8-17]https://elemental.medium.com/your-surge-capacity-is-depleted-it-s-why-you-feel-awful-de285d542f4c.
[3] ZECHER L J. Acedia: the lost name for the emotion we're all feeling right now. [Z/OL][2020-8-27]https://theconversation.com/acedia-the-lost-name-for-the-emotion-were-all-feeling-right-now-144058.
[4] DALSGARDL A. et al (ed.) Ethnographies of Youth and Temporality: Time Objectified[M].Temple University Press, 2014.
文章原载于《信睿周报》第44期,原标题为《与这个焦虑的时代相处:呼吁一种关系型的人类生存》。本文在原文基础上略作删减。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信睿FM(ID:thethinkerFM),作者:张慧(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黄剑波(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人类学研究所),编辑:蓦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