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扫码打开虎嗅APP

本文原载于《信睿周报》第75期,来自微信公众号:信睿周报 (ID:TheThinker_CITIC),作者:胡梦茵 浙江财经大学法学院社会工作系,原文标题:《胡梦茵|人与作物间的伦理叙事诗#“复调人类学”专栏07》,头图来自:视觉中国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在我初赴田野时,怎么也没想到李绅这首家喻户晓的《悯农(其二)》会如此完美地表现了我试图在“人—作物”这一主题之下探寻的内涵。当我进入更深的讨论中时,田地之上经由辛勤耕耘而出的粮食、与天候赛跑收割的橡胶树液,以及山林间经由搜寻而得的菌子,都陆续进入人与作物的叙事之中,组成一组更连贯的诗歌。认识人与作物之间的伦理关系和互动变成了我的目标。
“过度”地解读李绅的这首诗让我惊讶地发现,其中包含了我关注到的几乎所有方面:人对作物施为性的照顾,作物因为自身的特性对人的身体、体验、时间与空间感的形塑,作物对人“礼物”性的回馈以及伴随着作物的流动而传递出去的伦理义务关系。以上这些,几乎构成了我手中这块“伦理”透镜的主体。

作者的田野点——云南省迪庆藏族自治州德钦县茨中村,图为村中稻田。作者摄于2013年8月15日
说“几乎”,是由于对这个主体本身理解方式的不一样。这里包含两层可能。其一是将作物本身拉入人类社会的伦理网络之中。简单来说,就是将作物赋予人格或者道德品格的可能,而最终任何一种伦理关系和互动结果,都是满足人与人之间预设的伦理义务。“盘中餐”喂养了我的家人,我便借由禾苗这一作物履行了自己对他们肩负的责任。从广义上来说,这种伦理赋格的行为对一切有生命或无生命的物都可以进行。但“作物”这一特殊的分类,隐含的不是某类生物的性状,而是其与人以及人类社会的特殊关系。
“作物”之上,本就蕴含着浓重的人的色彩。这既是一种文化的凝结,同时也可以迅速转入任何已知的社会场景或语境:家庭分工与餐桌礼仪、农户与税吏、奴隶与庄园主、商品流通与全球化……在其中任何一种场景之下,作物被赋格以及其参与社会互动的方式都不一样,其上的伦理关系或道德色彩也不一样。
其二可能则是,在更新过的、“去人类中心主义”之后的视角中,作物并没有完全被动地作为人类对自身所处的伦理关系的指代物存在。相反,由于其作为“主体”的可能,作物有了缔结和拓展新的伦理关系的基础。于我自己的阅读和研究而言,这一点似乎更可以理解为:作物与人的互相驯化关系使得二者之间的伦理关系本身便是一种新的类别或样式。
这样,远离农业生活的人(比如去田野之前的我)似乎就很难进入这种特殊的伦理关系之中,也很难理解对应的伦理责任或义务的真正内涵。这似乎可以完美解释在作物产出并进入商品流通领域之后出现的伦理断裂或失调,即人与作物之间那种特殊的伦理责任在作物商品化的那一刻便终止了。
但重要的似乎还是如何理解“互相驯化”这一过程。因为其自身的性状及其与其他物种之间的关系,作物迫使人进入一种工作状态、形成一种身体记忆,乃至于获得一种社会身份。“日当午”似乎是农民痛苦不堪的源头。一位朋友做的关于“薅草锣鼓”[1] 的研究让我突然意识到,“日当午”的选择是禾苗与杂草竞生之后的一种必然结果,而一代代耕种禾苗的人拥有着同样酷热难耐、腰肢酸痛的记忆,甚至也拥有了相似的佝偻的身体,拥有了显明的可识别的 “禾苗农民的身形”。
唐代耕农锄草的对象很可能与湖北山区的农民一样,也是田间那些与作物争夺养分的“杂草”——这显然也是一种根据其与人和社会的关系界定出来的类别。作物似乎永远会在与杂草的竞争中败下阵来,而被伦理义务束缚着的人类则必须站出来接受这场战争。
至此,自然的物种之间的争夺变成了人的肉体与土地、天时以及一些不走运的、被归为“杂草”的植物根茎们的战斗。太阳最毒辣的时候,便是这场战斗最佳的进攻时机。杂草们被拦腰斩断,连根拔起,扔在地上。农民们期待炽热的阳光在烤干自己的身体之前,先一步杀死这些鲜活的根茎,而滴落的汗水则是农民献身这场战斗之外奉献给作物的又一重馈赠。
在现实生活中,人们似乎不会像学者一样醉心于区分这两重伦理关系可能,他们甚至很少能够主动识别出自身的行动是源于与作物已经形成的义务还是责任。只是在他们试图向我或者彼此之间说明某些事情的原委之时,这种似乎是预先设定的伦理关系才会突然被揭示出来。
帕特里夏 · 法拉(Patricia Fara)在《性、植物学与帝国:林奈与班克斯》[2] 这本小书中讲到林奈(Carl Linnaeus)和他创立的分类体系时,准确地指出林奈这一创见背后真正的动机落在了自然哲学以及既有秩序的完美印证上。而当这套分类体系被班克斯(Joseph Banks)以及大英帝国的殖民官员运用到对在殖民地发现的物种分类时,这套“知识体系”便成功地在词语上将外部的世界(殖民地)纳入到欧洲的、熟悉的世界中来。植物学被收编为帝国的一部分——将殖民地的一切成功地命名并且归纳进分类体系,便是成功的殖民。
这里很重要的一点是,“可识别”或“可分类”的植物是有效标志人类社会边界的象征物。中国西南边陲的一片橡胶林,便是如此区别了危险与安宁、疾病与健康、不可言说之痛与清晰可诉的疾病的地界。人与橡胶的互动使得这一界限被不断地往返跨越,人与橡胶间的伦理关系也就此形塑了一代胶农的身体与记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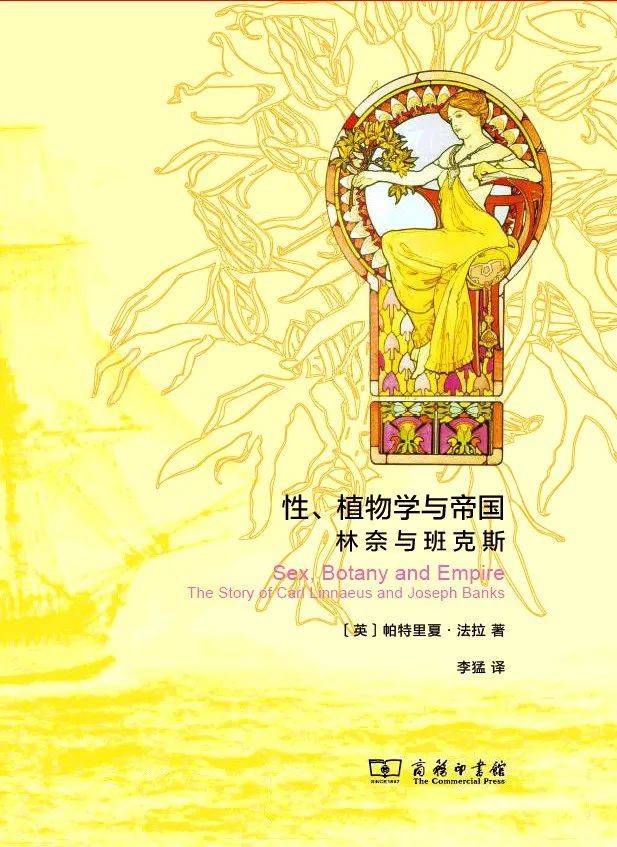
《性、植物学与帝国:林奈与班克斯》
帕特里夏·法拉 商务印书馆, 2016
云南临沧市沧源县的班洪佤寨[3] 在20世纪70年代时成立过橡胶种植队,全寨的青壮年不论男女都被编入生产队,从事橡胶林的围护和橡胶的收割采集工作。曾经的胶农[4] 陈金叶在当时还是一位年轻的姑娘,全程参与了开荒、橡胶种植、胶水收割以及生产队解散之后的分产到户活动。橡胶林于她而言不仅仅是一段集体生活的记忆或者佤寨胶农的身份,同时几乎直接成为她生活中苦痛的源头。
1980年左右,陈金叶生过一场大病,她昏迷了五天,几乎药石不进,村里的医生也束手无策。陈金叶奇迹般地苏醒后,医生和她对这场疾病的病因虽各有怀疑,但都和橡胶林有关。这片橡胶林原先是一片烂泥塘,而这些佤寨人都住在山上的老寨中,远离这片烂泥塘。在当地老人的记忆中,这并非人应该进入或者居住的空间。
新中国成立之后,老佤寨的居民们被迁下了山,这片烂泥塘也在村民的努力之下变成了橡胶林,但这种鲜明的由橡胶标示出来的空间似乎依然暗藏着问题。村里的医生认为,橡胶林里依然留存有烂泥塘中的蚊虫,正是这些蚊虫导致陈金叶患上了恶性疟疾。而陈金叶则暗自揣度,认为村中老人所言烂泥塘中的瘴气才是自己生病的根源,这些瘴气也继续在橡胶林当中飘荡。

云南省临沧市沧源县班洪佤寨橡胶林,田远帆摄于2017年6月。图片由作者提供
开荒过程中的蚊虫与恶臭气息似乎永久地留存在了橡胶林里,而从橡胶栽种到成熟出胶的七八年里,陈金叶都是育苗员。这份工作显然让她负有了照顾这些橡胶树的责任。为了就近照顾橡胶树,陈金叶住在橡胶林旁边的小棚子里。小棚子常年漏雨,陈金叶怀疑她的风湿病就是因为淋雨得上的。当遇到连日无雨的情况时,陈金叶则需要不停地挑水浇树,以防树苗干死。如果树苗死了,作为育苗员的陈金叶少不得受到批评,并且会有扣工分的处罚。
终于,橡胶树成熟,可以割胶了,陈金叶天不亮就要去割胶,不然胶树不会出胶水。同时,新鲜的胶水不能沾水,一旦遇到暴雨便会全部坏掉。当地多暴雨,也让陈金叶经常遭遇抢时收胶水的慌乱,稍有不及,一天的辛苦便会全部白费。而橡胶林施加于她身上的折磨在其弃她而去的那一刻点燃了陈金叶的怒火。这便是后来那场大病的缘由。陈金叶自述,自己因为橡胶林分产到户时的不公而“太生气,晕过去了”,严格来说,应该是不公导致的郁郁寡欢让林中的那片瘴气有了可乘之机。

云南省临沧市沧源县班洪佤寨橡胶林中割橡胶图景,田远帆摄于2017年6月。图片由作者提供
如今的陈金叶被贴上了“身体不好”的标签,这既是常年与橡胶打交道的过程中真实的耗损,也是她对自己和她孕育出的橡胶林最终关系的定性。在其中,可以看到一种对于橡胶树的“回馈” 的期待落空之后的痛苦。开荒填塘时的辛劳、漫长的等待、天不亮就起床赶往橡胶林以及每次变天时慌乱的抢收……这些苛刻的要求都被达到时,陈金叶才被视作一个合格的胶农,一个“好” 的育苗员。这是一种无形的道德判断,并且以橡胶树的存活与死亡、胶水品质的好坏得出一个最终的定论。
这些不断的道德判断最后让陈金叶获得了一具劳损的身体,一具充满风险的身体。这具身体随着陈金叶在橡胶林分配问题上的爆发而导向了一个不可逆的结果。在陈金叶的眼中,分配结果很显然是对她此前对橡胶林的付出的无视,同时也是对她在与橡胶树的伦理关系中的角色的否定。愤怒的陈金叶在病好之后决定切断彼此间的义务关系——如今再遇到暴雨,不会骑摩托车而无法赶往橡胶林的陈金叶选择直接放弃那些需要收集的胶水。
在陈金叶的故事当中,强有力的国家在场是另外一条叙事线索。从村寨的搬迁、烂塘变为良田,到橡胶种植队的成立、工作的分配、工分的计算,再到橡胶林的分配,这背后陈金叶很显然处于另外一重更大的伦理关系之中,即作为个人的她与作为集体的“国家”。橡胶树很显然成为两者之间关系的一种承载物,凝结着个人与国家之间的伦理互动以及义务关系的履行。陈金叶“不好”的身体不仅仅是她在和橡胶树的关系中承担伦理义务的证明,也是她在与国家的伦理关系中未被良好照顾的证明。
需要精心照料的作物似乎总是倾向于让耕种者失望,它们似乎常常逃避伦理关系中回馈的义务,但在一些不经意间进入人类社会的物种身上,这样一种回馈的关系以不寻常的方式完成了。
隆达 · 施宾格(Londa Schiebinger)在《植物与帝国:大西洋世界的殖民地生物勘探》[5] 中探讨了作物对人进行馈赠的另外一种可能:“在整个18世纪,金凤花被奴隶妇女当作反抗奴隶制的武器,她们用这种植物让自己流产,以免孩子生而为奴。”在这个例子里,奴隶女性和特殊情景下进入人类社会的植物之间形成的关系不仅呈现出当时奴隶制的社会情景,还介入到了人的再生产——亲子关系的改变上。
作为堕胎药,金凤花不但形塑了加勒比海黑奴女性(流产/不育)的身体,还塑造了她们的社会与亲属关系。金凤花的堕胎作用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是加勒比海的黑奴(后裔)女性专属的知识,这不但逃脱了前文所述的林奈的分类体系带来的殖民化威胁,还使得金凤花—黑奴女性之间的伦理关系完全脱离了殖民地庄园的日常生活。堕胎对女性身体的伤害在这里是为自由和反抗助力,而女性对金凤花的照看则似乎体现在其对于药效的秘而不宣之中。对于秘密的隐藏和保护似乎是一种常见的道德性行为,而其最终的回报便是一代又一代的黑奴女性可以在某种程度上重新获得自身子宫的掌控权。这种掌控权在18世纪显然是对欧洲社会通行的生育道德的极大悖逆,因此宣告了抗争的存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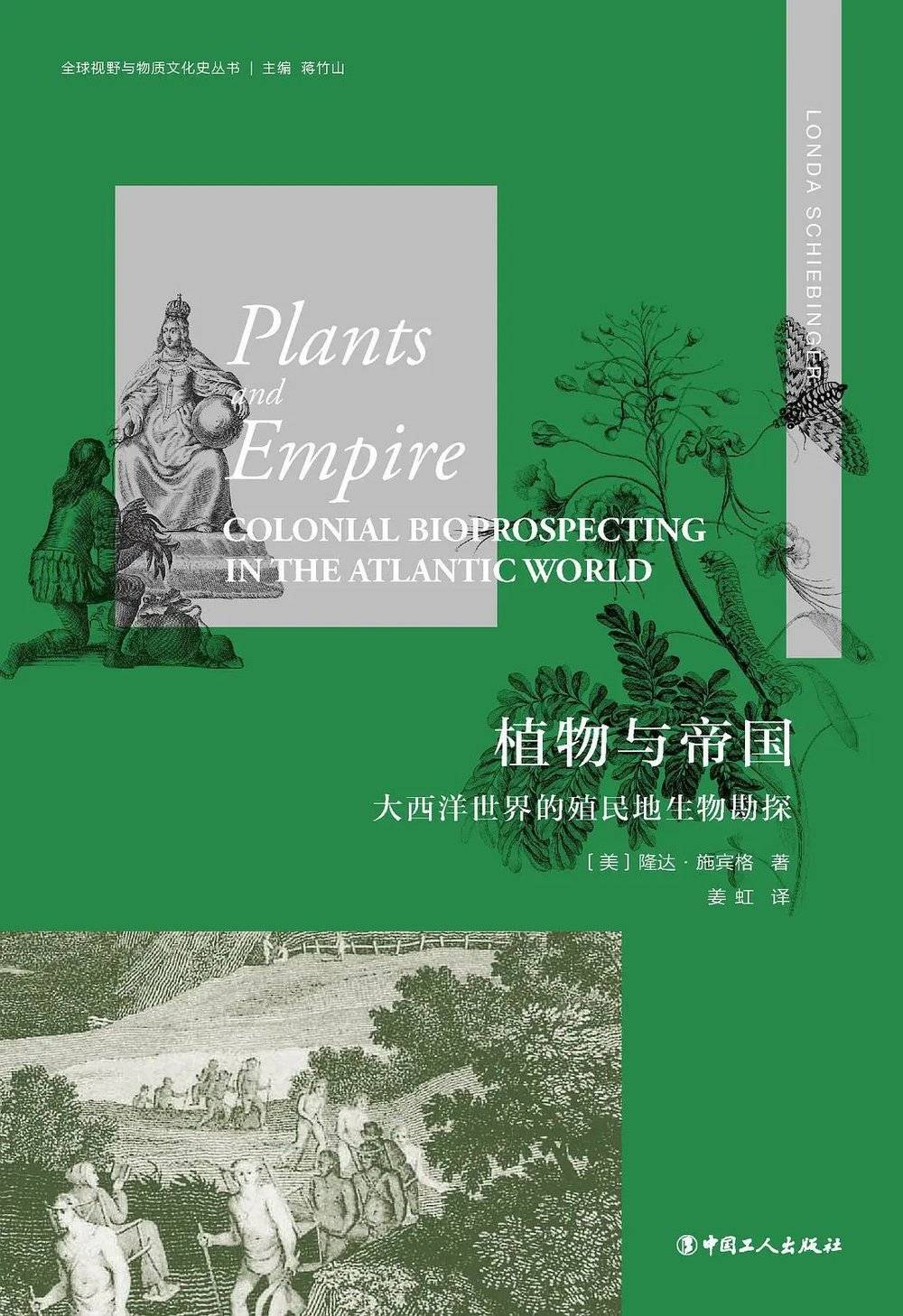
《植物与帝国: 大西洋世界的殖民地生物勘探》
隆达·施宾格 中国工人出版社, 2020
并非所有的人与作物间的伦理关系都纠结和挣扎于漫长的共存状态,但那些偶然建立和生发出的伦理关系同样也会被各种随机的因素重新打断。伦理关系断裂往往会伴随着非常强烈的社会影响,也会卷入更多社会中已经存有的伦理秩序。
我在2017年的冬天(大概11月的时候)重新回到了我的田野点。刚到便听说了一个令我震惊的消息:村口那户人家8岁的儿子前两天刚刚从山上坠亡。这家的女主人芳姐与我年纪相仿,此前我也多次去她家拜访,印象中她这个刚上小学的儿子十分懂事,一直帮着做些家务。思索再三,我还是决定去拜访一下芳姐,以表吊唁之情。芳姐让我进了屋,不太有精神,但也没有过于哀恸的迹象,于是我小心翼翼地开口询问这场悲剧的原委。
出乎我的意料,芳姐并没有太抗拒回忆这件事。孩子那天是跟着爷爷一起上山的,目的是捡些菌子(即松茸)回家卖钱。但在迪庆藏族自治州,采松茸的季节一般是8-10月,11月的时候已经不怎么能见到松茸了。果然祖孙俩一路几乎一无所获,这时孩子试图爬到更陡峭的地方,那里说不定有没被挖走的松茸。悲剧也是在这个过程中发生的,孩子失足摔下了山崖,当场身亡。

茨中村村景。作者摄于2014年7月16日

茨中村的葡萄园、稻田和山林 。作者摄于2013年8月17日
罗安清(Anna Lowenhaupt Tsing)在《末日松茸:资本主义废墟上的生活可能》[6] 中提到,松茸因为无法被人类大规模种植,其出产几乎全靠人工采集。聚集起来的采集工人依靠自身的技术与经验,在松林中寻找这种特殊的蘑菇的踪迹。
在迪庆藏族自治州,除了没有一群因松茸聚集而来的采集者,其出产方式并无太大差异。每家每户在松茸季都会派出成员上山寻找。在我田野点的村子里,上山采松茸的活动也很平常,但是正因为松茸是“随机”出现在某棵松树周围或是埋在松针下面的,搜寻者无一例外都认为这是大山送到他们面前的宝物。
这里,一个非常传统的伦理关系——山区的人与山的关系——便出现了。具体来说,松茸会不会出现在你将走过的路径边,会不会突然散发出香气引起你的注意,这一切都是山神对人好意的体现。这种好意是建立在人对山神的尊敬和顺服之上的,过度的贪婪和掠夺注定将破坏这种良好的互惠关系。人们尊重山林,山林喂养人们,这是一种彼此照顾、不断进行着赠与和回馈的伦理关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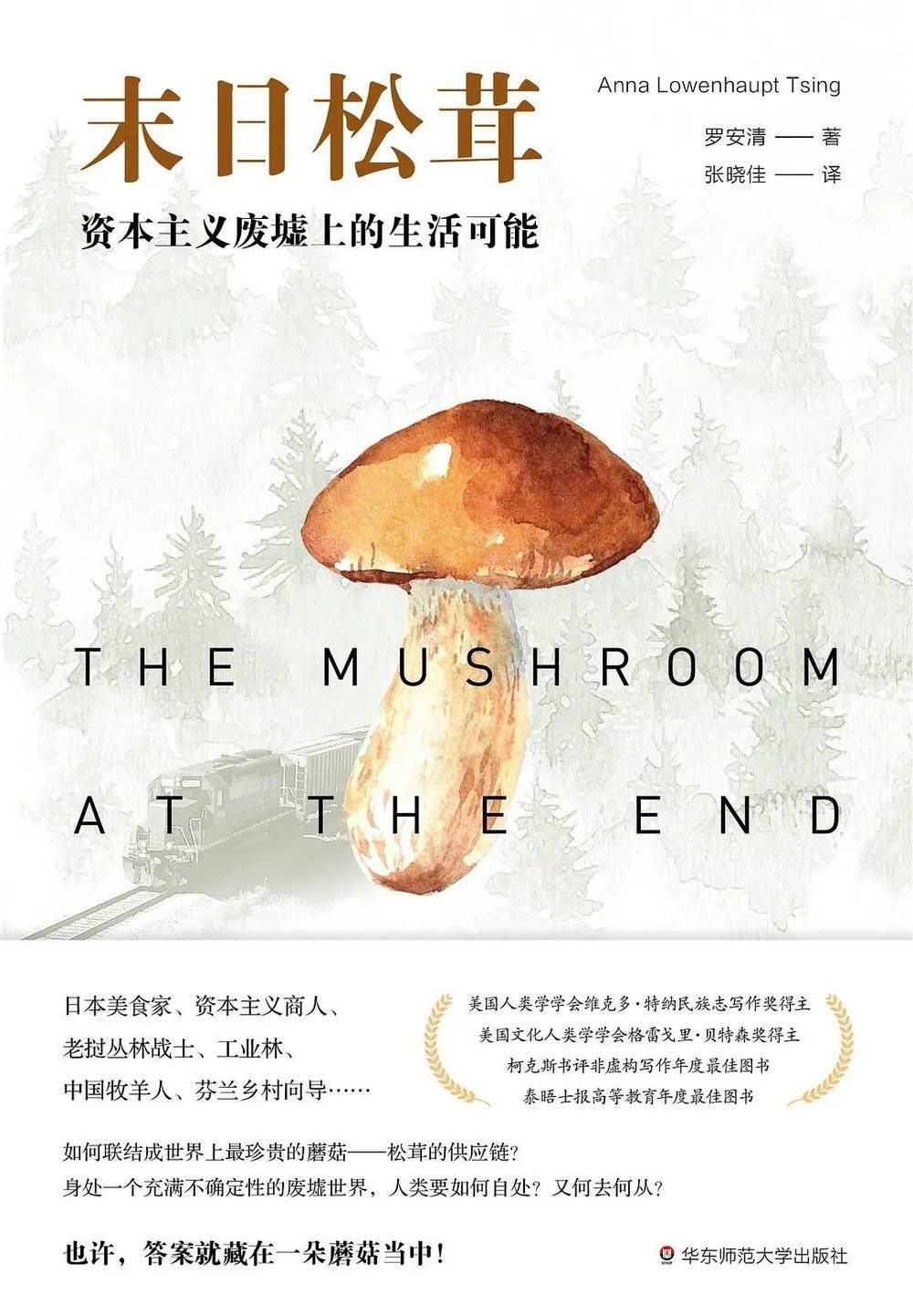
《末日松茸: 资本主义废墟上的生活可能》 罗安清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20
至此,芳姐的孩子的意外似乎有了一个伦理性的版本——贪婪的掠夺者不但无法获得财富,反而会失去宝贵的东西。我无法知道这个版本是否可以解释芳姐的状态——内疚和羞愧压过了意外带来的痛苦和怨恨。但是,另一个村子关于核桃林的故事似乎印证了这种人与山之间的伦理关系并不是偶然地通过作物传达出来的。在这个村子里,人们不断烧山开荒以种植核桃树,最终在村中老人的担忧之下,一场泥石流摧毁了几乎全部的核桃林,而村民们不得不请来喇嘛做法以平息山神的怒火。这个故事里的核桃林没能像陈金叶的橡胶林一样留存下来,但在某种意义上,二者都是被安置在了错误的位置上的标志物。
最后,用诗人余秀华的《我爱你》[7] 中的句子为人与作物之间的叙事诗做一个结尾:
若是给你寄一本书,我不会寄给你诗歌
我要给你一本关于植物,关于庄稼的
告诉你稻子和稗子的区别
告诉你一棵稗子心惊肉跳的
春天。
注释:
[1] 主要在湖北恩施一带进行。
[2] 帕特里夏·法拉. 性、植物学与帝国: 林奈与班克斯[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6.
[3] 这个佤寨在中缅边境正式划定之前属于班洪部落的势力范围, 故沿用。
[4] 黄剑波、胡梦茵、田远帆. 滇边佤寨的病痛叙事、脆弱性与具身化国家[J].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8(05) : 57-64 .
[5] 隆达·施宾格. 植物与帝国: 大西洋世界的殖民地生物勘探[M]. 北京: 中国工人出版社, 2020: 5.
[6] 罗安清. 末日松茸: 资本主义废墟上的生活可能[M].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20.
[7] 余秀华. 月光落在左手上[M]. 北京: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2020: 2.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信睿周报 (ID:TheThinker_CITIC),作者:胡梦茵 浙江财经大学法学院社会工作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