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扫码打开虎嗅APP
虎嗅注:本文是虎嗅“新女性”系列策划的第三篇文章。蒋方舟,1989年生于湖北襄阳,作家,《新周刊》副主编。7岁开始写作,9岁写成散文集《打开天窗》,2008年考入清华大学;2009年10月,蒋方舟获得第七届人民文学奖的散文奖。2012年从清华大学毕业,就任《新周刊》杂志副主编。主要作品有《打开天窗》《第一女生》《正在发育》《邪童正史》《故事的结局早已写在开头》《东京一年》。
文丨虎嗅特约作者 饭饭
蒋方舟在朋友圈、微博上与采访时,频繁地说自己“老了”。
她今年才29岁,但她在《圆桌派》聊天,对面坐着四十多岁的梁文道,五十多岁的窦文涛,甚至马未都,她都能坦然而又频繁地说出“老了”、“可能岁数大了,见得多了”这样的话来。
她7岁开始写作,9岁出书。签售会上,曾有读者大吃一惊:“我从小看你的书长大,没想到你才刚刚考上大学……”
11岁给《南方都市报》写专栏,每月收入4000,她是家里赚钱最多的人,甚至有一段时间,父母双双辞掉工作,全家靠蒋方舟的稿费生活(女儿养全家的状态一直持续到现在。前段儿某天,她听到父母聊天说:“方舟可不能生病啊。”她还挺感动,然后爸爸接着下半句:“对呀,得还房贷呀……”)。
上初中时,课业压力大增,她一度想退学写稿,班主任觉得她成绩不错,退学实在可惜,允许她不做作业。她每天下午放学回家,玩一会儿,吃饭、看书,完成写作必需的信息输入,睡觉。第二天三四点钟起床写稿,写到7点去上学。
这样度过了整个初中。
这么算起来,蒋方舟的职业写作生涯,已经持续了二十多年。她是写作的童工,确实称得上“老”。
1
她并不害怕变老。
她从小觉得自己人生幸运,所得大大超出自己应得的,再有抱怨,就是“得了便宜还卖乖”。从小在校园之外,身边都是比自己大的人,餐桌上也总是最小的一个,因此她小心翼翼,即便被冒犯,也不敢表达自己的意见。
她一边软弱,一边痛恨自己的软弱。
随着年龄增大,这种情况才有了改变。特别是今年,心态上的变化微妙又明显,“不再把自己当小女孩了”,她解释道,“性别感少了很多……不是说把自己当成男的,是说再没有那种曾有的性别暗示。比如此刻,我会觉得我们只是两个‘个体’的交流,我不用出于自己的性别身份而在表达上面做一些改变。”
在接受虎嗅采访时,她坦然开放,不回避任何问题,应答起来简直有点滔滔不绝又停顿得恰到好处。说得兴起时,两只脚挣脱凉鞋,双腿缩到椅子上自然一屈。
这是一个自信于什么问题都能接得住的姑娘,采访前她甚至表示不用看采访提纲。
“我现在甚至变得凶巴巴的,活得更开心、更舒服。”她说。但也有人说她:“你变了。你没有以前那么乖了。”
2
她不在乎别人怎么看。
“十年前各种声音就不会影响到我了。”
2000年,她的《正在发育》被媒体评为十大烂书,批评铺天盖地,大部分都在说她妈妈“拔苗助长”、炒作、代笔、伤仲永……这反而激起了她的斗志,她感觉自己与妈妈成为了一个“命运共同体”,她要用不断的写作来证明自己,也保护妈妈。
她争取到清华自主招生降60分录取的资格,被批评挤占了普通学生的机会和名额,18岁的她回应说:“一代代年轻人希望通过自己的人文特长进入大学,接受深造,我只是参与了开路。”
22岁时,她写《给清华的一封信》,质疑身边同学对体制不假思索的接受甚至维护,招来学生联名请求清华大学开除她……
这两年,她参加各种视频节目,被观众吐槽长得难看、身为女性却自我矮化、浅薄、爱抢话……她也从不回应。
但她的确每天都在网上搜索与自己相关的细节与评论,像在不间断地以自我为样本做第三方观察与研究。采访头一天,她刚看了一条网上评论说“蒋方舟除了反性骚扰,还有什么代表作品?”这一问,倒让她有点扎心。
她把自己殷勤搜索网络评价的行为解释为——她需要随时用外部视角来检查自己,她害怕自己活在一个虚假环境中自我美化与犯错,而不自知;最终像她看过的某部小说里提到的阿拉斯加犬一样,看上去跑的是一条直线,然而不知不觉方向就偏离了180度。
“对我来说,这个‘不知不觉’是一件很恐怖的事情。比如说‘不知不觉’时间就过去了,‘不知不觉’自己就变成了很讨厌的人。”她很警惕这个。
蒋方舟自称对未来没有规划、且认为规划无意义,但她显然也讨厌“失控”。相当理性。
3
面对争议保持超然、自在甚至自嘲,蒋方舟并非生来如此。她一路都在冲破她与身边同龄人之间的某种隔膜与纠结。
她的高中母校华师大一附中,是湖北省最好的高中,为了照顾她的写作,学校分配给她一间带电脑的单人寝室,这间寝室引发过同学各种流言蜚语,大家怀疑宿管阿姨每天帮她洗衣服;停电的时候,也有同学怀疑是学校专门将电量输送给蒋方舟写作……
在同学们的围观议论中,她的高中是这样过的:每天头戴耳机,一个人住,一个人走路,一个人吃饭,一个人去学校超市买东西,一个人坐在教室最后一排,身旁是一堆清洁工具:拖把、扫把和撮箕。
“自从我开始写作,就无法与人轻松自如地交谈了,”她觉得自己的话题和语言都太书面化,“我的笑话和噱头也职业化到一点真诚也没有。”她对和同学之间那种需要经营才能维护的友谊持怀疑态度,妈妈几乎是她成长路上唯一且长期的交谈对象。到今天,妈妈尚爱兰还是她笔下与言谈里的常客。
她在高中时期写的一篇博客叫《可笑我独行》:
“于是我遇到最大的困难就是无人分享。喜事不能分享就像衣锦不能还乡,穿了华美的衣服却走在黑而没有路灯的马路上一样难过。”
这种与集体疏离的生活在大学时期继续。老师经常跟她说,蒋方舟你不要把自己边缘化,蒋方舟你要融入集体。
但她并不知道要如何融入校园集体,也不愿融入。这种状态在清华变本加厉。之前,她长期生活在校方、妈妈、书籍为她架设好的世界与观念里,虽是孤单长大,但被保护得很好,而大学生活骤然将她攥出那个温室,让她看到外面世界原来有这么多跟她不一样的价值观,它们之间的矛盾与冲击甚至可谓“暴力”。此情此景,真的是冲击到她了。她一度不无愤怒地认为别的同学“活错了”“想错了”,想象自己在一个充满恶意的校园环境中,因而在态度和行为上表现出某种抗拒,“我对他们凶恶,然后外界就真的对我不友好了。”
“心态确实有问题,我在大学精神状态不是很好,每天,吃就是唯一的寄托,不停地吃。吃成胖子,又更加不愿意去上课了。”
她承认大学里那两年,自己犯了“荒废”的错误。
而终结这个错误的,是爱。

21岁的时候,她初恋了,对方不是学校里的同学。
她感觉到自己被爱、被信任,同时自己也可以去爱别人、信任别人。前所未有的安全感。自己不是不能被理解的。“对方是有跟你不一样的价值观,但因为你爱对方所以你也很愿意去接受,所以你学会了怎么跟不同的价值观去正确相处,而不是觉得都是别人错了别人傻逼,这是恋爱对我特别大的一个改变。”
“我觉得自己(从初恋中)学到了特别多,自己得到的成长远远大过所谓的伤害。”她说。
这是很善于在情感与时间中得到心灵滋养而不是纯被消耗的一个人。不是所有人都拥有这样的品质与福分。对这一点,她或许明了,但说出来却是自嘲的口气:“发现我人生中大部分心理问题都是通过衰老和过气自然解决的。”

3
每年新年第一天,蒋方舟会富有仪式感地为电脑日记设一个密码,密码代表她今年对自己的寄语。2017年的密码是“顺其自然”,2018年的密码是“无所畏惧”。
“很多大家觉得重要的资源和人脉也好,或者是什么也好,我觉得我不需要它,那我就没有必要去畏惧它和顾虑它。无所求,就无所畏惧。”
大学毕业两年后,2014年12月,蒋回到清华大学演讲(《在自己身上克服这个时代》),为年轻的学弟学妹,提供了一个个体应对当下社会的解决方案。她说:
“只要有越来越多作为个体的生存者不愿意去符合规则,不愿意面向主流,不愿意那么大程度地妥协和牺牲自己,相信社会的规则会放宽那么一点点。”
年岁渐长,蒋方舟越发希望自己拥有一种正义感,它应该是朴素的——同时,考虑到中国与社会种种现实因素,她承认行使它时需要谨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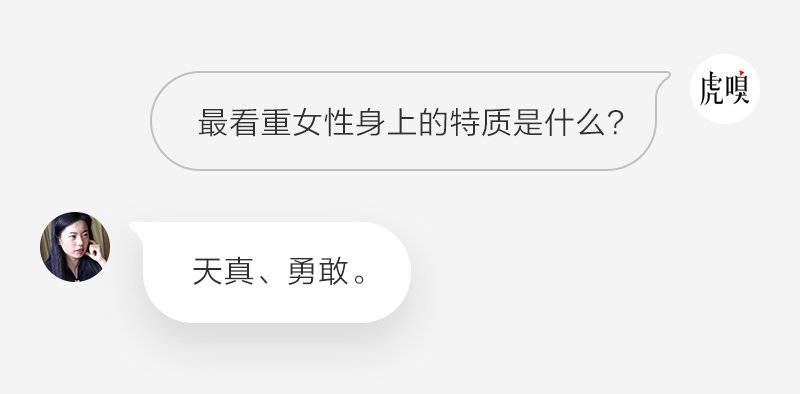
最近的突出一例,自然是公开指证“圈内名人”章文性骚扰一事。
今年7月某个晚上,蒋方舟在朋友圈见到有人在提章文的事,她联想到自己亲身经历,马上想跟随发声,但妈妈阻止了她,说“女孩子不要那么楞”。第二天,她又看到了,这次看到是当事人发的长文,“想了大概有三秒钟”,她决定曝出自己的经历以示支援。
“我与那个女生某种意义上是在一条船上的,所以对于我来说,底线是要保护她最小程度地受到伤害。无论是从言论上,还是她的个人信息上,还是她的人身安全上。”
她不认为这是“勇敢”,它只是一个简单的发声,“甚至都不叫‘站出来’”。
“人们喜欢用‘掺和’去形容某种言论或社会议题的参与,经常说‘你别掺和这事了’ ‘别趟这趟浑水’,以为只要缩一缩头,忍耐一下,等这片乌云过去就好了。我觉得有时候掺和一下也没什么。”
从去年到今年,她意识到自己“有一个很明确的成熟”,“如果有意愿的话,我是有能力帮助到别人的”。
多年前,她曾震惊甚至嫉妒于韩寒微博发个“喂”字就会被转发几万次,也正是在那个时候,蒋方舟意识到何为“公共资源”。
“话语、新闻,都是公共资源,名人笑一笑,哭一下就上热搜,也是在占用公共资源。每个人的时间都是有限的,他们来关注你而不是关注别人,就是因为你有公共资源。大家出了什么事就会去看韩寒对这件事怎么看,韩寒会怎么想,所以在某个时间段,他可能是拥有中国公共资源最多的人之一。我们的公共资源不仅是自己挣到的,还包括上一代人对你的期待、赞美,都是一种价值,都是把他们所掌握的一部分的话语空间让步给你,如果你很轻易地去把它挥霍掉或者是浪费掉,我觉得还是挺可惜的。”
“我很幸运在比较年轻的时候就积攒了一定的公共资源和一定程度的公信力,这些东西仅仅用来自保的话还是太自私了。”她说。
“但这样有被大众与民意裹挟的风险?”我们在采访中问。
她回应得不带迟疑:
“所谓的‘放飞自我’与‘被民意裹挟’并不是非此即彼的关系。纵观整个文学史,所有伟大作家都在自我任性和社会的责任当中不断地摇摆,它是一个动态平衡的过程。每个作家都不断地在这种动态当中去摇摆、选择和平衡。”
“这是作家的职责之一。如果你拒绝,说‘不行,我不要被裹挟,就是要放飞自我’,你就不可能是一个好的、伟大的作家。”
蒋方舟在多个场合提到已过世的南非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纳丁·戈迪默对她的影响。她翻译过后者那篇长达两三万字的著名文章《基本姿态》,这篇文章的核心论点是,一名作家在南非,基本姿态“只能是革命的姿态”,“一个作家必须不仅仅是个作家,必须为同胞的福祉负责。”
戈迪默身上的知识分子情怀与社会性,对蒋方舟是种强烈的引导与示范。
她与比自己大整整30岁、但私交甚笃的作家阎连科合作写过一本书,在台湾出版,叫《两代人的十二月》。他们每个月或对谈,或是共同参与同一主题的讨论。蒋方舟在序言中写道:
“中国在巨变,世界在巨变。文学家置身之外,无法参与历史,无法改变现状。每天的现状都和昨天的现状不一样。文艺家能捕捉的东西何其少?动作何其缓慢?哪怕捕捉了世界变化中的吉光片羽,影响和力量又何其渺小?
“这些想法对于文艺家们来说几乎等同于自杀——怀疑自己所做一切的意义。
……
“往大了说,这是两个作家的尝试,既立足于写作本职,又谋求参与社会,千方百计地找出尽职责的手段。”
对蒋方舟来说,文学与写作不可能是自喟自叹、躲进小楼,她对“文以载道”这件事深信不疑。
4
但蒋方舟发现自己在小说创作上并没有特别高的天赋。大量阅读让她意识到,她很可能穷尽一生,对那些悬挂在天上灿若星辰的前辈天才们也只能吃力地“揣测与模仿”,“你永远不可能走到他前面一步”。
这个最近两三年才有的发现,并没让她沮丧。“认清这个事情还挺好的,早认清早解脱,很多人容易把热情误认为是自己的才华。”
刚好在这个时期,她从当代自由主义思想家以赛亚·伯林的人生经历与态度观念上,找到了安慰与触动。
以塞亚·伯林是出身于俄国的犹太人,11岁时随父母流亡到英国。他原本想要做一个哲学家,后来意识到自己并没有做哲学家的天赋,转而投入观念史的研究。他在二战前后做了很多观念史的梳理和思潮的引导,不但见证了许多历史时刻,也在观念上走在了大众前面。他在思想与理论上的突出贡献,是区分了消极自由与积极自由两种概念。
正如人们所见到,伯林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大部头专著,写的更多的是一些长篇文章,这些文章绝大部分也不是独创理论,而是对哲学史、观念史、各种思想与人物的引述与评论。但他的人生过得非常幸福,蒋方舟说,“这种幸福简直可以被量化:他没有牢狱之灾,也没有真正地被命运捶到谷底,也没有受到政治上的祸害”,他还长寿,活到88岁。
当《伯林传》作者伊格纳季耶夫问起他平静而幸福的生活之源时,伯林答,他之所以幸福是因为他是一个肤浅的人。“我的生活方式比别人想象的要浅薄得多。”
伯林那句著名的自谓“我总是生活在表层上”,击中了蒋方舟,几乎要成为她生活的座右铭了。
“生活在表层,并不意味着对什么东西都采用反讽态度,或是不去做尽责的投入。‘生活在表层’是指不要太信任这个时代对你的承诺和嘉奖。人在得势的时候,容易觉得他(她)跟时代产生了某种别人都无法理解的、深入的感情或是深入的关系,觉得他与时代是一个共同体。但其实不是这样。伯林不会把全部身家都押在某一个历史时刻或事件当中,他其实永远有一点疏离。”
伯林这种处世观念与方式,让蒋方舟甚至有点感动:
“以赛亚·伯林在某种程度上,其实是牺牲了深度,而获得了一种广度。他是一个能够上下兼容的人。可能我也希望自己这样——在很多人看来,在某个专门的领域是二流的,但在很多时刻,我是在场的,而且也能提供某种上下兼容的沟通能力。”

5
戈迪默:“在南非,无论黑人作家还是白人作家,他进入人类团队——这是‘社会’的唯一永久有效的定义——的基本姿态只能是革命的姿态。”(《基本姿态》)
伯林:“人们解放自身的惟一途径就是保持游戏玩家的心态。”(《浪漫主义的根源》)
戈迪默与伯林,一个高度卷入时代、推动社会的正义,一个醉心于梳理与连结各种社会观念、见证历史却保持与时代的疏离。这两位20世纪知识分子的选择与姿态,同时投射于生活在21世纪中国的青年作家蒋方舟身上,成为她的某种“二象性”。
6
现在,除了写作,蒋方舟还将最大的热情投入到免费做一些知识的传播、分享和探讨上,比如她与她一位90后朋友,即将推出一档音频节目《非独立思考》。
对,“免费”。蒋方舟强调这个词。这两年“知识付费”很热,也不乏各种平台与机构试图来撺掇小蒋开一档付费节目,但蒋方舟都以“开出不可能的天价”方式拒绝了。
“首先,我获得很多知识就是趋近于免费的,那我传播它也应该是免费的。纯粹的事情就应该用纯粹的方式来做,我更多地希望这件事我能做得开心而不是说我天天去关注又卖了多少,当(知识传播)这事成了一种买卖,你心态上会有变化。我没有必要、也不想通过这种方式挣钱。”
金钱(商业)与写作,在蒋方舟这里是分而处之的。
但努力保持写作的纯粹性的前提是,你在这个社会能够体面地生活。于是她“以商养写”,通过接手商业合作、录制商业节目来赚钱,每年给自己定一个特别低的赚钱KPI,够养家、还房贷就成,可能用一个季度完成后,她就能在一年剩下的日子中去做最不委屈的自己:读书、写作、旅行。
“写作本身是一个很让人愉悦的事情,但如果你在这上面加了太多的预期,又要完成自己满意的东西,写得让自己开心,又要让大家去认可你,你还要挣钱,你给写作赋予的压力就太大了。”
虽然意识到自己在写小说上并没有那么高的天赋,虽然小说这种体裁十年后可能都会消失,但她还是想要写小说,“我不可能因为这事存在风险,就不去做它。”她想赶在30岁前写完手头的两部小说:一部现实主义题材;一部是国内作家较少尝试的反乌托邦小说。
她在写作上最大的野心,是成为中国年轻一代中,写得最好的作家。在她定义中,70后作家都算“年轻一代”。
饶是把年龄段放得如此之宽,这个赛道,似乎也并不那么拥挤,当下并不是文学高居显学的1980年代。跟她从1990年代一块开始写作的那些少年们,前前后后,很多都自动退出,不再写了,电影工业或商业,是他们常选择的下一站,而蒋方舟都没有兴趣。
“不断地跟人就一些事务性的事情去沟通,包括跟人谈钱,这个东西对我来说非常痛苦。我无法享受这种乐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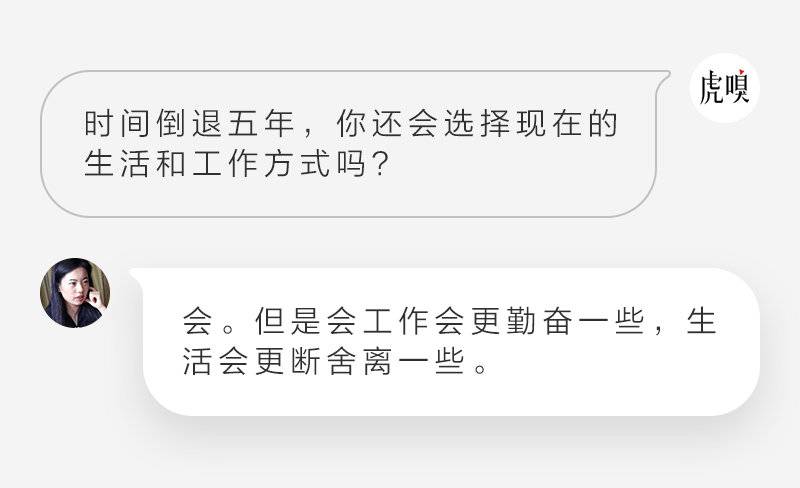
7
蒋方舟29岁了。这是一个对很多人来说还有很大不确定性的年纪。蒋方舟也是。一方面,她对世界的变化充满热情与好奇,对发生在当下世界的各种新闻眼观六路耳听八方,有时甚至显得比一般人还热衷于“吃瓜”(采访快结束时,她兴致勃勃跟我们打听“刘强东明州案有什么最新八卦”),但另一方面,她内心深处某个根基,已很笃定,所有这些变化,于她只是旁观而已,对各种潮流,她几乎从未想过要进去插一脚,哪怕顶着可能被时代与同龄人抛弃的风险。
她认识的创业者与商人不少,有人成长,有人踩空,有人死去。很多同龄人身份在过去几年都有变化,蒋方舟原地不动,默默把她观察到的、关于他们的变化写在每天的见闻里。
她有一颗与她年龄不太相符的老灵魂。
不少年轻人、特别是年轻女性会有“30岁将至”焦虑。她完全没有,反倒,她挺开心的,开心自己终于又可以从“年纪轻”的阴影下挪出一点。别人还没享受完年轻的好处呢,她似乎已受够了,觉得因为自己年轻,受到更多的是轻视而不是严肃对待,哪怕得到的某些赞美也显得轻浮——比如,“美女作家”。
她很反感这样的视角与称呼。
当下惟一让她略感焦虑的是生育。她想要自己的小孩,但这事不像写作可以以耐心与勤奋待之,卵子过一个月就少一颗,自然规律不等人。为了在35岁时也能健康生娃,她决定要好好锻炼身体。
男人么,倒不着急。“作为伴侣,我不喜欢有才华的男人。”她几年前曾这样说,如今更强调,她更看重的是男性身上的“正义感”。

然而她现在已不愿意为了找到那个人,像猎犬一样刻意四处搜寻。“早放弃了‘还有某个圈子里的男人特别好是我不结识的’这种幻想了”,“我不再抱着试错的态度去恋爱,我太了解自己,知道和哪些类型的男人在一起注定会失败,就不去尝试了。”
德国哲学家阿多诺有句话她特别喜欢,也是她的微信签名:“错误的生活无法过得正确”。
————
以下为虎嗅“新女性”系列报道的超长广告时间——
最近,我们首度以1988~2000年间出生,即18~30岁之间的科技界、商界、文化界中国新女性为研究对象,描摹其中的突出样本,准备评出2018年度新女性杰出代表。为什么要以18~30岁为界?各个年龄段的出色女性都很多,但18~30岁阶段的女性,她们已有了自己初步三观,然而还在成长变化;她们成人,但还没有被彻底社会化与庸常化,拥有天然活力,正处在影响社会的上升期;她们更加彻底地代表自己——我们认为,从某种程度上,她们能更突出地代表“新”、同时也具备了社会研究的意义。
当然,与此同时,我们也关注了那些即便进入世俗社会眼中的“平稳”年纪,但依然散发时代优秀特质的人,也会做一些采访与报道。
“新女性”项目,将是虎嗅今后长期年度关注与投入的一个报道与评选产品,希望得到社会各界关注与支持,欢迎金主赞助,与我们进行各种合作,共同为中国新兴女性群体发声。
总之——
感谢您对中国新女性的关注。我们都将在接下来的两个月精心奉上如下内容:
2018年值得关注的新女性一手采访文章,她们可能是您熟悉或不熟悉的;
部分采访视频:新女性何以成为新女性?面对镜头,这是更真实的她们;
“新女性之选”:除了精神特质,这个年龄段的女性在物质消费上还呈现出哪些选择偏好与特点?不同品类下的首选品牌是什么;
年度“新女性”榜单:欣赏的女性没有出现?还可以这样支持她——在评论里提名,她们将有机会成为“年度新女性”,并在2018年度的F&M创新节上持续闪耀。
欢迎扫描海报下方二维码,参与我们精心准备的、盛大的F&M创新节——

点击链接:https://fm.huxiu.com,移步专题了解更多详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