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扫码打开虎嗅APP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回响编辑部(ID:huixiangjf),作者:JiFeng Bookstore,原标题:《现代人的生活太南了,信仰会是解药? | 回响电台No.5-下》,封面来自:东方IC
这期讲的是上海郊区一个叫金泽的小镇。你可能从来没听说过这个地方,但也许你有这样的经验:逢年过节要祭祀祖先,祈福许愿时得去烧香磕头,这些常被认为是“封建迷信”的习俗,在金泽镇可谓“大行其道”。今天镇上仍保留着供奉各路神明的寺庙,每年有数不清的善男信女潮水般涌入小镇祭拜神明,祈求平安。这种现象被当地人称为“香汛”,一同顽强保留下来的,还有迎神赛会、扎肉提香等民间奇观。
本期节目的嘉宾之一,复旦大学的郁喆隽老师在目睹了金泽镇的祭祀过程后,感叹有一种进了侏罗纪公园般的奇妙感受,研究宗教学的李天纲老师告诉我们,这种让我们感到既熟悉又陌生的震撼场面,其实就是民间信仰的一种体现。不过,既然它被贴上了“封建迷信”标签,为什么仍然能在民间生生不息?这仅仅是老一辈的习俗吗?它和我们今天崇尚科学、理性的现代生活方式相冲突吗?对于今天的中国人来说,民间信仰还有存在的意义吗?我们来听听曾经多次造访金泽的两位老师怎么说。
对 谈 嘉 宾

江南民间信仰与现代生活(下)
(以下为音频文字稿及注释)
郁:这一点上(民间是大传统,知识分子是小传统)我和李老师的观点是高度一致。因为之前是学哲学的,学哲学只是关注一个文本,我们说摇椅学者,坐着一个armchair,你就可以知道天下事了。后来发现不对,真的有问题,你不去田野不到底层去看的话,看到都是很片面很局限的,很多书面文本,甚至是地方志,它已经在收集材料的时候进行了大量的取舍,或者对某些民间的传统它进行了一种刻意的压制、过滤、删减,所以真的到底层去看的时候,这种感觉就是跟李老师是一样的,中国文化真正的生命力可能是在基层,历史上是在乡、村、镇一级,我们以往对历史的理解可能过于知识分子气或者太精英化。
在我自己做论文的时候有一个案例,就是浦东地区的迎神赛会,而且正好是1919年。就我们说起1919的话,我们(想到的)肯定是五四。今年2019年,100年过去了,我们想到五四就想到北京那些学生运动、新文化、德先生、赛先生,这都是教科书上告诉我们的。但是就在那一年也正好在春天的时候,五四之前一点点,4月份的时候,浦东原来是有一个香汛季,很多不同地方的寺庙,同时出会,迎神赛会,当中最有名的就是吴家厅,现在它搬掉了,重新建了一个,当时一个状况是什么?就是地方的上海县政府明令禁止出会,但老百姓已经有强烈的意识,他说我们这个不是迷信,我们就是宗教,我们一定要出会,结果是地方上的那些军警和老百姓产生了一个冲突,就变成《申报》连载的这样一个冲突事件。事情发生之后,这些所谓的这些刁蛮的村民连夜开会,就说首先我们这个是一个宗教,他们明确用“宗教”这个词,一个外来的西方概念。而且他说民国约法里面,基本权利规定的宗教自由,那么我们就是宗教,说(和)地方政府产生这样的冲突的话,你们(地方政府)要检讨你们的做法是不是对,提了几条要诉诸司法,也是非常理性的。他们的信仰是一些历史传承,但是在处理冲突的后续事件是非常有礼有节,而且是按照法治来办事情。

上世纪30年代人扮城隍神出巡(文汇学人)
还有当时一个骑兵队的人,可能是不小心开枪走火,就把他们准备出会的会首打伤掉,当时生死未卜,还在抢救的时候,他们连夜开会就说如果这个人死掉的话,我们应该在庙里面给他以后造个像,而且我们应该捐一笔钱。他还有家人,我们要抚恤家人。所以这个很有意思,就是说,有一些民众他的观念思想上他已经与时俱进了,反而是有些地方的治理手段,政府的管治手段,他还停留在一种前现代的传统。这也是我们的一个问题,就是宪法当中规定基本权利,它没有下位法来保证它这个东西,越悬空,这里面产生的这种矛盾冲突、暧昧的空间就会越来越大。
所以讲到这个就很耐人寻味,我们一方面知道教科书上的五四,另外一方面有上海历史上的浦东社庄庙出巡导致冲突的五四,这两个1919年完全是不一样的,所以讲地方历史的时候,两个脉络可能都是都不能偏废,两个都是很重要的脉络,彼此之间可能会有一些交涉,也可能一种平行宇宙的关系,彼此不干涉。所以现代化当然是很重要的话题,民间这样的信仰,你觉得会经历一种怎样的命运?它会顽强地延续下去,还是会无可奈何地就会衰败掉?
李:郁老师讲得非常好,这个是谈五四和现代化的问题,100年前五四拿出来的一个现代化的方案,我觉得是一个知识分子的方案,知识分子启蒙肯定是需要的,就是说你先知先觉,你从西方盗火,当时有一个德先生、赛先生以外,还有一个莫小姐,莫小姐就是morality就是讲道德,那么我觉得五四的号召肯定是对的,是一盏明灯,但是五四的问题是它没有去真正地到民间。他们后来到民间去了,他们做学问的时候他们到民间去了,但是其实中国的社会到底是怎么样,参与社会实践、社会改造,我觉得这个都是没有做。后来做的东西,包括五四的左翼跟右翼做的东西都有偏差的。我们现在来做总结的话,这个偏差就是说其实对民间社会认识不够,只觉得是个经济的问题,或者五四的右翼就认为是一个文化的问题,那么也是一个片面改造。
其实我认为从民间宗教来讲的话,有一部分的东西可能还是一个道德的基础,当时的莫小姐如果提下去的话,它其实跟信仰是有关的,现在大家都已经差不多公认的,道德伦理背后应该是有宗教的。我们现在看西方宗教是如此是吧?但是其实中国宗教也是如此,佛教、道教也能提供一些道德的资源,民间宗教其实也会有,那么这个就要你做一个合理的取舍,这个取舍就是我们一个面向,我们的面向是我们要做现代人,过现代生活,要有理性的精神,同时我们保留宗教上的一些信仰因素。
民间宗教其实它要延续下去是蛮困难的,要有各种各样的条件,也并不是一个自然的状态。日本延续下去了,比如说神道教、佛教净土宗,包括甚至一些从中国借来的儒学、道家道教它也保留,但是最主要的它保留了它的神道教,但神道教是明治维新当中故意保留的,是在明治维新做了一个宗教改革,它用政策保留了下来。但是我们的宗教政策其实是颇值得反省的。我们现在考虑的宗教政策老是安全问题,伊斯兰教、藏传佛教、基督教那些安全问题,什么渗透都不好讲了,但他们一锅煮,就把这些问题连带着处理,佛教、道教、民间宗教,都连带地处理。反过来讲,就是民间宗教和佛教、道教其实是一个传统宗教,它不大存在一个政教分离以后的这种宗教安全问题,它其实面临了一个很大的问题:文化问题,它怎么转型成一个现代生活当中能够接受的一种文化因素,既保留着对整个现代生活无伤大雅,但是它又能起到文化传承(的作用)?
日本的情况表现在它的神道教(日本大和民族和琉球族的本土宗教,分为大和神道和琉球神道。大和神道最初以自然崇拜为主,起源于本州岛和四国岛本地的崇神传统,属于泛灵多神信仰(精灵崇拜),视自然界各种动植物为神祇。琉球神道起源于琉球群岛,以龙宫信仰、御岳信仰为主)保留下来了以后,比如说你结婚要用,办丧事要用,你想有一点仪式感的时候,神道教各种各样的神宫它都可以起作用。我上次在日本开会,在东京边上稍微离市中心远一点,有神社的,然后上班前的中年男子就把自行车一放,就到庙里面去烧一炷香了,然后就上班了。台北街头也经常看到,街角的寺庙,它仍然还在起一个作用,对白领,对这些管理人员,你碰到问题了,家里上有老下有小这些问题,这些宗教都不断地在提供“心理咨询”,然后我们也有求签的方式,欧洲也一样,欧洲的部分它是从忏悔发展过来的。现在大家都说我们的心理学很不发达,其实首先要对我们的宗教心理有所了解,然后你才能对症下药地探索、试探中国人的心理状况,我觉得是这样。

日本东京的神道教庆典“三社祭”(东方IC)
郁:可能前一两代的知识分子对宗教问题有点过窄的理解,就是宗教是关乎一个信仰的问题,关乎一个世界观的问题,说我到底相信什么,其实不是。宗教在老百姓的生活当中,它是个非常立体或者复合的一个事情。传统上五四这一代的知识分子对宗教的反对可能主要是一个经济论证,觉得浪费钱,尤其是在国力还不发达的情况下,在经济比较落后情况下,你把大笔的钱用到这些所谓无谓的迷信跟祭祀当中,显然相比之下还不如用到卫生、教育这方面,所以晚清到民国一以贯之的一个传统,就是从庙产兴学到后来寺庙登记管理条例都是一个很经济式的论证,它要服务于现代化。
庙产兴学就是把庙收归国有,或者收归地方政府,然后移作别用,比如说办学校、办医院。但也有些很有意思的现象,你说上海原来有一个火神庙,就是古代城市都是要拜火神以防走水,这个城市防火是很重要的,火神庙后来就变成了消防队的驻所,所以这是一个抽象继承,旧观念上是有个延续的。当然宗教除了刚说经济上的,它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怎么来建立地方上的集体记忆跟身份,就说你是什么地方人。很多中国人历史上除了家里有宗族祭祀之外,很重要就是你地方上的神明崇拜。比如说泉州、漳州、福州的人移民到台湾之后,他各拜各神,那就是建立一种共同的叙事,这对一个地方社会的稳定也很重要。
刚刚李老师提到了伦理道德,就很多中国古代人他在县太爷面前打官司说不清的时候,他会到地方神明到城隍老爷面前发誓,就说我没有做过什么事情,有的人就是真的做了坏事,他敢在县太爷面前说谎,但在城隍面前他不敢说谎,因为他怕死后遭报应,城隍老爷给他记上一笔,等等。其实中国历史上的这种平行的治理体系,既有官僚的那些治理体系,又有一个依靠信仰,依靠世界观来进行道德教化的体系,两个并行不悖,所以宗教就很复杂很复合,它有经济有地方治理,有道德伦理建设,也有身份认同,等等。所以它在现代化过程当中,它受到的挑战可能也是方方面面。当然很多的人会把它简化,就把它简化成是一种单纯是信。
其实它任何一个外部的边界条件,只要一个条件给抽掉了,比如庙没有了,可能这个信仰也就很难为继下去,或者说它传统的一些生活方式遭受了根本的改变,它可能也会发生一些变化,不是完全消失了,但是它会变得跟原来不一样。我们会在金泽这地方看到一些很有意思的现象,因为历史上金泽是一个航运中心,是江南市镇的一个中心,所以才会有香汛,很多人划船来烧香,但是现在的交通就变成了陆路为主。虽然金泽镇还是在318国道边上,但是它一下子就从原来这个中心变成一个边缘边陲的地方,所以这种交通方式当然更便捷,更远的人可以来到这个地方,但是使得它失去了原来这种市政中心的一个位置。
李老师肯定有更多材料,你考证过,那个地方也是上海最早的一个稻米加工中心是吧?所以它的信仰和它的市政经济也是合在一起的。每逢香汛的时候,它也会有一些集市、庙会,商品交易的这样一个功能,也包括看出会一个没有手机没有电视的时代,是个娱乐活动,所以它又是非常复合的。在现代化过程当中,某些一些很小的外部条件的改变,就会对它产生一些非常意想不到的变化。我不知道李老师有没有观察到什么?
李:金泽这种祭祀、这种香火、这种庙会能不能延续下去?我觉得确实是比较困难的。原先有一个困难,就是说刚刚讲的水路系统、太湖流域是通的,但是49年以后的管理体系是以省市为单位的,我们边界是很严的,水路都是以省市为界,把它建了闸,割断了。我在想这个事这样做,对不对?后来想有合理性,去年嘉兴把死猪都扔到河里边去,结果就漂,如果没有一个闸的话,这些东西都漂到太湖里,从那边就漂到了淀山湖,金泽的河道里面都会出现,是吧?他们是拦起来的。但这几年的政策,我们是要江浙沪一体化的时候,大家想办法要把它给打通,打通以后说不定那些小船就能够进来了。
但是我不抱乐观的希望,最主要的是金泽的这种信仰方式,它不是都市化的。现在都市里边大家不意识到的,我们在上海的市区生活,我们那么忙碌,我们都是核心家庭,谁还祭祖宗?还想得到吗?这种传统的方式,这种中国人的信仰就丢掉了。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这它没有消失,这些信仰的方式其实跑到城市里边来它有转变,它开始转成另外一种方式,变成一个现代宗教,能够组织起来,能够关心老百姓的日常生活,甚至办医院办学校,这个都是西方是18、19世纪教会都做的,那么我们佛教道教也做,做得很好。中国人对灵魂的关注很强烈,尤其是人死了以后要做的事情,要不然这个魂魄鬼神不升天的,然后留在地下,这个是不好的。你看玉佛寺、静安寺,尤其龙华寺,做得很多的,它的收入很大(在于)这部分。
因为最近三四十年其实是宗教是宽松的,但是宽松也导致了很大的混乱,有些做法是权力的干预,有政府权力的干预,也有经济权力的干预。比如说地方政府也是从下面上来的,他们说要发展,不是说要落实信仰,或者是推动传统文化,他不是考虑这个问题,而是说为了招商引资,宗教搭了台,然后经济来唱戏,确实产生了腐败。但是权力本身对宗教也产生了一些偏差。如果我们把宗教的民间的(组织力量)这些都引导到政府的职能上来,自身可以行使很好的职能,做社会慈善,它做一些政府没有想到的、其他组织没有想到的,比如说心理咨询,哪怕就办医院、学校,它有财力,有信仰的基础,有很多捐献,那么这些东西都可以拾遗补缺地来做,完善这个社会。但是如果权力把它引导到一个方向去的话,它就不在民间做事,这个会产生很大的问题。

右侧是金泽镇内自发来维持进香秩序的居民,他们还要维护古桥的安全(王越洲 摄)
郁:是,我们在最近几年的田野调查当中,会经常发现李老师刚才所说的宗教搭台或者文化搭台,经济唱戏。就是说地方政府它现在有一个很强的主导性,在很多地方事务上,街道或者区一级政府就变成一个很强的历史意义上的赞助人,它既是一个你合法性的保证,又是各种政策性的前提的保证,又出钱又出力,它甚至是会找一些专家来设计这样的一个仪式,当然跟我们整个的一个政治文化是有关系。但这会导致一种结果,就是说它本来是一个很民间的很草根的事情,现在它的传统意味发生变化,甚至出现了这种意义的空心化。我们看到有些庙会它是政府主导主持的,也会有出巡,但出巡的时候这个地方的神明老爷是不抬出来的,或者走在路上的时候,穿的花里胡哨的衣服,但老百姓已经不知道这是干什么的。这当然是跟整个城市化、空心化是有关系的,责任不完全是在政府,它可能动机用意上是好的,但是会造出一个有点四不像的东西,跟传统仪式的感觉很不一样。
其实我个人做宗教学,最近和李老师在做田野,还有一个自己的反思,我们五四的传统继承了西方启蒙运动对人的一种自我理解,它有一些局限性。理性的反面可能不一定是非理性,我们以前把人想得过于理性化、条理化,尤其是像自然科学理解的一样,但是你会发现人作为一种社会性的生物,或者作为一种哺乳动物,它有很强的情感的一面,包括个人体验的一面,就是说理性它本身的限度在哪里?它肯定是有限度的,不知道理性的限度,不知道自身限度,它就是非理性。
如果提出这个问题的话,你会发现其实不管科学技术再怎么发展,它依然有一些很要命的问题,未来的不确定性,比如说人的生死问题,人的价值问题,人的意义问题,世界观的问题,它很难用一种所谓科学的方式、理性的方式来解决,这个时候就为信仰留下了一定的空间。所以即便是在我们现代城市人高度理性化、高度节奏化、高度原子化的生活的情况下,不仅信仰不会消失,反而是因为这种高度理性化的、高度原子化、高速的快节奏生活,使得人另外一方面的需求也会更强烈,这种白领的未来不确定性,生活的无意义感,996甚至007的生活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大家都会问这样的问题,这个时候,传统的信仰,不管是佛教、道教还是民间信仰,它都可能成为一个意义的提供者,或者帮助你克服内心的焦虑或者是紧张,或者是帮助你提供一些自己为什么的问题,这是一个很人性的问题了。
李:顺着这个逻辑讲下去的话,我有一个观察,我是觉得做宗教学了以后有一个体会,到了21世纪,我们中国人大概是和全世界其他的人,欧洲人、美国人、日本、印度、东南亚,在一个比较一致的平台上来考虑一个相同的问题。谈论信仰也是这个样子的,以前五四的时候谈信仰,一定是我们中国人跟西方人多么地不同,儒、道、佛,我们完全跟他们不一样,为什么我们不跟他们一样?那么就产生了一个全盘西化的问题。我觉得100年过去以后,我们大概能够接受这样一个现实,就是在不同当中仍然还要去寻找一个共同,而这个共同我觉得今天我们已经被我们共同地感受到了。我们跟其他的西方的宗教学的学者在一起谈论的时候,我们觉得没什么难以沟通的,我们面临着一个共同的问题,是整个人类的问题。
你看,今天的这个是瞬息万变的,高科技的发展是延续20世纪的,我们今天到了整个的生物科技、IT、宇宙……所有的层面都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个时候信仰还在吗?有些人的回答那是不在的,比如说像霍金,以前他认为一定是有一个宇宙的开端的,但是他临终的时候,明确地说,他是无神论,他不认为有这样一个起点,跟一个终点。这是一个时间跟空间的问题,但是它表达了一个现代人的一种焦虑,就是说我们的生命本质到底是什么?
这个问题,我还是相信一些对宗教学有所体会的学者,比如说查尔斯·泰勒(加拿大哲学家,是晚近西方特别是英美道德哲学中首屈一指的思想家、社群主义的主将),泰勒的那本书叫做《世俗时代》(泰勒在书中探讨了这些问题:生活在世俗时代意味着什么?这些变化意味着什么?我们究竟是如何从一个不可能不信仰上帝的社会,走向一个即便对最坚定的信仰者来说,信仰也只是诸多选择之一的社会?他向我们提供了一个历史视角,他考察了现代性的世俗化面向在“西方基督教”世界的发展。事实上,他所描述的不是一个单一的、连续的转变,而是一系列新的尝试。在这个过程中,早期的宗教生活形式逐渐消融或不再稳定,新的形式被创造出来),世俗时代过去,它给我们提了一个问题,人到底是什么?人的精神状态,精神的东西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存在?我觉得现在人类都面临着这样的问题,我们中国的民间从中国的宗教,哪怕是民间宗教,它其实本质上都在思考这个问题,死了以后到哪里去。我觉得中国宗教在这个方面都有很长期的思考,在这个方面,那就跟西方宗教一致了,讨论同样的问题。所以我们也不必焦虑,即使中国的宗教消失了,其实这些问题都还会留给我们。我是这么看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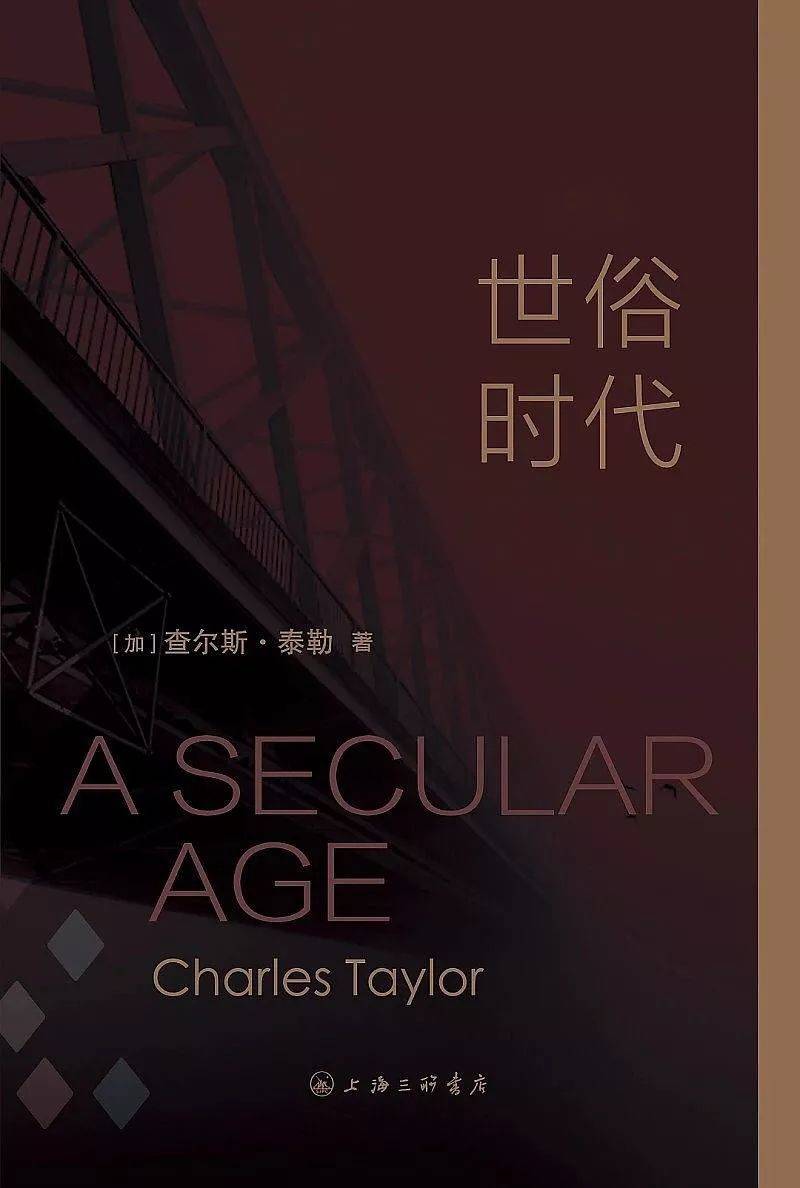
[加拿大] 查尔斯·泰勒,张容南、盛韵、刘擎、张双利、王新生、徐志跃 译,上海三联书店 / 2016
郁:我觉得恰恰这个时候,就是学者对本土文化、中国传统宗教已经有充分的文化自信,但是有些人还没有,所以依然用一种传统的士大夫的想法对它采取一种价值评价,认为它是比较低的落后的,应当被淘汰的,但是没有看到,如果真的没有这些本土的信仰之后,中国文化本身会变成一个什么样子,完全靠知识分子建构起来的那套经典文本的文化可能也很难维系下去,它是有一种共生关系在里面的。
李:现在所有的对中国文化的解释肯定是片面的。我们写《金泽》的时候有一个想法,原来按照中国文化史、中国思想史、中国哲学,我们儒家研究、儒学研究、新儒家都是有一个看法,就是说中国人的宗教观念、祭祀观念是血缘崇拜,是祖宗祭祀,是孝文化,就好像这是唯一的,没有别的解释。那么如果你批判它的话,你就会觉得,看,多落后,这是原始的祖先崇拜。拥护它的人就说,为什么不,这是最自然的情感,他就拿着孝道来要求所有的人,那么孝的上面就是忠,忠孝节义,变成这样一种思维方式,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误区。
我们讲的一个问题就是说,中国文化有另外一种解释,你看金泽的这种祭祀,它不是家庭祭祀,它已经扩展到一个社会祭祀。中国人也有社会观念,也有一个超越个人、超越家族,一个区域性的、地方性的这样一个完整的社会认同。不单单是自己的镇,邻镇也过来了,对面的县也过来了,那么这它形成一个方域祭祀。所以我们的解释,中国主要不是一个血缘中国,而是一个地缘中国,它的社会性、它的地方性是完整的,是有这样一个关系。如果你不从这个角度,至少是这两个角度来看中国文化的话,你是偏的,你就只知道忠孝节义,你不知道这个有人群,有社会,有公域,有地方,有共同体。所以中国人的公是怎么建立的?我觉得我们应该还想想中国的一个问题,不要一厢情愿地把中国解释成其实是应该如何,而不是实际是如何。
郁:对,但是这里面还有一个问题,除了我们宗教社会学,包括社会学、人类学一直在讲的问题,就是我们在理解一个现代化进程的话,就一般的社会动员体系,除了血缘跟地缘之外,还有没有第三种可能?西方宗教提出了第三种可能就是以教会的方式,比如说,绝大部分在上海生活的人都不是本地人,或者说他已经离开了自己本乡本土,传统的血缘跟地缘这两种纽带都已经被割断了。那么在现代化的过程当中,有没有可能产生第三种共同体,或者社会动员方式?不管是社会治理也好,还是形成认同也好,第三种可能性变成一个重要的问题。如果这个社会有第三个纽带,它可能会好一点,就像最早的欧洲社会学家涂尔干所讲的有机团结这样的,如果大家没有纽带,都变成原子式个人,活得都没有很孤单,还没有意义感,大家都很焦虑,也不愿意跟交流,这个社会会有很多的问题,所以依然是会提出一个现代性的挑战。
参考资料:
1. 《金泽 : 江南民间祭祀探源》 李天纲 /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 2017
2. 金泽香汛 | 湃客年度视觉大赛 https://m.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2966892
3. 民国时期上海城隍庙的三巡会 https://cul.qq.com/a/20160714/005191.htm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回响编辑部(ID:huixiangjf),作者:JiFeng Booksto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