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扫码打开虎嗅APP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界面文化(ID:BooksAndFun),作者:董子琪,编辑:黄月,题图来自:视觉中国
“给孩子的电影不等于儿童片、不等于卡通片,更重要的是,不等于简单、明确、阳光灿烂,不是所有以孩子为主角或名为儿童片的电影对孩子来说都是贴切的。”昨日,在思南文学之家,学者戴锦华与作家毛尖围绕日前出版的新书《给孩子的电影》进行了一场对谈。
《给孩子的电影》由戴锦华编著,是一本送给孩子的电影入门书。她和编选团队遴选了50部电影,按照电影史的顺序排列,从1925年上映的《战舰波将金号》《淘金记》开始,一直讲到2019年的《流浪地球》。戴锦华在序言中讲述了编选此书的缘由:“当我与电影初坠爱河之时,我已成年。彼时彼地,我心心念念的是,若是我在孩提时代、青葱年华便能看到如此丰富而杰出的电影,我的生命也许便会有所不同?我也许能更早地窥破自己、洞察生命、理解社会、拥抱人生?”
戴锦华认为电影的教育是爱的教育,但这种爱不是今天快餐文化所说的“甜甜的、有奶油花的、洒满了糖霜的爱”,电影表现的是情爱、是亲人之间的爱、是对生命和世界的爱,也是同理心和共情能力,是由自身到达别人、从此处到达彼处的钥匙。
她说自己之所以会选择1980年的日本影片《远山的呼唤》,是因为它是温暖的而非矫情的,“这种温暖不是刻意生产出来的、虚假的温暖,而带着痛和沉重、带有社会黑暗和个人创伤,最后我们执手相看泪眼,走下去和活下去。”戴锦华在活动现场说,“今后的世界可能会越来越艰难,我很难相信明天会更好,以及我们孩子一定会生活在比我们更好的世界当中,他们可能会面对我们从来没有面对的东西,他们需要从内心找到那种力量,就算山穷水尽的时候,看过的电影的画面可以闪回。”之后她补充了一句,坦言自己 “有点滥情了,我这人不太滥情”。
至于为什么会选《流浪地球》,她认为这是一部相对成功的中国人复制的好莱坞电影,好莱坞叙事模式中也有一些诸如“人定胜天”这类中国元素,而太阳熄灭后把地球开走的设定,是科幻和好莱坞没有的豪情气魄。她本来只是想跟大家分享这部电影有好莱坞的流畅和奇观式的好看,没想到要放大到代表中国崛起这样巨大的意义上。“后来听说很多人在电影片头就开始哭了,我开始对自己的选择有点迟疑。“
毛尖在活动现场发问为何书中没有收入明显色情与暴力的影片,戴锦华回答说,这些年来她对网络常见的道德审查规范深表怀疑和忧虑,如果做一本普通的电影欣赏书,她不会做任何妥协;但这是一本给孩子的书,因此有一些妥协,“我不是要保护孩子,我是为了保护那些自以为懂孩子的人,为了保护自以为要保护未成年人的成年人。我们在新闻媒体和各种短视频APP中看到的色情和暴力还少吗?”戴锦华说,“没有比禁忌更清晰的标志,告诉孩子别干什么,那简直是诱惑。”在对谈之后,界面文化对戴锦华进行了简短的采访。

戴锦华,北京大学中文系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研究所教授,研究领域为电影研究、文化研究、性别研究。《给孩子的电影》属于北岛主编的“给孩子系列”,此系列此前已经出版了《给孩子的诗》《给孩子的散文》《给孩子的古诗词》等等。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界面文化:你在活动中提到,“给孩子的”不代表是“儿童向的”,“儿童向”有什么问题吗?“儿童向”的对立面又是什么呢?
戴锦华:“儿童向”本身不是问题。我所接触的“儿童向”的问题,首先是它把低龄等同于低幼,想象儿童年龄小,智能一定也低;另外我们有一个强大的、一厢情愿的保护意识——今天的家长想要划个圈,把孩子放到圈里,生怕孩子出圈,也担心圈外的邪恶伤害到他——这其实是你自己的想象,孩子从来没在这圈里,而且这个圈不能保证社会上那些真正具有伤害性的力量去伤害他;或者我们一定想象孩子的世界没有黑暗、邪恶、肮脏,总是阳光灿烂、充满正能量,更大的问题不在于正能量,而在于正能量是如此地单一与单调。在这样的意义上,我完全不认同《给孩子的电影》是儿童向的,在编这本书的时候也完全不参照那个标准。
界面文化:《给孩子的电影》一书里收入了《流浪地球》这部电影。在中国科幻史上,科幻和儿童经常是联系在一起的。为什么很多科幻片都被视为儿童电影?
戴锦华:这是一个历史的事实和规定。原来我们在国家的文学体制当中设定了一个儿童文学的类型,把科幻等同于科普,把科普大致设定在儿童文学的项目里,所以历史地存留了科幻与孩子的联结。在世界范围内,科幻是一个“二战”后全面崛起的文类,紧密联系着“二战”和“冷战”的历史事实。
在英美的科幻写作当中,有两个特征非常清晰:一个是对世界面临的巨大危机发出警报,经常是反乌托邦的、有些黑暗的;另一个特征是美国政府曾非常有效地把重要的科幻作家组织在太空总署NASA里,鼓励他们写作,作为太空探索和国防工业的应用文,就是“你们来想象,我们来实现”——这两个特征表明了,在世界范围内,科幻和儿童是相距甚远的主题。
中国正在经历全球化的过程,本土的历史脉络仍然有意义,同时又深受国际的冲击,所以怎么重新定义科幻倒是个挺有意思的命题。我们的“科幻即科普以及儿童文学”和他们的“科幻即应用文以及向世界拉响警报”之间的联系是什么?在这个意义上,我觉得我们倒可以借鉴西方的科幻。中国某种程度上已经经历崛起、站到了前列的位置,所以不再是赶超逻辑之下的状态,于是我们需要警惕那种科学进步的单一信念,同时也要警惕“二战”所提醒我们的——科学可能会被邪恶的力量利用,科学可能会具有戕害人类甚至毁灭人类的力量,从孩子们开始反思和警惕其实挺必要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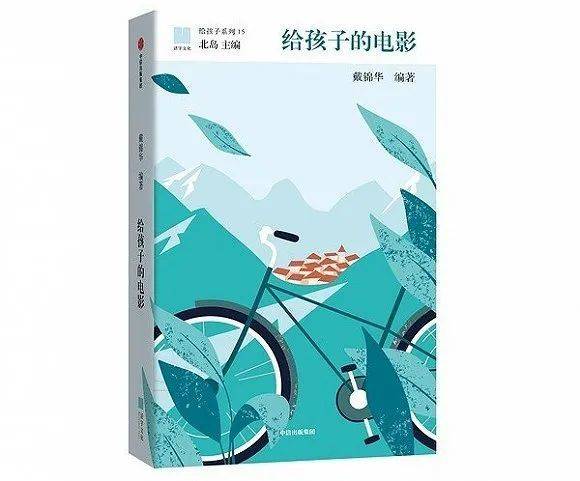
《给孩子的电影》戴锦华 编著中信出版集团 2020-8-5
界面文化:你之前也在一篇文章中写道,以《流浪地球》为代表的中国科幻可能过于元气满满,缺少对发展主义的质询。
戴锦华:美国那么多读者拥抱《流浪地球》,我特别可以理解,今天美国科幻当中那样的元气完全丧失了,所以对美国来说,那是再也找不到的有力度的表达;对于我们来说,它完全是在我们的文化土壤中生长的,而我们某种意义上已经走过了那个阶段。所以刘慈欣、韩松算老一代了,新一代的科幻写作已经不一样了。我们也在丢我们的元气,但也开始增加反思,所以在把孩子和科幻重新联系在一起的时候,我们也想分享我们的元气和反思。
界面文化:你在刚才的活动中提到当今世界正在分裂,这是对世界和未来的悲观态度吗?
戴锦华:我不觉得是悲观,因为前五百年的历史是欧洲引导的历史。以前我们好像有人类共识,但事实上我们只能把自己想象成欧洲人,因为“人”或“人道主义”这个字,就只是指欧洲人而且是欧洲男人,连欧洲女人都不算。今日全球正处于变局当中,这种混乱可以视为一种开始。不是说我们要用中国替代美国,而是开始思考我们是不是有一些不一样的东西,再下一步是不是可以跟别人分享(而不是让人接受)。在任何意义上,我都梦想着一个尊重差异和多元的状态,我认为那毫无疑问是健康的状态。
界面文化:你刚也讲到,对现在网民的“道德主义的标准”深表怀疑……
戴锦华:这种现象无处不在,包括对电影、对故事、对电视剧、对明星的态度,还有在豆瓣上打分的态度。不是说这里面没有真问题,艺术的不道德论是持续了几百年的论争,在生活中我们真的会去痛斥那些渣男或邪恶的女人,真的不想跟他们讲话,那在艺术作品中可不可以去书写?如何书写?一个道德上的败类是不是可能是一个非常迷人的文学人物?是不是读到一个非常迷人的、道德不完美甚至是败坏的人物,就是在诲盗诲淫?这样的问题持续了几百年也没有统一的回答。在看到人们试图用日常生活中的道德来要求和净化文学艺术作品的时候,我都会感到警惕,因为这种“道德主义”一定伴随着一种社会暴力,一种对更多元的、尊重差异的文化的损害。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界面文化(ID:BooksAndFun),作者:董子琪,编辑:黄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