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扫码打开虎嗅APP

作者:殷珊珊(品牌体验设计师),题图来自视觉中国
在表达这件事上,我始终傲慢、无能、企图心还重。欲望来得汹涌,然后潦草退场,装作毫不在意。可以说是表达的猥琐流,不够大气。
很多事情为了达到目标,都可以忍受一定程度的迂回猥琐,唯独表达不行。表达是忠于自我的试炼。如果不能进行真实、正直、勇敢的自我表达,存在与行动只会进一步扭曲意志。

在表达这件事上,我始终傲慢、无能、企图心还重。欲望来得汹涌,然后潦草退场,装作毫不在意。可以说是表达的猥琐流,不够大气。
很多事情为了达到目标,都可以忍受一定程度的迂回猥琐,唯独表达不行。表达是忠于自我的试炼。如果不能进行真实、正直、勇敢的自我表达,存在与行动只会进一步扭曲意志。
这篇文章记录了我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的自我反思,它们关于:
如何才能进行“正直的沟通”?
如何拆除滤镜?与真实世界建立友好关系?
我一直在回避和恐惧的阿喀琉斯之踵到底是什么?
凝视自己害怕的事物能帮助我获得成功吗?
为什么要表达?为什么还在表达?
美妙的生命结构与生命体验是如何被创造的?
如何搭建自己的生命力基础设施?
在投资机构做设计对我来说到底意味着什么?
还要搞教育吗?怎么搞?什么时候搞?
如何理解优势?最大的优势是什么?
还想证明的事情是什么?
这些问题不能说都想透彻了,但确实想明白了。结合我的个人经历与感受记录在这里。


在过往的人际关系中,我过于喜欢和稀泥,总是在回避冲突,always appear to be a nice guy.
为什么老在和稀泥,没办法进行“正直的沟通”?有主观和客观原因。
主观原因是动机的缺席。简单来说,就是mindset里没有认识到正直沟通的优先级。形成这样的情况有很多个人原因,但最根本的,是我一直在回避真实的世界和自己。
客观原因是缺少高频次、高强度、正确反馈的刻意练习。“正直的沟通”本质上是一种技能,要熟练掌握它,必须为自己打造系统的刻意练习方案与正确的反馈系统。
客观的原因不细说了。能力锻炼么,该补位的标准和高强度高频次的训练安排上,剩下的就是交给时间。
唯一值得一提的是,在这个过程中,要有一个能给正确反馈的外部支持系统,不要闷头苦练钻牛角尖。每次想到这个,就觉得自己还是挺强挺幸运的,有靠谱强力的伙伴作为我的训练反馈系统。很爽。
细说一下自己为什么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没有“正直沟通”的mindset。
在认识A哥前,“正直(integrity)”这个词在我的生命中是缺席的。事实上直到今天,在运动员和投资圈以外,“integrity”这个词出现的频率和权重也不算太高。
如果我从来没有遇见A哥和Chien,听到搞投资的人说“integrity”,大概内心是要涌现排山倒海的吐槽弹幕。归根结底,这行业太幂律了,70%的选手是真的烦人。
在溯元,经过一年的互动和训练,我对“integrity”有了非常立体生动的感知——与其说“integrity”是一种道德品质,不如说是一种极度简单、纯粹、强烈的处事风格:按照极高的标准,直接开干。

这里“极高的标准”与“直接开干”是非常“自然”也是非常“反人性”的动作。说它们极度自然,是因为能用这种风格做事的人,都发自内心的体认这种风格,正直是一种无须加工的生存状态;说他们极度反人类,是因为能让“自然的状态”停留在“正直”区间的人,往往经受过大量反人性的训练。
极高的标准来自内心的律令。
这种律令往往诞生于良好的教育,还需要大量的信息、资源与爱去喂养。在这种极高的标准之中,未来作为一种具体可感知的目的地,对此间的生命散发着致命的吸引力。

视觉的确是决策的一部分,但对于心中有律令的人来说,眼前看到的东西只是行动的一小部分原因,那些来自10年后、30年后的与世界交互的标准,指挥着聚光灯下关于未来的交响乐——决定一个空间或者一个位置的是声音。
而直接开干,则是一种通过高强度、高频次刻意练习才能获得的“勇于失败的魄力”。
为了培养这种魄力,背诵“失败是成功之母”是完全没用的,必须在正确的节奏里失败过100次,才能对这种事情建立体感。

这个过程会比想象的更加枯燥、沮丧和无聊,因为这100次失败,并非是走流程的100次失败,而是每次都想赢的100次失败。
“integrity”内含着一种“用少处理多,并且通过处理多来获得更多”的效能美学:
在这个钱和知识都极度充裕的时代,知道自己想要什么,想去哪儿,用什么样的状态生活,直接开干就行。
直接开干,所有的资源都会向你涌来。
链路短促,不过真的有效。但要真正建立这种mindset,并体现在日常的行动与沟通上,每个人还是会遇见不一而足的个性化挑战。
比方说我的问题就是不够authentic,一直在回避真实的世界和自己。
带着滤镜看世界和看自己,会有很多浪漫的认知与想象在滤镜的折射中显现出来。但这种浪漫与天真带来的扭曲,在资源高度密集的节点上,往往会带来系统的灾难。
而在滤镜中产生的思想,由于不接地气,往往也难产生真正的“极高标准”并在“直接开干”的反馈循环中,接受真实生活的检验与挑战。


不够authentic的原因只有一个,就是不能直面自己内心的恐惧。
为了拆除滤镜,需要一些“可感知的指标”,重新建立自己与真实世界的友好关系。
实际上,看世界的时候装滤镜,本质上是对世界的“真实状况”不太满意,或者说,对于自己和世界的“真实的互动关系关系”不够满意,归根结底,是不能直面“真实的自己”。
十二岁之前的世界有海盗、地下城与魔法,那些浪漫与天真的模组让人如此沉迷,以至于进入真实世界的无限游戏时,无法立刻舍弃那个平行世界的所有天赋与荣耀。
Ted Chiang有一本科幻短篇叫《赏心悦目(liking what you see)》,里面的人为了消除“相貌歧视”,会给大家带上一种设备,叫做“审美干扰镜”。
审美干扰镜干扰的是我们所说的联想型审美,而不是领悟性审美。这就是说,它并不干扰人的视觉,只是干扰对所看见的东西的辨识能力。
安有审美干扰镜的人观察面孔同样可以做到洞察入微,他或者她可以辨认出对方是尖下巴还是往后倾斜的下巴,是挺直的鼻子还是钩鼻子,皮肤是光洁还是粗糙。只是对这些差异,他或者她不会体验到任何审美反应。
审美干扰镜通过技术来阻断真实世界传递的信号,从而获得一种封闭的安全感。
认识世界的时候带上滤镜,也是一种极度相似的操作。拥有知识越多的人,越方便给自己抛打精致的滤镜,让精致羸弱的精神在真实世界的汹涌浪潮中得以存活。
但我们不可能通过对差异视而不见来消除差异,不应当试图用政治正确来取代审美体验——而且它们在多大程度上成功了,就在多大程度上使我们的人性沦为贫困。
成熟意味着看到差异,但又意识到差异并不重要。没有技术捷径可走。拆除滤镜的过程,正是成长的冒险。

滤镜的拆除,会带来“可感知指标”的变化——即现实资源的调度能力与富集程度会随着自己与“真实生活”的关系日渐友好而增强。
无论真实的自己与真实的世界是什么样子,只有真正看到它们最本质的样子,才有做出改变的可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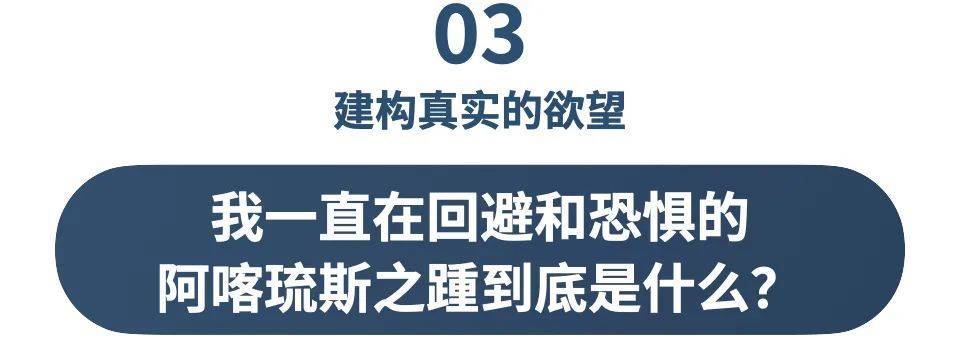

Everything in the world is about sex except sex. Sex is about power.
最底层的恐惧,在于一个想上演英雄主义剧本的个人,猛然发现“真实自我”的无能。
在努力去除滤镜的过程中,多次跌入的陷阱都是相同的:证明自己。
我沉迷在一种极度自恋的表演当中——用义无反顾的英雄主义姿态证明自己。这种雄心壮志的正能量心态,底层追求的是仍然是自己的成功,强调的是自我的“能力”。
之所以对这样的活动如此痴迷,本质上是不愿意正视“真实自我”的无能。无能是一种真实状态,是一种初始状态,也会是个人的最终状态。但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我没有办法忍受自己在这样的状态中停留一秒。更早期的匮乏感编织着此时此刻的恐惧。
然而在这个兴奋剂社会,不分场景的英雄主义会带来灵魂上的彻底失能。一个人如果只有做某件事的能力,缺少不去做某件事的能力,那么将陷入致命的过度活跃之中,产生一种由于过度自恋而导致的忧郁症。


凝视害怕的事物,不会帮我获得成功,也不会让我经历失败,但是会赋予人活力。
赋予人活力的,恰恰是彻底的否定性与分裂。世间不仅有肯定之地狱,也有否定之天堂。
在充分认识到“真实自我”到底有多无能的一个深夜,内心出现了一个清晰的念头:就算失败一百次,那些要做的事儿,会爱的人,要过的生活都是一样的。
所以失败真的无所谓。无能也无所谓。甚至成功也无所谓。有所谓的是那些要做的事儿,会爱的人,和要过的生活。


表达寻求的是反馈,批评是反馈,共鸣是反馈,不屑一顾是反馈,看不懂也是反馈。
反馈是为了迭代。
在表达之前,没有什么思想真正属于我。为了捕捉那些思想,必须很认真地采集与狩猎。
真实地认知自己已经很难,真实地表达自己还要更难。因为真实地表达,需要的不仅仅是勇气,还有难以琢磨的技巧。
就像包豪斯的设计那样,要让所有的形式追随的功能,less is more,所需要的并不是更少更简单的设计,反而是更多更深刻的设计。
所有可以被表达的真实,都被更深刻地碾碎过。而那些设计的过程性材料——所有晦涩的、不准确的表达,都是私人的思想手稿。


To iterate is human, to recurse, divine. 迭代者为人,递归者为神。(L. Peter Deutsch)
美妙的生命结构和生命体验是没有办法向外证明和向外设计的,只能向内搞自己——即最终回归到,自己对精神和肉体的统治,能多大程度上遵循自我的律令。
接踵而来的要求,则是有技巧的表达。把一种已经存在的机构和体验表达出来,为精神内部产生的新波段找到合适的时空做仓储。
体验设计是时空的异步对话,要在通道的两端分别作业,实现两个精神宇宙的相互赞美与共鸣。每次都能对上的波段几乎没有,但又不是无迹可寻。
这种特定结构和体验的表达工作,基本上就是体力活儿,或者说是一种生命力能耗的大功率工作。设计师的水准如果飘忽不定,那往往不是能力问题,而是能源问题。

持续的价值创造需要的不是别的,正是持续的生命力。


充足的时间、空间、爱的资源和钱。
生命力基础设施,要根据理想生活的生命力能耗,进行量级匹配的建造。
坊间也流传着一个土说法,叫做:要让能力大于欲望。这说法实在让人不喜欢。
能力没办法拯救人于磅礴的欲望之中,但生命力确实可以为生活创造新的游乐场。



最开始是个意外,有些过程极度美妙,更多挑战接踵而来,然后需要一些时间。
虽然从学生时代我就靠给别人做PPT赚钱,但我从来没有想象过自己会直接通过做PPT开始设计师的生涯。挺意外的。
从小到大,我对金融和金钱都有过多的执念与偏见,与现实世界的关系不好,与钱的关系也不好。具体表现为乱花钱,不理财,瞎投资。
在投资机构做设计,最大的收获应该说是“重新矫正了自己的价值转换模型”——正视不同资产本身的特性,也更理解价值交换与价值创造的模型。从一个因为官能刺激而对设计产生兴趣的票友,到关注设计本身的价值创造空间,在时代的张力里,探索伟大的结构和体验是何以被创造。
钱本身是无聊的,赚钱本身也很无聊,但学会驾驭无聊而不是被无聊以任意一种形式吞噬,是价值高效转换的训练。


一直在搞。先搞自我教育,然后努力表达这个自我教育过程中发生的生命结构与生命体验。
想要搞教育,也没什么特别原因。教育即生长,生长不需要原因。时间矢量的正向遍历过程中,对搞教育有热情是一件和热爱呼吸是一样正常的事情。
但想要搞好教育,和学会好好呼吸也是一样困难的事情。
在25岁教师节的时候,我写了一篇文章,叫做《教育对我来说是人性的塑造与实验》,里面的很多说辞到今天也同样适用。出于对未来的好奇,以及进化的欲望,大学毕业后,在教育行业摸爬滚打了4年。这4年倒是极度热血的4年,工作得很high,整个人张力十足,非常激进。
近来换了行业,倒是没有原来那么激进了,但对教育的conviction其实更多了一些。
我是一个typical接受了九年义务教育的标本。这个过程中,家庭教育没有太好,也没有太差,中学资源还可以,大学是个风景秀丽但不知道为什么总在主打旅游的场子,挺想出国念书的,但各种原因也没去成。总之就是整个被动教育的过程,说好不好,说坏不坏。
但我自己给自己安排的主动教育,那就很精彩了。能有今天的信息素养,多亏我一路折腾——从跟着王姐姐要在巴黎搞服装设计工作室(失败)到去伦敦郊外的没信号庄园搞文化培训与传播(魔幻),从做数学系的奇葩死活不念金融双学位(去了新传)到大拐弯跑去给中学生做生涯教育鸡汤一姐……数不清折腾过多少没谱的事儿,说它们是一种社会实践,我更愿意把它们当成一种自我教育。
因为我普通的起点和无能的初始设定,到今天可以非常自信地说:我的自我教育搞得很成功。
我的知识储备和阅历还不足以拍着胸脯去定义什么样的教育是好的教育。有时候我想,好的教育可能有着一百种一千种样子,但每种样子的背后都是有一个鲜活的生命结构与生命体验的。我能做的事情,就是把我体验过的、好的教育,以一种合适的方式封装起来,变成一种可被复制可被传播的结构与体验。我在努力做这件事,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做好。
这个时代的人们面临最大的精神挑战:不是关于“少”的挑战,而是关于“多”的挑战;不是关于“creation”的挑战,而是关于“curation”的挑战;不是在古典世界“解决冲突”的挑战,而是借助比特世界“完成超越”的挑战。

人类总是循环往复地发现新大陆,建造新大陆,直到新大陆再没有新的故事产生。


我现在越来越体认,自己的无能,正是自己最大的优势。无能且充满好奇心的生活,美妙到难以说。
阿甘本在The Comming Community说古尔德的钢琴艺术是至高的艺术,因为他不仅有“弹的能力”,还有“不弹的能力”。但是他选择不去使用“不弹的能力”,即who can not not-play。别的钢琴家是用“弹的能力”,古尔德是不用“不弹的能力”。
Only a power that is capable of both power and impotence, then, is the supreme power. If every power is equally the power to be and the power to not-be, the passage to action can only come about by transporting in the act its own power to not-be. This means that, even through every pianist necessarily has the potential to play an the potential to not-play, Glenn Gould is, however, the only one who can not not-play, and, directing his potentially not only to the act but to his own impotence, he plays, so to speak, with his potential to not-play.
正是否定性的存在,给了双重否定的空间,生命的张力总是因此而产生。


其实很多事情不想证明了。做到的事情没必要证明了,做不到的事情大约也都放弃了。
只剩下最后一件事想证明:所有热诚到无可救药的理想主义和英雄主义,坚持下来,会有好结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