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扫码打开虎嗅APP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界面文化(ID:BooksAndFun),作者:潘文捷,编辑:黄月、叶青,原文标题:《从东北老虎、杭州豹子到长江江豚:过度害怕和过度轻视都因我们不了解动物 | 专访》,头图来自:视觉中国
近期,有关野生动物的新闻热点频出。先是4月23日,一只野生东北虎闯入黑龙江省密山市村庄,该虎救护后被确定名称为“完达山1号”。5月7日,群众报警称在杭州富阳区发现疑似金钱豹。经调查,确定杭州野生动物世界有三只未成年金钱豹外逃。5月8日,其中两只金钱豹被寻回,一只至今仍未找到。5月9日,上海海昌海洋公园和珠海长隆海洋王国分别接收了4头和2头野生长江江豚,也引发了舆论热议。
如果说有一条线索能将这些新闻串联起来,那大概是动物的野生与圈养之别。为何杭州动物园出逃的金钱豹必须安全尽快完成搜索和捕捉,而“完达山1号”却应尽早“放虎归山”?为何野生长江江豚被迁往海洋公园引发如此之多的不满,圈养环境和野生环境对江豚而言有何不同?
在野生东北虎出没新闻被曝前期,人们普遍认为这是东北虎生存环境和东北生态环境变好的表现。与之类似,当金钱豹的踪迹在杭州最初被发现时,也有舆论认为这说明了杭州生态环境在变好。虽然后续得知豹子并非野生,但这也让我们意识到,随着生态环境的改善,的确会有越来越多野生动物出现在人类生活环境周围,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又应该如何与动物相处呢?
结合近期的一系列事件,界面文化采访了复旦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研究员王放,他的主要研究方向是野生动物种群动态、种间关系和适应性等。王放在解答了我们一系列疑问的过程中也指出,人不应该对野生动物过度害怕以及过度轻视。环境日益改善,野生动物必将更频繁地出现在我们身边。除了可以和刺猬、喜鹊、麻雀、翠鸟这些常见动物相处融洽,我们也可以与豹子、老虎等野生动物共存。王放和他的团队以及同行所做的,正是“在承认人类中心长期存在的前提之下,解决人和动物共存的挑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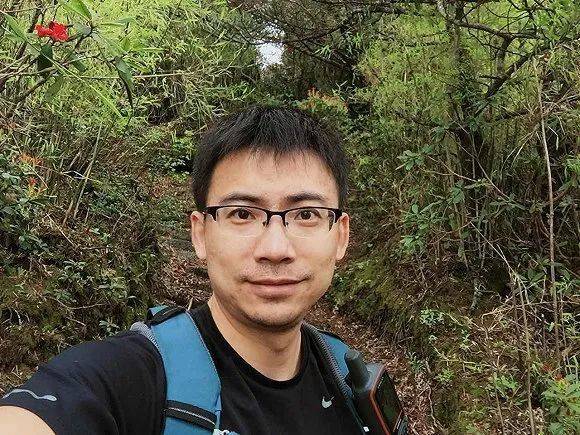
复旦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研究员王放(来源:受访者供图)
一、在帮助野生动物方面,绝大部分野生动物园做的跟城市动物园没有本质区别
界面文化:“完达山1号”东北虎出现的时候,媒体跟拍、高调直播、无人机在天上飞,一些科普文章说这些做法不可取,可能让老虎出现应激反应。是不是现在几百人追金钱豹也会让动物出现应激呢?那么比较好的应对方法是什么?
王放:杭州的豹子跟“完达山1号”这只老虎是完全不同的状态。我们国家一共只有几十只野生东北虎,其中一只自由扩散到了人类的村庄,在这种情况下,最理想的状态是它能够意识到村庄并不适合生活,意识靠近人类的地方存在威胁,或者自己撤离,或者在专业人员的帮助下安全撤离。前提是我们要避免过度的追踪干扰,避免让动物感受到不能够处理的威胁,避免它进入到应激状态。
野生动物在自然环境里生活,一般都有很丰富的经验,会不断学习怎么在人类的世界里面找到躲藏的地方,所以通常情况下知道如何处理这种和人类的错误接近。
但是杭州豹子是完全不同的状况——在人工养殖状况下,动物没有野化训练,也没有生存的经验和能力,面对人类时存在的不确定性比较高。所以杭州的豹子关注重点不是应激问题,而是安全、尽快地完成搜索和捕捉。
界面文化:豹子出逃听起来是一件有点浪漫的事情。约翰·欧文有一部小说就叫《放熊归山》,讲的是主人公怎么解放动物园里的动物,体现了一种追寻自由的精神。但在现实生活中,人是不可以直接解放动物园的。
王放:很抱歉需要打破美好的想象,放掉的话它们都会死掉,这是非常现实也非常残忍的事情。我们国家很多工作人员对大熊猫进行了那么多训练,但是在大熊猫野放的早期,在野外依然很难存活,最近几年才出现一些成功案例。
很多研究人员和自然保护工作者花了巨大的精力去做普氏野马的野放,可能很多人会觉得,一个食草动物只要有草原就能吃草,就能活下来,但这也遭遇了长期的失败,在很多失败教训中才取得了一点点成功。美洲鹤的野放一开始大家觉得是很成功的,但是最近几年发现小鹤繁殖也遇到了困难。所以说,让动物回到野外是一个漫长而且艰巨的事情。
豹子本身在野外就会遇到很多困难,从觅食到繁殖,成功活下来充满了挑战,更不用说是动物园跑出来的豹子。让我简单判断的话,这三只豹子没有任何在野外靠自己生存下来的可能。

普氏野马 图片来源:Unsplash/Tengis Galamez
界面文化:中国的动物园分为城市动物园和野生动物园两种,金钱豹是野生动物世界出来的,为什么不会更野生一点?野生动物园是不是比城市动物园能更好地保护野生动物?
王放:很遗憾,目前没有看到动物园对野生动物有非常大的帮助。我不否认动物园和野生动物园存在的必要性。但是在帮助野生动物这件事情上,动物园和野生动物园其实是五十步和百步的差别。
未来我们确实更希望看到动物园对养殖个体开展野化放归的实验,但是动物园参与野生动物的保护,是一个非常漫长又复杂的过程,比如需要在动物出生后就减低它们对人的依赖,需要对动物进行行为训练,训练它们捕食、躲避敌害、参与繁殖。真正野化放归之前,需要给动物提供学习空间,需要训练场,有一系列非常复杂的工作。
迄今为止,除了部分濒危动物的繁殖和野放中心之外,在动物园这个体系里面,我们并没有看到太多动物园能够直接帮助野生动物的案例,也许通过科普教育会有间接的帮助。
界面文化:野生动物园不是笼子比较少,空间更加开阔吗?
王放:可以明确地判断,即便野生动物园动物生活的环境更加宽敞,但是动物仍然是养殖个体、靠投喂、缺乏真正自然的行为,放到野外也基本上活不了。这和真正帮助到野生动物是天差地别的两件事情。
在帮助野生动物方面,绝大部分野生动物园做的跟城市动物园没有本质区别。但是,野生动物园的动物生活空间会大一些,会更自由更快乐一些,养殖情况之下的刻板行为会少一些,这些是有用的。在教育上也有机会做得更好,毕竟野生动物园能够更多地让游客看到接近自然的行为和状态,让人想起来这些动物是生活在野外的。
界面文化:现在很多人在批评杭州野生动物世界,说动物园前前后后有很多的问题,比如人们看到这家公司背后控股的投资公司的投资人不仅投资了杭州野生动物世界,也投资过马戏团甚至还有狩猎俱乐部,对这个动物园的印象可能就会不大好。可是我们普通人该怎么去决定这个动物园到底好不好?
王放:这是很有趣的问题。随着动物园的发展,其功能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以前大家会觉得动物园是一个给人看动物和娱乐的地方,但是今天的动物园有几个非常关键的功能,比如科研,提供动物关键的知识;比如参与保护,收入和经营应该一定程度上支持野生动物的保护,养殖的个体应该作为野化放归的来源;同时也应该有教育的作用。在今天动物园的四五个功能里,最常规也最不需要强调的是游憩休闲功能。
作为游客,其实动物园有没有很好地完成这些功能,是可以感受到的。比如动物在一个很破的笼子里边,没有装饰,没有丰容(圈养条件下,丰富野生动物生活情趣,满足动物生理心理需求,促进动物展示更多自然行为而采取的一系列措施的总称),动物在那发呆,一圈一圈走,刻板行为通俗讲就是“神经病”,是很差的动物园里动物的状态。
在好的动物园里面,我们能够看到动物在觅食、在喝水、在求偶、在玩耍,有丰富的行为。好的动物园里没有动物表演、马戏,因为这里展示的是真正动物自然的行为,而非人工控制的取乐。我们看动物的时候也真正得到了一些知识,而不只是看到被关起来的一些动物。
二、未来城市周围会出现更多野生动物,与人类共存并非那么惊险和不可接受
界面文化:你和你的团队长期对城市生物多样性进行监测,你也提到过:“比如北京,如果我们展望未来三十年、五十年,那么城市里将来出现野猪几乎是必然的。”在关于金钱豹外逃的早期新闻里,有一种观点认为杭州出现了豹子是生态环境变好的体现,后来才发现这是不对的。究竟哪些动物出现在城市附近可以证明生态改善?这个普通人怎么辨识?
王放:我觉得作为市民,很难简单判断动物出现意味着什么。因为国家一二级保护动物有700多种,再加上“三有名录”的话,受到某种程度保护的动物实际上有近2000种。
不过,也许每天都生活在身边的物种是比较好的评价指标。比如说,城市里有刺猬、喜鹊、麻雀、翠鸟这些最常见的动物,如果这些动物更频繁地出现,说明城市环境比较好。

城市里的麻雀 图片来源:Unsplash/Elena G
但除了普通的动物,还会有一些更不寻常的动物出现在人类活动区域附近。通常我们会认为,大型猫科动物对人类比较敏感,会回避人类密度比较高的地方。但是美洲狮频繁出现在美国洛杉矶、西雅图等大城市周边,印度孟买周围也存在着豹和虎。在我们国家,目前阶段大型的食肉动物很难出现在城市周围,但是随着生态恢复,豹这样的动物已经被多次发现出现在村庄周围。
生态系统的变化需要时间。伴随着之前森林的采伐、城市的扩张,伴随着道路、铁路的修建和各种人类活动的加剧,过去几十年里,很多动物都曾经处在种群减少、分布退缩的状态中。也因此,大型食肉动物近距离的出现让人感觉更加震惊。
但是近年来,像野猪、狗獾、貉、狍这些常见动物越来越近距离了。因为从1998年天然林全面禁伐之后,中国大规模的森林采伐已经成为历史,森林和其他生态系统出现了一定程度的恢复。再比如说最近20年,很多城市的急剧扩张已经放缓,进入到生态恢复的过程中,所以在未来十年、二十年的时间尺度上,我们在城市周围可能会看到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甚至有可能看到更大一些的野生动物。
界面文化:刚才说到像老虎和豹子这种动物对人类十分敏感和回避,杭州的失踪的豹子目前还没有攻击过人,它们究竟会不会攻击人?
王放:杭州的事件不能作为野生动物来解读,因为它是一个人工养殖情况之下从动物园跑出来的豹子,不具有野外生存的能力,不是杭州土生土长的动物,不熟悉这个地方的自然环境,是一个非常独特的案例,针对这种案例只能限制和抓捕它。
但是如果我们去看真正野生的豹,会发现不同的状况,它们和人的共存也并不是想象中那么惊险和不可接受。
比如,宁夏六盘山是我们的一个研究基地,是中国野生豹数量最多的区域之一。在那里,回避和共存是同时发生的,比如豹子会出现在距离村庄只有200米的地方,也会在冬天下到山谷里边、相对温暖的农田周围,距离居民点很近的地方觅食和取暖,跟人共存。但是豹子尽一切可能减少跟人的直接接触,减少冲突。
六盘山和周边区域有几十只豹子,但是在几年的时间里,仅有几个见到豹子的人,都是坐在车上跟豹子擦肩而过,惊鸿一瞥,更不会有豹子攻击人、尾随人等冲突。保持距离、避免接触、谨慎共存,我想就是目前阶段野生豹子跟人真正的关系。

生活在非洲奥卡万戈三角洲的野生豹 图片来源:Colin Watts/Unsplash
界面文化:刚才说的在美国、印度大城市周边的这些动物也是类似的情况吗?
王放:不一定,这其实充分证实了野生动物是有变化的。
美洲狮的数量相对多,分布非常广,从美国西部到中美洲到整个南美都有。可以发现的是,第一,随着动物数量的增加,动物跟人的关系会不断变化,比如美洲狮出现过攻击老年人和小孩的案例,是有可能会出现冲突的。
第二,人类可以通过改变生产生活方式,尽可能降低冲突的可能。比如说在有豹子的地方,把狗拴在家里,不让狗到处跑,减少村庄周围散放家犬对豹子的吸引,因为豹子看到到处跑的狗可能会觉得这是食物。如果进行粗放型放牧的话,豹子或虎会发现家畜是特别容易得到的食物,进而就会形成一个概念,认为村庄不是危险的地方,村庄周围到处都是食物,是可以靠近的。所以在有野生动物的地方,我们就要设计一些方案和规则,避免人对野生动物的吸引,以及由此产生的直接冲突。
第三,美国没有杀光美洲豹、美洲狮,没有把它们都抓起来赶走,印度也没有因为冲突的出现就把这些野兽视为不可接受的。实际上,这些区域都是特别好的案例,尽管在罕见的情况下会存在人和野生动物的冲突,但是我们仍然需要容忍它们的存在,当务之急是建立起来一套规范健全的机制来减缓避免冲突,在冲突发生的时候能够紧急去处理,这会是更长远的方向。
其实在东北虎这件事情上,我们的邻居俄罗斯也是这么干的。我们发生了一起人跟虎的冲突,闹出轩然大波,很多人会觉得这是不可接受的。但实际上,在跟中国接壤的俄罗斯的远东地区,它们每年处理的人跟西伯利亚虎(即东北虎)的冲突数量超过100起。有些冲突很小,就是老虎出现在村庄周围,有些冲突比较大,是虎攻击狗或者牲畜,还有一些冲突更大,就是它们对人进行攻击。针对不同的冲突,有不同的解决方案。
三、野生个体不应长期进入人工环境,让它们在野外生活下去是最重要的
界面文化:近期,和豹子从动物园跑出来相反的一条新闻是,19头长江江豚从天鹅洲保护区迁到了其他地方,比如上海海昌海洋公园接收了4头,珠海长隆海洋王国接收了4头。将野生动物从保护区送到圈养场馆,也遭到了一些批评。
王放:迄今为止,几乎没有成规模的海洋公园或者水族馆养殖的鲸豚重新回到野外的成功案例,所以这样的事件才会如此让人担忧。
这和之前“完达山1号”的例子有相似之处,整体来讲,我们会不愿意看到野生的个体长期进入到人工环境。“完达山1号”就算是需要暂时进入,也希望这个时间越短越好,因为在人工环境下待的时间越长,动物就越容易失掉在野外生存的能力,不确定因素也就越大。
界面文化:你之前也在采访中说,中国野生动物保护正在出现从保护个体物种到维护整体生态系统的转型,如果是这样的话,保护江豚等动物应该保护的是整体生态环境,是这个意思吗?
王放:对。应该保护的是河流生态系统,应该保护的是堤岸、河水,应该管理的是人的活动、航运、水的污染。我想这就是今天被频繁提到的“大长江”“大保护”概念的真实体现。因为缺乏足够的信息,我很难回答为什么这些江豚会被送到海洋公园,只能说如果这些江豚真的停留在人工环境中,那么从长期来看,这并不是一个正确的方向。
界面文化:把江豚放在海洋公园里,是不是能更好地进行教育科普?
王放:教育科普功能应该是人工养殖下、已经建立了成熟的人工种群的那些个体来做的。野生的个体,尤其是这么濒危的个体,应该尽一切可能让它们生活在野外,存在于它们的栖息地之中。每一个事情是有轻重的,残存的野生动物能够在野外生活下去,是最重要的,是压倒一切的。
界面文化:人在野外的时候可能会觉得自己是自然的干扰,在动物园里又想要尽力消除动物在圈养环境中的刻板行为,究竟怎样才能跳出二元论,建立跨物种的联结呢?
王放:哲学问题我也很难回答,只能说我们能做什么。复旦大学我的团队以及同行们在努力做几件事,第一件事是搞清楚动物到底是怎么样的。
今天之所以出现了好多让我们担忧的事情,是因为我们不了解动物,有些情况下把动物妖魔化了,或者过度害怕,或者过度轻视,不够了解它们的行为,也不足够清楚它们起到了什么生态学功能,怎么维持物种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怎么维持生态系统服务。所以第一件事情就是科研,搞清楚真正生态系统运行的规律,搞清楚动物需要什么,搞清楚动物的生活状态。
第二个是要非常努力地去做教育,去做科普,尤其要让孩子在更小的时候就理解动物需要自由地生活在它们的栖息地中,知道跟动物有关的知识,知道我们有可能跟动物、跟自然以更好的方法共存。
第三件事情也非常重要,就是立法。我们需要有更好的法律法规来管理。比如,我们建动物园,要把动物抓起来的话,要满足什么标准?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我们不能抓?这些是需要法律和法规的。
不管是过去还是现在,我们都会面临方方面面的问题,但实际上我们也在不断取得进展。比如说我们更熟悉大熊猫的生存需求了,也更了解金钱豹怎么跟村庄共存了,这些进展可以帮助保护区制定更好的野生动物管理政策。尽管这些进展常常是局部的,但对于更大的区域和其他物种也有帮助。
再比如说很多研究者都参与了《野生动物保护法》的修订。新冠疫情以来,大家很关注野生动物,所以在迅速修订《野生动物保护法》,增加了国家级保护动物,改变了一些管理方法,全面禁食野生动物,重新规定哪些动物能养。
而教育则是更漫长的工作。我们现在有一些小的教育的探索,比如说我们在上海成立了“城市里的公民科学家”项目,邀请市民跟我们一起调查城市野生动物。参与调查的市民,以及看到了照片、报道和故事的市民,会更了解野生动物就生活在我们身边,它们没有那么可怕,我们可以找到办法共存,我们也在尝试让我们的工作更多进入到校园里去。
如果越来越多的人在尝试的话,也许未来会有改变,但这不是一个团队或者一群人能够完成的,需要长期努力,也需要科普进入到科研考核指标体系中。
界面文化:那我们是不是需要有一个什么要改变的整体的理念,比如说人类中心主义这样的想法?
王放:很遗憾,短期内,甚至相当长的时间内,我不觉得人类中心主义会改变。除非出现重大生态灾难,或者地球环境以我们想象不到的速率急剧恶化。
我觉得要面对现实。在一个理想的世界,人和动物能共存,我们尊重并且努力跟各种生物共享资源。但是在一个现实的世界里,我觉得从业者需要意识到人类中心会长期存在,并且长期都是世界的主流。所以我们做的工作需要在承认人类中心长期存在的前提之下,解决人和动物共存的挑战,这是我自己的心态。
野生动物的问题不仅仅是人类中心论这么简单,也不能简单把类似思路指责为错误的。比如说把野生动物当作资源,当做药材,当作农副产品,这在很多文化、很多人群里都存在,我们只有充分意识到大家对自然对野生动物的不同态度,才有可能更好地制定法律法规,更好地进行保护。尊重生物多样性,也尊重人的多样性,这是我们必须要做的功课。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界面文化(ID:BooksAndFun),作者:潘文捷,编辑:黄月、叶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