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扫码打开虎嗅APP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硬核读书会 (ID:hardcorereadingclub),作者:刘苏里、赵世瑜、孙歌、宋念申,编辑:谭山山,题图来源:视觉中国(乌克兰切尔诺贝利,一辆汽车被遗弃在开满花的树下)
2023年12月30日,在万圣书园新店,举行了“巨浪中的个体:历史写作中的‘小人物关怀’”主题分享会。
这是广东人民出版社旗下的“万有引力”出版品牌、新周刊与万圣书园联手举办的沙希利·浦洛基作品分享会的第二场。分享会由万圣书园主理人刘苏里主持,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孙歌、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博雅特聘教授赵世瑜、清华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所教授宋念申担任嘉宾。
“我对个人的思想、情感和行为非常感兴趣,但最重要的是发现和理解形成这些思想、情感和行为的政治、社会、文化环境,以及个人应对环境的方式。在我的书中,那些做决定的人、‘塑造’历史的人不一定身居高位,他们可能是,而且往往只是碰巧出现在那个时间、那个地点,反映的是时代的光亮和悲歌。”
浦洛基教授如此阐述自己的历史观。在他关于人类命运的宏大叙事中,总有那么一些重要的时刻,留给了那些无法留名史书的普通人。
时代的一朵小浪花,足以成为淹没你我的滔天巨浪。幸运的是,有些人,在为我们记录。
本文即摘自该分享会的对谈记录。
一、时代的巨浪与不确定的个体
刘苏里 :这个题目起得非常好。巨浪中的个体,讲的是个体在历史大势当中的命运。“命运”,拆开看,是“命”和“运”。命没办法,爹妈把我们生下来,没办法改造,没办法复制;运就很玄妙,跟今天我们谈的历史节奏有很大的关系。孙老师虽然是研究思想史的,但是对个体在历史中的命运,相信有长期的观察。
孙歌 :2011年9月底,我去了京都,得以近距离观察“3·11”核灾难之后日本社会是如何摆脱创伤的。小人物对于大灾难的感受,可能离我们每个人都很近。这给我提供了一个宝贵的机会。做思想史的人都会重视本雅明的著名命题,即历史只有在危机饱和的那个时刻,才会突然展示它真实的面貌。
作为只能存活几十年的个体,我们都希望一生无病无灾;但是作为思想史学者,我们必须意识到灾难不仅是灾难,也是一次近距离进入历史的机会。怎样抓住这样的机会来观察看上去很正常的那种生活方式当中的反常部分,这是我给自己确立的一个思想课题。
核能作为战争武器被发明,即便后来被“和平利用”,仍然携带了巨大的风险——不仅仅是技术上的风险,还包含了政治的、意识形态的、经济的,甚至是人的各个层面的因素。《原子与灰烬》把核实验和核电站的事故放在一起讨论,这是很有意思的排列方式:前者是战争,后者是和平利用,但是作者告诉我们两者有千丝万缕的内在关联。
刘苏里 :浦洛基的《切尔诺贝利》,讲到切尔诺贝利核灾难当中的小人物。赵老师是研究历史人类学的,也叫社会史或微观史。你是怎么进到这个领域的?
赵世瑜 :我不懂核能,但是核能的利用或者一系列悲剧性事件,就发生在我们身边,特别是在全球化的进程中,不管相隔千里还是万里,我们都会马上有直接的感触。
核危机给每一个人,尤其是受到灾难损害的人的心灵和肉体带来不可磨灭的创伤。这种创伤会带来沉重的记忆。西方国家的历史研究中有一个主题,专门研究创伤记忆。20世纪90年代初我就在美国接触过这方面的研究,最开始它集中在二战后幸存的犹太人的苦难记忆。我们老说“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创伤记忆就是“后事之师”当中很重要的一点,但是我们做得很少,值得反思。
刘苏里 :宋念申老师是我定义的“中生代学者”,我们来听听就这个主题他想说什么。
宋念申 :浦洛基的写作方式让我感觉特别熟悉。他写的不是传统的历史研究作品,而更像是新闻写作。《原子与灰烬》中,那艘日本渔船在比基尼核爆之前,船长一心想的就是,“我的网坏了,要多捞点鱼,再多走一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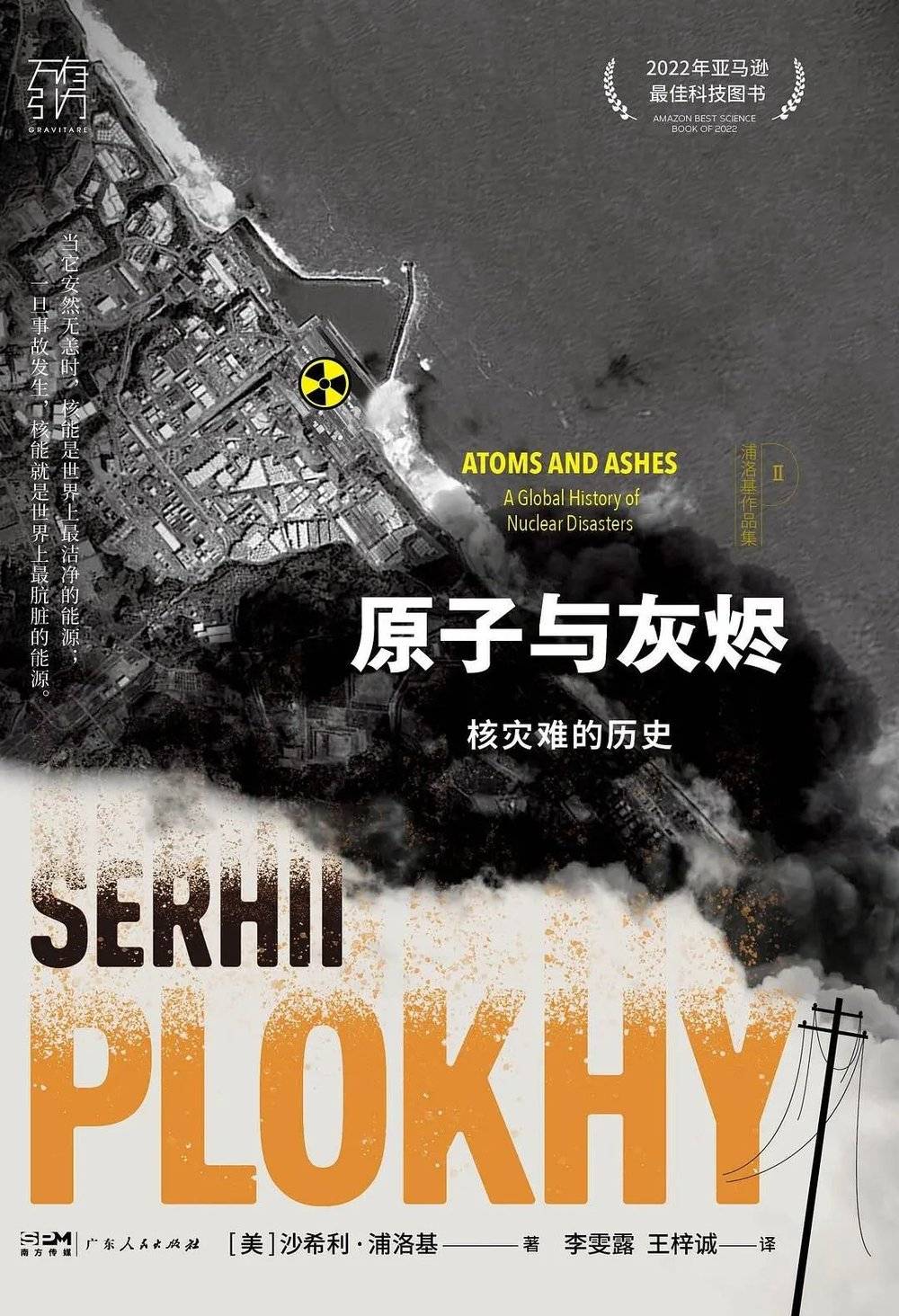
《原子与灰烬》(2023年10月版)封面。
2001年9月8日,我第一次踏上美国的土地,完全不知道三天后会发生什么。“9·11”当天,我去看了冒烟的五角大楼,然后开始做街头采访。我不知道后面会发生什么,我只知道我在经历一件事情,这就是一个普通人正常的反应——在真正发生历史转折时的那种不确定性。
于是,我去学历史。只有在历史里,才能体会那种经验性的感觉给你带来的东西。历史写作和新闻写作,我认为是很接近的,都是站在已经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的基础上去揣测事件发生前的结构是什么样子的。对于一个人文学者来讲,把握不住的那种命运感比确定性更有魅力。
二、在历史写作中寻找普通人
刘苏里 :浦洛基跟史景迁还不太一样。史景迁写小人物,就是写他们的故事;浦洛基是写一个大的主题,把小人物放在其中展现他们的命运。
赵世瑜 :他这三部书和一般意义上的、学术化的历史著作不同,它们非常像新闻采写或者纪实文学,不是典型的历史学家的作品。我相信这样一种叙述方法一定是作者有意而为的,他希望让更大范围的群体——尤其是那些觉得这件事情离我们很遥远,跟我们没太大关系的人,知道事情的严重性及其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巨大伤害。
找一些根本没有文献资料的人群做研究,背后的理念是:在叙事可控的范围内,尽可能不让那些在历史中扮演过重要角色或者经历过重要事件的人,被历史忘记。浦洛基的三部书中,除了提及戈尔巴乔夫、肯尼迪、赫鲁晓夫等重要人物,也提到了很多亲历者,消防队员、逃难的人等,这在新闻采写或纪实文学中常见,而在学术著作中是少见的。
今天我们的观念、价值观发生了很多变化,我们关注重大事件、重大危机当中的那些个体,也包括日常生活当中的个体。我们每个人都会遇到生老病死,这对个体来讲都是危机。这些危机难道不该关注吗?这是每个人都要面对的。
在重大危机中的体验和日常危机体验可能有很大差别。朱令去世,在座的年轻人没有经历过那个时代,我的好朋友谈起这个事情的时候会有完全不同的感受,无奈、无力,愤懑又没办法。这不是大事件,但今天有那么多人在讨论这件事,说明我们进步了。我希望这类事情能进入历史学者的视野。

沙希利·浦洛基作品。(图/万有引力 提供)
孙歌 :中国的历史学传统,一向是有面孔的、有人的。但近代以后学西方,历史学开始社会科学化、非人格化。今天,在主流的历史叙述里可以看到事件、找到知识点,但是你没有办法找到历史的不确定性里若干在场之人的感觉。
这三部书的强项就在于,它写的是最严重的时代危机,但同时它有面孔——既有大人物的面孔,也有小人物的面孔。
我们在看历史、看同时代各种危机时有两个视角。一个是国家视角,那是传媒、教养给我们的,也是我们用逻辑不断复制、不断再生产的视角。另一个是生活人的视角——作为小人物,人们面对的是生老病死这些具体的生存问题,这个时候核战争、核污染是离他们很远的,要活下去,该怎么办?
浦洛基的作品中有一个细节,我在日本也强烈感受过——在危机来临的时候,面对危机的人并不知道它来了。这是一个极重要的提示,它有点像今天我们面对AI时的感觉:带着一点兴奋,觉得与己无关,又觉得有点危险。
第二个细节,科学家在面对核这样一个无法完全掌控的能量的时候,是用三七开的逻辑来对待的。比如现场负责人在核危机来临时,认为小剂量的辐射可以忽略。小剂量的辐射会置人于死地,但这些在国家视角里是忽略不计的。
三、回到人的主题
孙歌 :今天所有人都认为核能源是安全的,核电站只要建在海边就安全。日本有个反核科学家叫小出裕章,到2011年为止,他任职于京都大学核物理研究所,但他一直反核。他说核电站是“不修厕所的高级公寓”,没有办法处理核废料。
2011年之前,还没有人知道存在这样的问题。但小人物有小人物的智慧,比如福岛、福井这些有核电站的地区的姑娘,很难跟东京的男孩结婚,家长不同意。老百姓不傻,他们只是不说而已。小出借2011年的核危机,把它说出来了。
小出后来说,60岁以上的人,吃点带核辐射的东西问题也不大,因为辐射损害身体需要一个积累过程。他还提出了一个很不讨巧的建议,建议商店里建一个60岁以上老年人专柜,专门放那些被污染的食材。
刘苏里 :周其仁说过,每个人都想喝新鲜牛奶,要原汁原味、好喝,还能保存一定时间,这件事以传统的方式根本不可能完成,然而大家又对添加剂有意见。所以这到底是厂家、消费者还是社会的问题呢?
孙歌 :小出是个诚实的科学家。科学思维的特征,即设定一个目标,之后向它不断推进。但人文思维要照顾到人这样一种多面、复杂的,有内在矛盾的生命综合体,这跟科学思维是有矛盾的。小出的行为体现了科学思维的典型缺陷。
当我们把科学意识形态化,强调必须用科学思维来主导一切时,其实面临着巨大的风险,因为这意味着人退居到边缘。透过核危机及它牵引出的无数个相互矛盾的个案,我们获得另一个契机。
近代以来,科学被神圣化、绝对化、意识形态化之后,我们忽略掉了更为重要的——看上去拖泥带水且不那么光鲜的——和我们每个人的生命息息相关的另外一些要素,而这就是赵世瑜等学者在田野里打捞的、小人物生命中核心的东西。当然,我并不是在挑战科学,而是挑战科学意识形态的绝对化。
宋念申 :历史写作要关注小人物,个体的视角非常重要,在主流历史学界,这一点不需要再讨论。近两年来,这种写作方式并不少见。以前主要在近现代史领域,因为材料够,有底层人物留下来的日记、口述材料;像赵世瑜老师他们那样,从乡村的碑刻、家谱里也能找出很多材料。作为一种方法,现在甚至可追溯到中古史乃至上古史。
历史写作要尊重叙事的完整性。关注底层的话语,对国家话语而言是有效的补充。二者是一种非常微妙的共存关系,是相互构建的。
从《切尔诺贝利》到《原子与灰烬》,浦洛基的关注点更复杂、更宏观。核危机已经不仅仅是一个国家问题,而是全球性的问题,延伸到孙歌老师所说的人类的现代生存问题。对小人物的书写,它的目的在于揭示历史里更微妙、更复杂的层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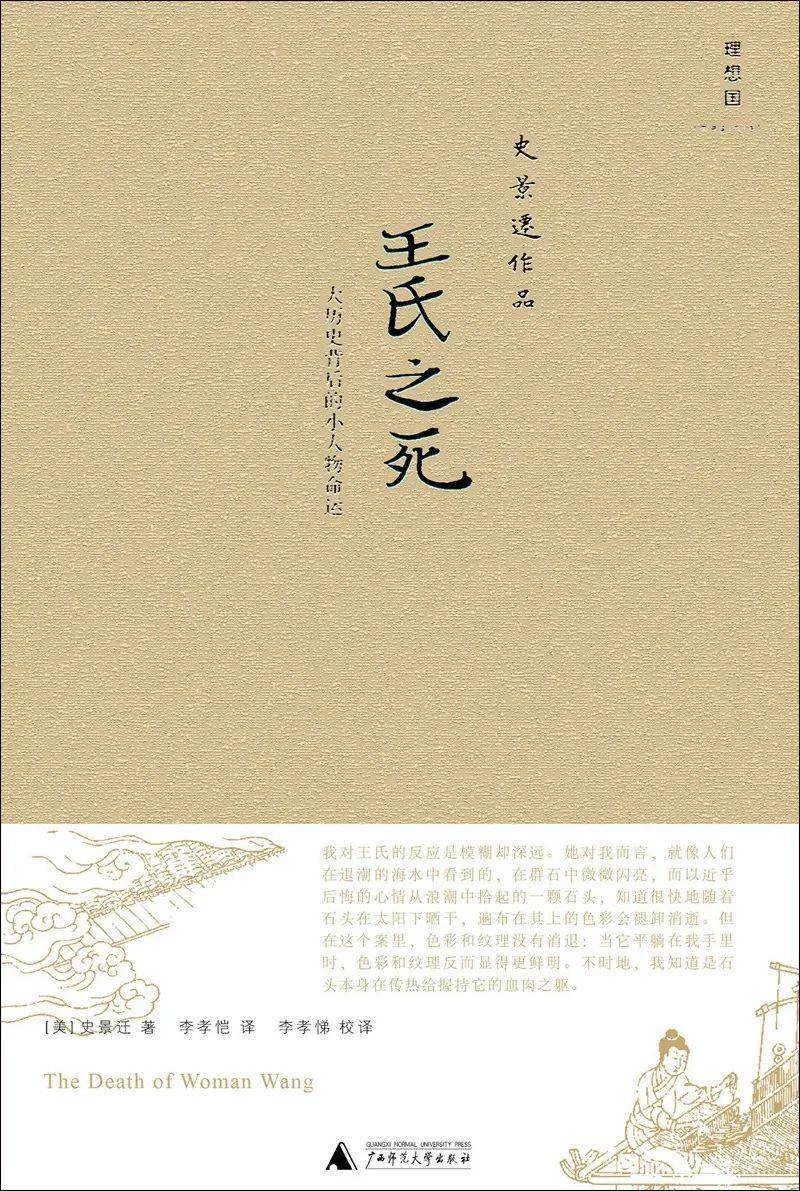
《王氏之死》(2011年9月版)封面。
赵世瑜 :对于小人物关怀或者“巨浪中的个体”,国际史学主流并没有太多分歧。但在中国学术界还是有挺大的不同,我自己就经历了很多同行嘴上不说,但内心不以为意,或者觉得我标新立异。
而在2023年,我看到了变化。央视一套播出的一部考古纪录片,在证明秦简史料价值的时候选择了两个故事:一个是鲁西奇教授写过的《喜》的故事,另一个是秦简里一封小人物的家书。这在过去是不可想象的。
《儿童的世纪》作者、法国学者菲利浦·阿利埃斯曾说,经济史能使人了解小人物、默默无闻的群众是怎样生活的。在法国学者布罗代尔的《地中海与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世界》中,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具体的东西——巴黎街巷或者威尼斯市场的生活场景;一家人在厨房里一起吃饭。布罗代尔通过这些东西来讲食品价格等经济学概念。
从学术上讲,如何回到人的主题,依然任重道远。就读者来讲,当他们无法共情,并把自己的经历代入历史作品时,也就很难理解作者所描述的那些事物。
刘苏里 :很多事情是这样的,一定是文学家走在前面,准文学家走在中间,然后才是学者。近两年比较有名的,像《张医生与王医生》《东北游记》等,就是准文学家作品。学者吕途就“中国新工人”主题写了几部书,说明我们的学者已经意识到这件事情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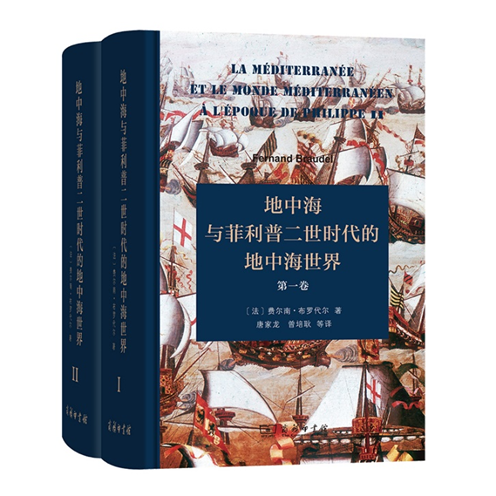
《地中海与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世界》(2017年1月版)封面。
四、小人物如何对抗时代的巨浪
现场提问 :赵老师提到“集体创伤记忆”,我们缺乏集体创伤记忆,也缺少相关教育。如果我意识到自己是巨浪中的渺小个体,想努力记住巨浪下的时代记忆,应该怎么办?
赵世瑜 :孙歌老师提到的日本科学家小出裕章,像他这样的人很多。他一开始唱反调的时候,并没有想到后来会引起这么大的反响。我们都可以做这样的事情,虽然不见得有他那样的专业知识。
浦洛基给了我们一个提示。为什么他的书里能写这些东西?因为他可以获得的资料变得丰富了。过去为什么资料少?除了技术手段、修史者的史观问题,或者是孙歌老师讲到的科学意识形态化问题,还有很多复杂的原因。
如今,通过各种渠道和手段,小人物能够发声的机会比过去增加了不知道多少倍。我们可以做的事情,不仅仅是记录我们的一点一滴,也要记录父辈的一点一滴。
比如,可以给父辈甚至爷爷奶奶辈录音,或者让他们自己写;很多家里留下的老东西,不要随便当垃圾废品扔了。举个简单的例子,我们经历了近半个世纪的人民公社时期,每一个人民公社的办公机构门口都挂了牌子,某某人民公社、革命委员会、党委等。后来国家文物局想搜集这种牌子,发现全中国只剩一个了——而在过去,全国可能有数以十万计这种牌子。可想而知,我们平常会不经意地损失多少记忆。
我们需要多留点心,多带些主动意识,去留下这样的东西,记住这样的历史。未来因此可能会不一样——不仅仅是每个个体会不一样,甚至我们国家都会不一样。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硬核读书会 (ID:hardcorereadingclub),作者:万有引力,编辑:谭山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