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扫码打开虎嗅APP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硬核读书会(ID:hardcorereadingclub),嘉宾:黄灯(作家、教授,任教于深圳职业技术学院)、程猛(博士,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讲师),主持:郝汉(硬核读书会编辑)、董牧孜(期刊编辑、自由撰稿人),内容监制:萧奉,节目编辑:郝汉,协同策划:钟毅,头图来自:《Hello!树先生》
近日,张锡峰在《超级演说家》的激烈言辞——“我就是一只来自乡下的‘土猪’,也要立志,去拱了城里的白菜”,引起热议。似乎每逢高考季,人们总是热衷谈论那些出身贫寒、通过教育获得上升机遇的农家子弟们。
在励志的正面表述中,这些阶层旅行者经常被称作“寒门贵子”。在负面社会新闻里,他们有时会被贴上“凤凰男”等标签。
在人们口中,他们被当作“教育改变命运”的坚实论据,而农村的家庭出身又仿佛是某种“原罪”,神秘地解释了他们在城市生活中的种种不适应。
一些关于农家子弟的负面报道往往会让人形成这样的印象:他们与城市文化的摩擦,在社会交往中的问题,都是由于没有摆脱自己的出身。他们想在大城市立足,就必须违逆自己的家庭,只有抛弃乡土积习,才能涅槃重生。
对此,北京师范大学博士程猛在“一席”的演讲里,借助自己的博士论文《读书的料及其文化生产》,提出了不同理解。他认为,农村生活和家庭经验对于农家子弟取得高学业成就至关重要,农家子弟的向上流动也不是一个简单地“走出农村、改变命运”的故事。
与此同时,他指出,农家子弟跨越城乡边界的向上流动,伴随着内心的情感震荡,也有道德和文化秩序的重塑。
同样农家子弟出身的作家黄灯,曾在《大地上的亲人》序言里这样写道:“作为整个家族唯一获得高学历的人,我的成长,隐喻了一种远离乡村的路径。”而她的一切写作的起点正是对自己“远离乡村”状态的不安与反思。
本期节目,我们邀请到了程猛和黄灯,聊聊70后、80后农家子弟的不同高考经验。作为高校教师,他们对农家子弟在中国社会的浮沉又有什么观察?农家子弟的向上流动之路,就是对自己出身的背叛吗?
以下是内容节选。
“当年高考不考数学,对我来说特别亏”、农家子弟面临“大考”的情形就像“等末班车”
董牧孜:黄老师在《大地上的亲人》里说自己是“整个家族唯一获得高学历的人”。程老师在《“读书的料”及其文化生产》里提到自己一到大考就超常发挥。高考对很多人来说是既痛苦又解脱的时候,是十几年来决定命运的节点。两位老师可以回忆一下自己高考时的心态与印象深刻的事情吗?跟今天相比有什么不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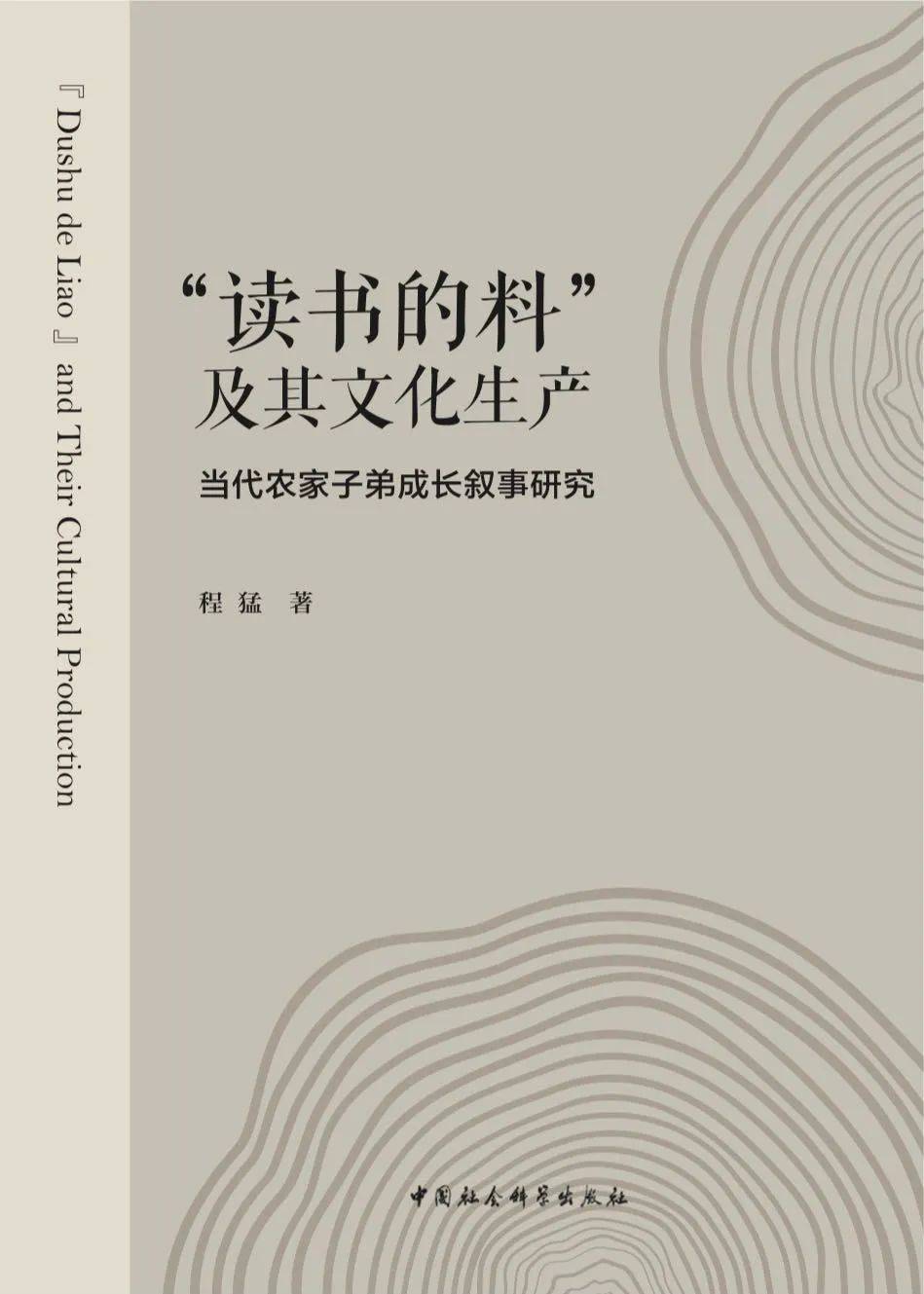
《读书的料”及其文化生产》,程猛 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1-4
程猛:高考的时候,印象最深的就是我非常紧张和焦虑。因为自己在高一的时候成绩不太好,一度去网吧打游戏来逃避这种压力。到了文科班之后,不再考物理了,自己也慢慢转变学习状态,成绩有些提高,但一直都不算班里学得最好的。
高考时特别担心自己到底能考上一个什么样的学校,如果考得不好该怎么办。当时我妈妈特意陪我住在市里姑姑家。高考前一天晚上9点多钟,我就上床准备睡觉了,但是一直睡不着。到凌晨三四点,可能才眯了一会儿。第二天早上,在路上我又肚子疼,我妈妈就很担心。但真正到了考场之后,好像一下就不紧张了。
作为农家子弟,能够考上大学,成为走出来的“读书的料”,真的太偶然了。许多人真的因为这样那样的原因,一次考试被埋没了。命运有时真是有点捉弄人。
我是高考意外地超常发挥,数学最后一道大题在最后几分钟解出来了,数学分数因此多了接近10分。这些经历让我觉得自己好像真的是有“考运”,可能把学习之外的运气都用光了。
郝汉:黄老师能不能讲一下您的经历?您是哪一年高考的?
黄灯:我高考都是上个世纪了,在1992年。其实我为什么会动念头写《我的二本学生》呢?就是因为我在教学生的过程中,发现他们的心态和精神状态跟我们当年读大学时的差别特别大。所以说,现在要我回忆高考,我真的没啥印象。
我印象深刻的就是那年开始改革,以前高考分文理科,但从我们那一届开始,湖南、海南、云南的高考分成4类——文史、地矿、理工、农医。文史不考数学,农医不考语文。但我属于数学成绩好的那一类文科生。所以对我来说非常亏。我这个人最大的毛病就是记忆力特别差,什么东西都记不住。150分满分,我记得政治我只得到了73分,历史可能才90多分,那时候我早知道高考我考不好的,所以,我从来觉得我能上一个大专也是达到极限了。
当年考大学只有三个层次,一个是本科,一个是专科,还有一个是中专,但是它们的分数差别不是很大,专科和本科分数线相差4分,然后中专可能就比专科要低十几分,我的两个姐姐都是读的中专,当年中专、大专和本科生在国家人事制度里面都属于干部身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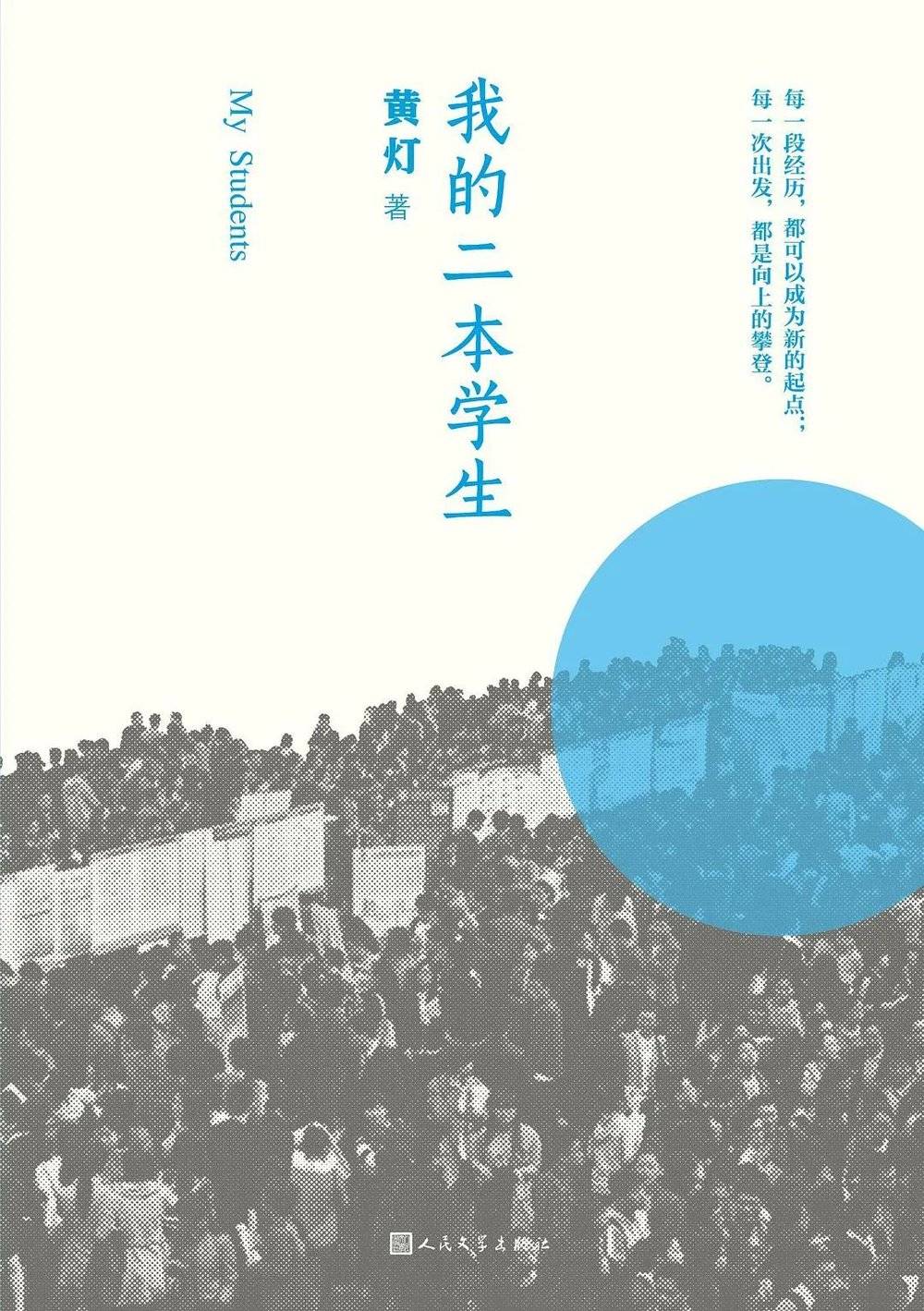
《我的二本学生》,黄灯 著,人民文学出版社,2020-8
董牧孜:那黄老师印象比较深刻的是不是考硕士?我记得你中间好像去车间工厂工作了一段时间。
黄灯:我考硕士的状况其实和程猛高考有点像,就是运气特别好。我1997年下到车间,1998年年初工厂接不到单彻底下岗以后,就决定考研,复习了7个月。当年是1999年,我记得那个时候还没有网络,信息也不通,专业书都没有买齐,但自己就开始复习,就属于这种情况,但也不像现在的孩子考研要考一次、两次,要那么拼命,好像也不是这个状况。
我就是把那些重要的专业书非常认真地读了看了一下、慢慢地理解,然后用最快的速度复习政治,英语是从基础开始学的,因为1998年6月,我回校参加四级考试都没过,但最后考研的时候也考了将近60分。

电影《钢的琴》,反映了上世纪末的下岗潮。
郝汉:我想到程猛在《“读书的料“及其文化生产》里的一个比喻,他把那些改革开放后出生的农家子弟面对“大考”的情形,比喻成“等末班车”,如果上不了车可能就一直留在原地了。但从黄老师的际遇而言,70后比较幸运的部分好像在于,总是有好几班公交车,哪怕你去了工厂做工、遭遇下岗,也可以重新拥有教育上的选择。
黄灯:对,我觉得这就是当年教育资源公平的地方,没有固化得那么厉害。而且我感触最深的一点是,就算我的原始学历是一个大专,但在我考研究生的时候也没有遭到任何歧视。我考武大的时候,从报考到面试,我的本科文凭是自考的文凭,但没有任何人多问你一句,也没有人去问你的第一学历是什么。只要你合格,就得到跟武大的本科毕业生一模一样的对待。
那些高考失利的“读书的料”
郝汉: 黄老师刚才提到的其实正是由于两位作为观察者的不同,你们观察到了不一样的群体。黄灯老师的新书是关于二本学生,一个被广泛忽视的存在,他们是没有考上名牌大学的普通年轻人。而程老师一路都在重点院校读书乃至任教。我蛮好奇您会怎么看待那些高考失利的“读书的料”?
程猛:我觉得自己是非常幸运的。如果说我最后那道题没做出来,其实很容易滑档。当时报志愿的时候也非常傻,完全不知道自己的高考成绩到底在什么位置,所以好像都是报了一些师范大学。当时我对师范大学也有误解,以为录取分数低,生活补贴会高。所以,别的大学,像黄老师之前就读的中山大学,或者厦门大学、武汉大学,还有其他来我们高中做招生宣传的一些场合,我根本都不敢报名,也不敢去。我觉得我肯定考不上这些大学。
我觉得不管是就读于二本院校的同学,还是别的院校的同学,如果是出身于农村或城市里的普通家庭,真的都经历了许多辛苦。至于为什么会最终考到不同的学校,这个影响因素太多了。除了个人因素,学校、家庭和社会都在影响。命运之神随意拨动了一下,就有可能读二本或读一本,这个跟外部的许多因素有关。

改革开放后恢复高考。
尤其对于我们80后、90后来说,家庭可能给予的支持和乡村的教育资源是非常关键的。为什么我10岁就离开家去读初中了呢?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当时乡镇中学的教学质量和区县中学的教学质量差距在持续扩大。
那时我爷爷在乡里的中学教书。他知道乡里的中学优秀老师、生源流失严重,能够考到市里重点高中的学生越来越少,于是就跟我爸妈说让我去考区里的学校。就这样一个偶然的机会,我考到了区里的中学,才有了后面考上市里重点高中的可能。
“读书的料”字面意义是说一个人有读书的天赋,但每个人都是某种“料”。人的天赋和潜力是多元的,有的人可能比较适合读书写作,有的人适合画画、音乐,有的人适合沟通协作……不同的人最有天赋的地方是不一样的,这些能够考上大学的人大概都有些学习方面的天赋。那些家境贫寒的孩子,家庭能给予他们的具体支持太少了。个人天赋强烈地依赖外部支持,依赖社会的公平正义。
“到广州读博士以后,我家里人跟我说,不要接触那些打工、偷东西的亲人”
董牧孜:黄老师在书里写道:“十几年前的博士头衔,还有足够的含金量让任何一个底层青年摆脱卑微。”程猛老师在书里提到,有被访的同学说看不出来你是农家子弟,这让你感觉心情复杂。
大学教师可以说是具有文化资本、受到社会尊重的职业。但两位老师似乎都有在书里表达过这种对于自己日渐精英化而远离乡土亲人之后的焦虑感和道德负担。知识包裹、理论堆积的学院生活中,会有怎样的不安感?学位给你们带来了哪些改变?对乡村生活的感情和理解有了哪些转变?
黄灯:如果说博士学位、文凭给我带来了什么,我觉得还是让我获得了相对的自由,给了我做自己喜欢做的事的机会。但正是因为进入一种学院生活以后,我个人的生活跟我以前的生活差距太远了。尤其是那种学院生活因为它是相对封闭的一个圈子,让我觉得我跟真实生活一直有隔膜。
在《大地上的亲人》序言里面,我就写到过一个事情,我到广州读博士以后,家里人跟我说,不要太多地接触家里那些在广州打工的,尤其那些吸毒、偷东西的亲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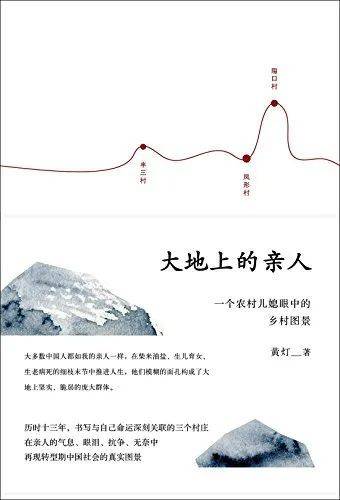
《大地上的亲人:一个农村儿媳眼中的乡村图景》,黄灯 著,理想国 | 台海出版社,2017-3
然后有一次,我的一个堂弟来看我的时候,就唤醒了我的那种记忆,在他们的心目中,我还是他的姐姐,他在情感上面还是在牵挂我的。
从这个事情以后,我就一直在反省自己,我读了学位以后,按照生活给我的路径,我是应该越来越远离他们吗?但自己和亲人之间到底应该建立一种什么样的文化关系?随着时间的流逝,我跟他们之间的距离越来越远了,我是不是要心安理得地接受这种疏离感?
后来,我发现这样对我来说确实会有道德上的负担,我觉得这样是不对的。如果我获得的学问越来越高,就意味着我要越来越远离乡村的话,那这样的成长路径对我的家庭来说,到底有什么样的意义呢?我有时候会这样去问自己。
所谓的焦虑感和道德负担,主要来自亲人之间的那种具体的生活境遇差距,差太远了。客观地说,虽然我在城里过得也不像他们想象的那么好,但不管怎么样,我有一份稳定的工作,有个地方住着,能够从事自己喜欢的工作,有机会去获得别的信息。而家乡的许多人,他们基本上就只能够为自己的生存去奋斗、去拼搏,甚至去到城里面讨生活、去流浪。

《摇摇晃晃的人间》剧照。
从这个角度来说的话,我那篇文章《一个农村儿媳眼中的乡村图景》也是在这样的反省状态下写出来的,是对自己过去生活的一种回望。如果我不读出来的话,可能就跟他们一样,但读了书,拿了学位以后,可能事实上又在远离他们,这确实是一个巨大的矛盾。
程猛:这个问题特别拷问我们的内心。刚才黄老师提到的道德负担感以及不断去审视自己和家乡亲人之间的关系,我也有同感。包括我的整个研究,某种意义上就像我在后记里所写的,它是我在那个时候必须去反省和面对自我的迫切需要,是一种自我疗愈。
在求学和成长的过程中,我感受很深的,是和自己最亲的人,也就是和我妈妈的关系的变化。小学时候,我总是坐在妈妈自行车的大杠上去上学,是非常亲近的。后来10岁那一年,为了求学,我就去区里的学校住宿了,和家庭以及家人的关联突然被打断了。
我记得布尔迪厄在《实践与反思:反思社会学导引》中引用过福楼拜的一句话——“长到10岁还对寄宿学校是怎么回事儿懵懵懂懂的人,对外面的社会只会一无所知”。在这样一个离开乡村、离开家,到一个陌生的世界寄宿的过程中,好像慢慢地就有一些疏离的感觉,不自觉地“报喜不报忧”。由此导致我在青春期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不知道该怎么跟家人相处。我妈妈也跟我说过好几次,觉得我怎么就跟她不亲近了。

《实践与反思:反思社会学导引》,[法] 布尔迪厄 / [美] 华康德 著,李猛 / 李康 译,商务印书馆,2015-12
直到我读研、工作、读博、再工作,随着自己慢慢地长大,包括生活里发生的意想不到的事情,关系又有了变化,可以更自在地和家人分享自己的生活。一个标志性的差别是现在会和他们开玩笑。以前确实就是嘘寒问暖——吃了什么呀、天气冷多穿衣、多喝水这些比较多一些。每次打电话都是很快就结束的。现在和家里人打电话时间变长了,聊的话题也比以前多一些,一些困扰也会跟他们说了。
至于和家乡的伙伴还有一些亲戚家的兄弟姐妹的关系,确实生活环境不一样,共同话题就没那么多。一些哥哥姐姐初中、高中毕业就去闯荡,而我一直在读书。读了这么多年,他们可能会觉得:哎呀,这个读书读的,也没有房,没有车。确实,在人际关系的处理上自己还是挺呆的,经常还是比较像一个书呆子。
在回馈家庭和愧疚感方面,我觉得有个过程。以前有段时间,回馈家庭的心理特别重,特别想多挣点钱什么的,但自己又一直在读书,做的这些事情显然又不能挣多少钱,甚至大多数时候就是挣不到什么钱。从大学时就开始做家教和各种兼职,赚生活费。读研、读博时,能把自己的学费、生活费都搞定就已经很好了。
硕士毕业之后,去当了两年中学老师,工作还算适应,但是觉得在北京生活压力很大,不知道自己该往哪里去,没有方向。后来的话,觉得自己可能也不需要有那么大的负疚感。有时候自己也会鼓励自己一下,虽然说没办法回馈父母太多,这么多年也没有给家里带来什么大的改变,但是至少在努力做自己想要做的事情,没走上什么歪路,已经挺好的了。
农家子弟的向上流动之路,就是对自己出身的背叛吗?
郝汉:刚才两位动人地讲述了许多自己的体验和心路历程这些经验性的东西,接着我们谈谈比较硬核的部分。程猛在《“读书的料“及其文化生产》里面提出了一个比较有创见的理论——“底层文化资本”。
我们往往会认为法国社会学家布尔迪厄所发明的“文化资本”概念是由社会中上层人士所占据并在自己的阶层内继承的,而底层向上流动往往要对中产阶级文化的模仿以获取“文化资本”。你能谈谈你所说的“底层文化资本”吗?
程猛:“底层文化资本”是这本书在理论上希望贡献的一个闪亮的点。我们刚谈到法国社会学家迪迪埃·埃里蓬的《回归故里》,就像作者一样,我们每个人都需要直面自己的过去,直面自己的出身,直面自己的家庭与家人。刚才黄老师也特别提到了这种“断裂感”,甚至“愧疚感”,好像我们变得越来越远离自己的过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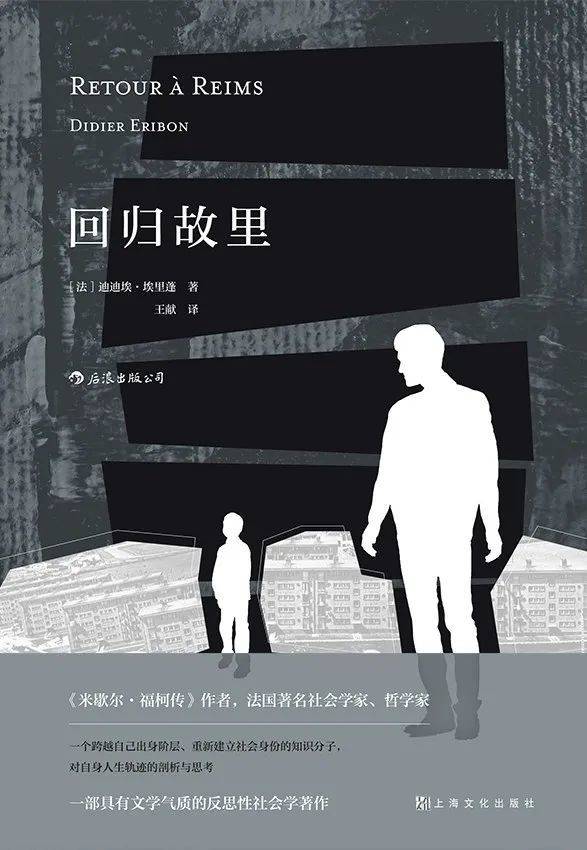
《回归故里》,[法]迪迪埃·埃里蓬 著,王献 译,上海文化出版社,2020-7
但在这个过程中,究竟该如何理解和处理这种“断裂感”?出身农村、通过教育向上流动的旅程,是不是意味着就是要脱离乡土,要远离他们的家庭,要成为和他们父辈完全不一样的人?农家子弟的向上流动之路就是对自己出身的一种违逆和背叛吗?
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他们原有的生活经验将变得意义阙如,是完全要弃之不顾的。如同《位置》的作者法国小说家埃尔诺所说,“他用脚踏车把我从家里载到学校去。无论晴,无论雨,从这一岸到另一岸的摆渡人。说不定那个他最觉得骄傲的事,或者说他存在的正当性,是这个:我属于鄙夷他的那个世界”。我在想,难道农家子弟取得高学业成就就是被另一个文化世界完全浸染甚至同化的一个过程吗?

电影《咖啡公社》剧照。
事实上,正是这些理解铸造了底层子弟的自我枷锁。完全抹掉过去,是一件残酷的事情。正如美国哲学家桑塔耶那(George Santayana)所说的那样,“谁忘记过去,谁就注定要再一次承受这一过去”。
“底层文化资本”在某种意义上不只是试图揭示底层子弟取得高学业成就的内在机制,也是试图和上面这些现实中的困扰对话。
中国情境下农家子弟所拥有的文化资本和城市中上阶层子弟是不一样的。不同阶层“文化资本”间的差别并非如法国社会学家布尔迪厄所设想的,是一种“多和少”的差别。如果能进行多和少的比较,那么所理解的“文化资本”就是同质的。
但我认为,“文化资本”不是均质化的存在。从这个意义上讲,农家子弟之所以能够取得高学业成就,不是一个弥补他们所没有的文化资本或者说文化同化的过程,而是基于他们独特的家庭生活和学校生活实践所创造出的“底层文化资本”。
在家庭生活与学校生活经验的碰撞中,他们生产出了这种动荡不安、具有强大能量却又异常脆弱的“底层文化资本”。组构底层文化资本的先赋性动力、道德化思维、学校化的心性品质,都与他们的过去息息相关。这种文化资本只有在文化生产中方能呈现自身,它依赖强有力的公共支持体系和公平正义的社会环境。

电视剧《平凡的世界》剧照。
这样,我们才能够理解农家子弟成长的特殊性究竟在哪里,他们的成长能量和局限又在哪里。我们需要看见这些农家子弟生命体验的复杂性,不能只是标签化甚至妖魔化地讨论他们。关于“读书的料”的研究以及关于“底层文化资本”的言说,是想要农家子弟重新看见自己所经历的一切所可能具有的意义。让过去变得有意义,我们才能真正拥有未来。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硬核读书会(ID:hardcorereadingclub),嘉宾:黄灯、程猛,主持:郝汉、董牧孜,内容监制:萧奉,节目编辑:郝汉,协同策划:钟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