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扫码打开虎嗅APP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界面文化 (ID:BooksAndFun),作者:徐鲁青,编辑:黄月、叶青,原文标题:《豆瓣小组里的crush与劝分:讨伐“恋爱脑”,做没感情的搞钱人?》,题图来自:《花束般的恋爱》剧照
豆瓣上一则“和电影院认识的陌生人接吻了”的帖子在上个月传播甚广,帖子讲述了楼主在电影院认识后座男生,两人看完电影散步回家,接吻后选择不留微信互相告别的故事。这则转发过千的帖子来自豆瓣小组“我今天遇到了一个crush”,crush指“短暂热烈的心动”,以女性为主的组员在这里记录自己经历的crush时刻——现实里仅有三秒,情绪的余波却可以持续绵延。
和“crush小组”沉醉于心动瞬间与浪漫幻想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热度不相上下的“豆瓣劝分小组”,成员也大都是女性,这里的主流态度是:感情都是“虚”的,搞钱搞事业才是“实”的。“没有感情,才能在男女关系里立于不败之地”等类似发言被大量点赞,对浪漫爱有所期待、对分手不够斩钉截铁的人被批评为愚蠢的“恋爱脑”,“骂醒恋爱脑”是该小组的永恒主题。

(图片来源:豆瓣)
“Crush小组”与“豆瓣劝分小组”几乎在同一时期迅速增长,受到大量关注,许多用户同时是两个组的组员,并“在上头和下头之间反复横跳”。这两个对爱情态度全然相异的小组提供了一条缝隙,让我们得以一窥当下女性面对浪漫爱的复杂感受:一边是热衷crush的上头瞬间,快乐嗑起“即时糖”;一边是视感情为男性圈套,哀叹“恋爱脑”的自甘堕落。
同时我们也看到,在女性联合起来形成新的感情叙事时,内部的割裂与冲突也随之产生:“恋爱脑”被指控为自甘堕落,沉溺感情被视为软弱无能。如果浪漫爱是父权制的糖衣毒药,那么当女性撕碎浪漫小说、挣脱既有爱情话语的镣铐、走向理解中的反面时,她能够看到怎样的“新”图景?做独立自主的经济理性人就是一副理想的解毒良方了吗?
嗑糖上头与劝分下头:面对残酷现实的殊途同归
Crush的瞬间有很多,可能是做核酸检测时的一个对视、地铁上男生手机里的一首歌,或人群拥挤时无意间牵错了的手。小组成员们为crush对象在聊天时多打出的一个语气词扰动、烦恼,浮想联翩,也在阅读他人crush经历时共情相似的心潮涌动。
“Crush小组”的高热度似乎体现了女性对浪漫爱的渴望与期盼,然而兴趣又往往只停留在心动一瞬的浪漫,许多人觉得后续拉扯的恋爱故事破坏美感,还有很高的“下头”风险。小组中点击量最多的,大都也是当事人互相错过、不再有任何后续发展的故事,惋惜之外也有不少“不必后悔”的声音,因为“靠近总是会失望”。
“电影院亲吻陌生人”的故事符合“相遇-分别”的模式,楼主最终拒绝了男生要微信的请求,“因为我觉得如果继续下去,大家也知道无非就那么几种结果。不会再有比今晚更美好的体验了,就停在这也很好。”许多人对楼主的选择表达了赞赏和佩服,比如“我觉得不加微信的你好励志清醒,你们的见面已经是这场crush的高潮”。
进一步分析,为何拒绝进一步联系会被看作“励志”呢?或许这显示出楼主没有被心动瞬间冲昏头脑,掉进恋爱的陷阱——毕竟按照小组主流观点来看,在crush的故事高潮之后,恋爱、结婚与“三胎”是不难想见的一路下坡、一地鸡毛。

crush小组受欢迎的“be美学”(bad ending),指遗憾分开的结局,与happy ending相对
(图片来源:豆瓣)
在“豆瓣劝分小组”的帖子中,这种一地鸡毛的具体现实便体现得淋漓尽致。在澎湃新闻《豆瓣劝分小组:当代青年的“结婚冷静站”》一文统计的劝分小组分手原因里,“身材羞辱”“处女情结”“嫖娼家暴”等并不少见,还有许多女性在婚后面对着婆家催生、丧偶式育儿与职场困局等等。
与性别议题相关的社会新闻也会出现在劝分小组的帖子中,不管是霍尊与吴亦凡事件,还是冠姓权与妇女拐卖问题,小组中都会有女性成员表示,在这些讨论中男友和自己态度相差过大,担忧自己可能成为下一个“受害者”。
与“劝分小组”这一现状相呼应的是,“crush小组”里曾出现过这样的建议:过于上头的组员可以去浏览一下以直男用户为主的虎扑,会发现许多男性用户对女性的关注几乎只集中在外貌、身材等物化强烈的特征上,有“立马下头”之功效。
“劝分小组”对浪漫爱的不屑与“crush小组”对心动一瞬的极度迷恋看似相反,却一致强调爱情之短暂,这或许是面对制度性保护缺位、性别平等观念缺失这一残酷现实的殊途同归。当女性开始认为进入一段亲密关系不一定有幸福,而是更有可能遭受伤害与风险时,她们更愿意一边嗑着“即时糖”,用二手心动满足情感需求,一边翻阅“劝分小组”的下头经历,预防自己掉入感情陷阱。
女性联盟与内部割裂:解构男性话术,讨伐“恋爱脑”
两个情感小组并非只是简单的感情经历交流会,其中也形成了女性联盟式的互相支持。评论区常出现对亲密关系中被打压、陷入过度自我怀疑的女性的鼓励,以及对因暗恋对象过度纠结者的支持。劝分组内有固定的“已分”栏目,专门发布前任作为,既不是以可怜受害者口吻痛陈不幸,也并不为寻求帮助,而是讲个故事“让姐妹们乐呵乐呵”,用自身经验警醒他人。这样的叙事打破了被伤害者总是深陷悲伤的刻板印象,同时也让其他组员意识到,受到伤害的人无需掩藏和自责,应该羞耻的是做错事的人。
劝分小组还会通过集体狂欢式的质疑、讽刺与嘲笑,用极具女性主体性的话语颠覆男性打压话术,为自身赋权。比如曾有帖文记录男友在情人节只送了0.25元红包,当女友质疑互赠礼物是否应价值对等时,男友回复“我一直以为你不是那种物质的人”。“我一直以为你不是那种物质的人”在评论区被反复引用,有人配上“哈哈哈哈哈哈哈”的嘲笑,有人制成了表情包,男性的打压话语被集体反向凝视,其逻辑的不堪一击立刻显现。

男生情人节的礼物是一张花坛的照片,劝分组认为没有送上门不够周到,于是自制了表情包
(图片来源:豆瓣)
然而女性联盟并非一片祥和,其内部也展现出割裂和矛盾的一面。纵使两个小组有许多重合用户,但“劝分小组”时不时会出现针对“crush小组”的轻视发言,称其是“恋爱脑集中地”,组员都陷在爱情幻想里。“恋爱脑”被“劝分小组”认为是第一大绝症,渴望浪漫关系或者投入感情难以自拔的女性被看作陷入了父权制设下的圈套,软弱愚蠢。小组的最热精华帖总结了历史上“那些让我后悔看到的回复”,收录的大多是因感情问题上组寻求建议,却因“舍不得”“感情太深”“心软了”等理由没有听劝分手的例子,评论区一片谩骂声,攻击她们是没骨气的“娇妻”“懒虫”等。
以独立女性之姿攻击“恋爱脑”,制造了一种新的“受害者有罪论”,许多言论直指受到伤害的女性是自讨苦吃,有成员概括了在感情中不幸却不愿分手的女生心理,评价其“自己价值低廉且贪图别人的价值,又懒又蠢”。“活该”“锁死三胎”等攻击性评论不时出现,在一段关系里的付出与爱成为了女性软弱与愚蠢的佐证。
此外,将“恋爱脑”同“理智”对立,认为女性更容易被爱冲昏头脑,控制不了自己的理智,而男性总是十分清醒、专心事业,这样的本质主义判断也制造了类似“疯女人”的厌女话语。这些针对个体的攻讦让更关键的问题隐蔽了起来——是什么让“爱”这种人类基本情感需求对女性而言如此高风险?是什么剥夺了女性拥有爱情的权利,使对于爱的正当渴望遭到污名?
尾声:独立自主的经济理性人是女性的出路吗?
诚然,从十九世纪的浪漫小说,到如今文化工业制造的大批电影与偶像剧,几百年来浪漫爱叙事并没有多少进步,一代代女性都包裹在被父权制影响的爱情话语中,轻易将浪漫爱看得过重,在恋人身上付出过多,阻碍自身潜能的发展,所谓的“恋爱脑”最早抨击的也是关系中过度奉献、不计牺牲的倾向。
在今天的“劝分小组”里,经常出现的“恋爱脑解毒”建议包括:以自我感受为中心,“做事只考虑自己,不在乎对方的感受,想做就做”;工具化对方,“把男人当工具,而不是爱上他”;不要投入感情,“男人其实也不太需要女人的爱情,只是需要女人理解、支持、好看,能睡就行了,女人挑男人也可以参考这个角度,注重男人的实用性而不是爱情”……这种种心态在一定程度上既是厌女大环境中的以牙还牙,也是女性在结构性不公中的自我保护。
然而,当对过度付出的批判滑向对一切爱情渴望的讨伐,新的“政治正确”成为“莫得感情”、“爱自己”与“会搞钱”,沉溺爱情的人被认为是可耻的,哲学家韩炳哲对爱欲之情的描述——“我不再维护自己的地位,而是在他者中、为他者失去了自我”——更是该杀。在播客《海马星球》“科学地消解恋爱脑”一集中,嘉宾运用了许多经济学理论来为“恋爱脑”解毒,包括模块化管理、博弈论、边际效益递减等。
“模块化管理”是指将自己的需求拆成不同的小需求,并通过寻找最适合的对象进行需求搭配,达到最高效益。这套管理学方法理性、高效,完美贴合效益最大化逻辑,但似乎又生产出了新的规训:独立女性应该足够理智,不依赖他人,“搞钱搞事业”能力强大,做一个优秀的经济理性人。当我们把资本逻辑延伸到人与人的关系中,视每个人为工具与资源,利益考量成为一切行事指南,女性是否在撕碎浪漫小说后,又陷入了同属男权思维的资本逻辑之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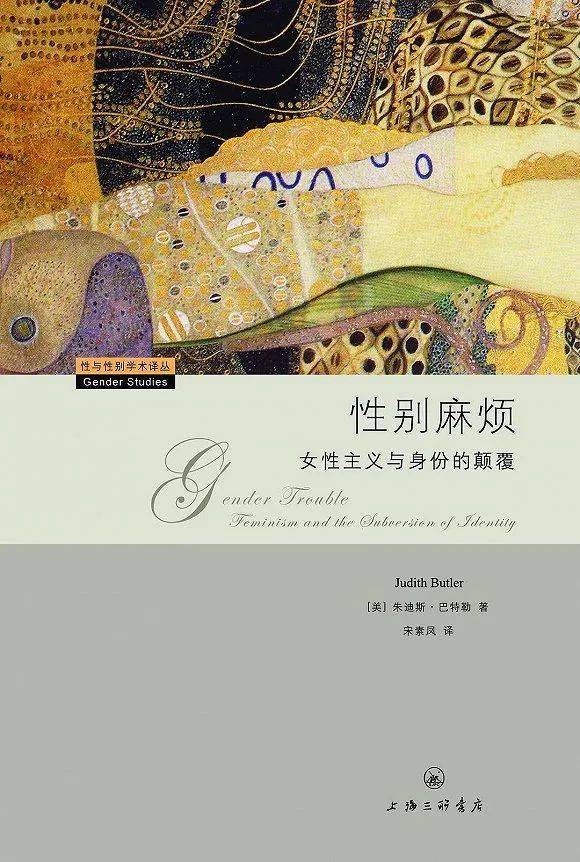
《性别麻烦:女性主义与身份的颠覆》
朱迪斯·巴特勒 著 宋素凤 译
上海三联书店 2009-01
女性主义学者朱迪斯·巴特勒曾指出,资本逻辑给予的自由样貌是父权的、是男人形态的(man-craft),连经济理性人都是男人的形象(rational economic man),它限制了我们想象一种全新面貌的自由与平等。
上世纪80年代美国新自由主义兴盛,在独立自主成为新道德风尚之时,也曾出现过“恋爱脑”被病理化的现象。美国成瘾问题专家迈雅·萨拉维茨的《我们为什么上瘾?》是一本心理学著作,她在书中描述道,那时人们将“爱得太多”视为一种心理缺陷:
“所有的感情都不过都是形形色色的成瘾,大多数爱情都是以自我为中心的妄想。爱得太多被指责为病态,依赖他人成为原罪。人应该结束一切带有痴迷特征的爱情,将共同依赖扼杀在摇篮中。”
那时的美国人是这样描述爱情的——“所有病症里最严重的一种”,让一个人极度敏感,心绪不宁,以致打扰正常的工作生活。与这一说法形成有趣对照的,是当下“crush小组”的一篇帖文,发帖人感恩暗恋者为自己带来足足一个月的悸动,虽然这没有效益回报,更满足不了模块化需求,但“crush提醒了我们,我们的感受可以这样鲜明、真挚和强烈,我们的生活不是一片贫瘠枯朽的荒原,而是有茂密森林、磅礴瀑布的连绵山脉”。
我们畅想一种女性主义式的自由与平等,那或许不是依循既有的霸权结构,在市场逻辑里实现游刃有余的理性人独立,而是在一个可以托住脆弱与柔软的社会,人们不惧同爱人互相依赖,不惧拥抱充沛的情感与激情,被绩效社会视作无用的脆弱、敏感与动荡能够得到容纳,在那时,女性或许才真正把浪漫爱从男性手里夺来,创造出属于我们自己的话语。
参考文献:
《我们为什么上瘾?》理想国·海南出版社 迈雅·萨拉维茨(Maia Szalavitz)著作 丁将 译 2021年
Precarious Life:The Power of Mourning and Violence. Judith Butler. Verso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界面文化 (ID:BooksAndFun),作者:徐鲁青,编辑:黄月、叶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