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扫码打开虎嗅APP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简单心理(ID:janelee1231),作者:江湖边,原标题《性侵案中的“完美受害人”:你怎么不笑呢,你怎么哭了呢?》,题图来自IC photo
最近引爆舆论的“高管性侵案”,想必大家都听说了。
《南风窗》以报案者“李星星”(化名)的视角,讲述了她从14岁起遭受鲍毓明性侵、囚禁,被逼观看“恋童癖”视频,多次报案未果,之后自杀未遂的遭遇。

文章写道,在一封写给李星星的保证书里,鲍称呼她为“我现在的女儿,和未来的妻子”。“李星星掉进了一个只有鲍某明的世界”。
但随后,《财新》一篇以鲍毓明为主要信源的报道引发轩然大波。焦点在于,其将性侵案描述为“这更像是自小缺爱的女孩向养父寻求安全感的故事”。鲍对外喊冤:我与李星星是恋爱关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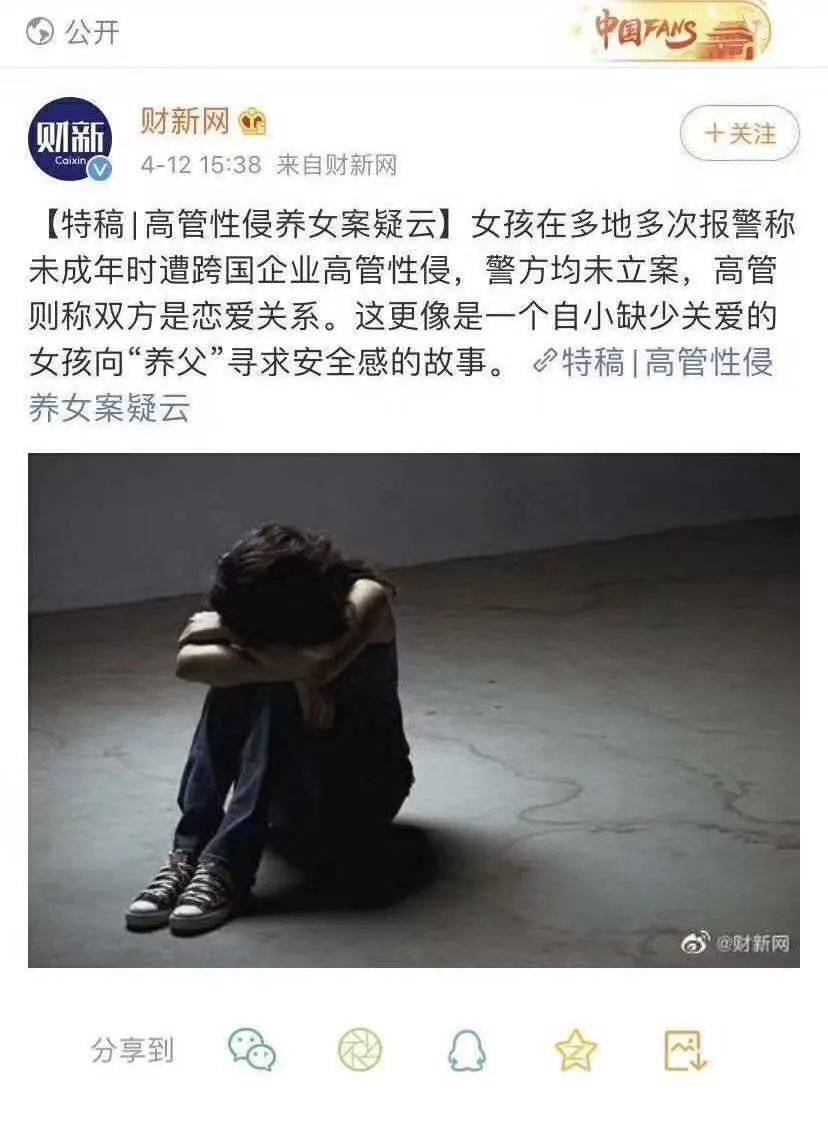
熟悉吗?
嫌疑人在用一些并不能撼动犯罪事实本身的信息,模糊案件焦点,削弱受害者的可信度,制造“受害者有罪论”。
不少网友看了这篇报道后说,“气到发抖”,甚至引发了自己原有的心理创伤。
曾经有过相似经历的人,接力写下了自己年幼时被性侵/性骚扰的感受。微博上有关#trigger warning的热搜已经挂了一整天。几百条留言都在说:
“小时候妈妈找的新叔叔,会趁晚上妈妈不在进我房间动手动脚,一开始不懂,有和妈妈侧面说过几次,妈妈只是说叔叔喜欢我。”
“我7岁左右时曾经被我17岁的表哥多次性侵过……你们知道我明白过来以后是怎么做的吗?我去故意“亲近”表哥了,还一度对表哥产生了奇特的依恋,伴随一些异常行为,比如故意去和他身体接触、甚至当着大人的面钻他的被窝。”
“对,我也假装自己爱上过TA。我不敢跟别人说,反正也没有人帮我”
性侵就是性侵,说出花儿来也是犯罪。这不是14岁少女恋上“糖爹”,这是房思琪和李国华!
那些在说“等待反转”的人,都着了“完美受害人”论调的道。
有关“完美受害者”的论调无处不在,它们与犯罪事实一样具备“舆论破坏性”
1999年,作家Alice Sebold出版性侵回忆录《他们说,我是幸运的》(Lucky)。她在大学校园里遭遇陌生人强奸,最终打赢了官司。Alice 说,这归功于她被警察认为是“完美受害者”:年轻的白人大学生、穿着保守、在路上被陌生人袭击、处女。

《Lucky》已经出版了20多年,但有关“完美受害者神话”(“perfect victim” myth)的论调却依然没有破灭。
直到现在(如韦恩斯坦案),法庭上有关施暴者的辩护总会集中于“受害者并不清白”。
1. 指责TA们的穿着
这种指责认为,遭受强暴是由于被害人自己不检点,衣着举止像是个荡妇(Slut),被强暴是自取其辱,受害者自己也有责任。
国际平权历史上著名的“荡妇游行(SlutWalk)”运动,最初就是针对一名加拿大警官的荡妇羞辱言论而掀起的。
2011年,这名警官在一个公开演讲中说:“女性要避免性侵,就不应穿的像荡妇般暴露。”(women should avoid dressing like sluts in order not to be victimized.)

2011年6月4日,芝加哥“荡妇游行”。人们穿着迷你裙、丝袜、低胸衣、比基尼,手持抗议标语,呼吁社会认知的改变——不管女性穿着如何,被谴责的应该是强暴者。
2. 为了让受害者有罪,TA们的性史也常常被提及
“完美受害者”的论调常常希望TA没有性经验,年纪轻轻,是个处男/女。
如果一个上了年纪的“强奸幸存者”收了钱,那就是“仙人跳”。在这样的预设下,强奸者作为罪犯,甚至可以引发舆论的同情——如果这个报案的人是个性工作者,那么根本别指望得到什么救助,你有原罪。
首个被送上#Metoo运动审判台的性侵犯Bill Cosby,就曾在法庭上为自己辩护说:
她(模特Janice Dickinson)几乎和地球上的每个男人都睡过觉——言下之意:别给自己立贞洁牌坊,你才不是妇女运动的道德灯塔。
3. 过分关注受害者在犯罪期间和犯罪后的行为
除非TA全力以赴地与罪犯搏斗,否则TA就是“享受这段关系”;
如果TA在报案前拖延了、犹豫了,甚至在创伤发生后仍然与肇事者保持联系,那么TA一定是个骗子,或道德上有瑕疵的人。
我们回到“鲍视角”报道中呈现的“倾向性事实”:
受害者的陈述出现瑕疵(比如第一次性侵时主张自己未满14岁);
她家里穷,母亲有残疾,在路边做小吃摊,暗示她们存在很大可能获得了“交换的利益”;
“帮助她的志愿者证实,她在报案之后仍然与鲍来往密切。”
“她那个报的都是假案。按她说的,我第一次强暴她是2015年12月31号是吧?那么惨,能过了六个月,她才报案?”
……
李星星被说成一个人格和心理上存在矛盾、习惯说谎的人,甚至是财富和阶级上的“既得利益者”。

“你怎么不哭呢,你好像不够悲伤”
为什么说一篇看似在“给另一方说话机会”的报道,是不合伦理的?——是“故事呈现方式本身的恶”。
这些所谓的“事实呈现”,就是强奸者的辩护律师会在法庭上做的——目的是为了削弱受害者的“可信度”(即便写作者并无主观意图)。
一名未成年者被操纵是容易的。在权力地位显著不对等的情况下,“只有爱上对方,她才能为性侵找到合理性”。而且,性侵事件本身也会对受害者的人格造成影响。
当故事的叙述者陷入刻板印象的描述时,都会模糊“犯罪”这个焦点事实,引发社会对幸存者“可信度”的疏远和怀疑,让他们更难获得支持,甚至更难相信自己。
这些“要求受害者完美无瑕”的态度,不仅无视了性暴力的事实,还无视了受害者在反抗、报警时需要经历的重重阻碍。
在日本、澳大利亚和全世界,犯罪者的指控被驳回或降级,可能仅仅是因为受害者“哭得不够伤心”,企图以此淡化强暴造成的创伤。
伊藤诗织曾在采访中说起,自己在警局讲述被强暴的经历时,警察问她:“你怎么不哭呢,你好像不够悲伤”:

如果在一桩强奸案中,男性才是受害者——那么警方会问,你为什么不反抗(明明身体力量占优势),而忽视他可能出现的“冻僵(freeze)”反应。研究显示,70%的性侵受害者会经历“僵直的假死状态”,也就是说,因为害怕而无法动弹。
人们还希望受害者明确拒绝和反抗——然而,大多数性犯罪都是熟人作案,且往往发生在家中。肇事者通常是朋友、亲戚或伴侣——受害者难以立刻作出伤害他们的决定。

如果你还记得“重庆巫山童养媳事件”的主角之一马泮艳,她也在微博上为李星星事件发声:“想起了那些暗无天日的过去,又忍不住哭了一场”。
她还曾在微博上说,“王X安(媒体记者)和当年卖我的马正松罗元道没有什么区别”。
遭受过创伤的人,为什么就不能快乐和成功?——“刻板印象”的另一种恶
性侵受害者Erin Zaranec曾讲述了自己受害“之后”的生活:
大多数主流媒体和社会都无法应对我的日常现实。
人们勾画出了一个“理想的被害人”。如果你不扮演这个角色,你就要付出代价。
我因为快乐而受到质疑;我因为谈了恋爱而被审问;我因为不允许那30分钟(指代强暴经历)支配余生而被审问。
遭受了创伤,需要帮助,产生了心理阴影,甚至会有PTSD,或是让TA难以再次走进亲密关系……都是可能的后果。
但是,受害者并不一定要“苦”一辈子。
完美受害者没有模版。TA可以活下来,过得很好,有梦想的“自我实现”,组建家庭,和创伤一起活下去——TA需要帮助,但并不需要这个社会“永久的、循环往复的”同情。
伊藤诗织说,自己所有的报道照片,都是一副饱受伤害的严肃脸——因为人们认为她应该永远是这个表情——但她也有快乐的时候,有时候,她也是开心的。

“我不能总是作为受害者去想发生的一切。这就是我想打破的,关于受害者应该如何表现的刻板印象。”
社会希望受害者们保持沉默。当她把自己的故事写成书时,立刻有人质疑她这么做的动机,做道德上的抹黑:“她想利用受害者的身份出名,然后从中获利”。
帮助TA们,但不要同情。不要让“对受害者的想象”造成二次强奸。
因为,性骚扰和性侵犯的幸存者,从来都不是完美的典范——TA们是人,很多人都曾经做过冒犯他人的事、不道德的事,甚至犯过罪。
在现实中,没有一个故事这么简单,无数的问题都起源于“完美受害者”的论调——
除非我们接受这一事实,并消除我们对幸存者和犯罪者行为方式的“先入为主”式的描画。否则,房思琪、李星星的故事,永远不会结束。
每隔一阵子,总会有绑架强暴案幸存者的自传译本出版……惊奇的是,她们脱逃之后总有一番大义,死地后生,柏油开花,鲤跃龙门。一个人被监禁虐待了几年,即使出来过活,从此身份也不会是便利商店的常客、粉红色爱好者、女儿、妈妈,而永远是幸存者。
——《房思琪的初恋乐园》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简单心理(ID:janelee1231),作者:江湖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