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扫码打开虎嗅APP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理想国imaginast(ID:lixiangguo2013),源自播客Naive咖啡馆,嘉宾:严飞(社会学者、清华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主持:郝汉(利兹大学社会学硕士),题图来自:视觉中国
近年来,“社会学”这几个字眼高频次地出现在我们视野中,“内卷”“去魅”“中产”等社会学名词也随之普及,甚至成为日常词汇。相比十年前,社会学似乎逐渐成为大众眼里的一门“显学”,而这丝毫不妨碍大家依旧搞不清楚什么是社会学。如今,在不断更迭的热点面前,许多自媒体对各路社会学理论进行着不加节制地引用并佐以快餐式的分析,这让人对社会学感到眼花缭乱,也让人生出许多困惑与质疑:如果什么都能和社会学扯上关系,那到底什么是社会学?社会学是一门真正的学问吗?
本期Naive咖啡馆邀请到了任教于清华大学社会学系的学者严飞,结合他与社会学深刻交织的个人生命历程,和我们聊了聊关于社会学的种种。我们怎样通过社会学来体察秩序之必要,理解人性之幽微,从而更坦然地面对我们身处的现代世界,更清醒地认识作为现代人的我们自己?
一、学社会学的人会不会天天想一些奇妙的事情?
郝汉:我们知道西方有很多电视剧、电影里,社会学已经成为大家都知道的学科,在中国也慢慢的被大家广为所知。西方开始有一些调侃,或者那些误解都被戏剧化呈现出来,出现在他们的文学、小说里面。中国目前没有这样的情况,但是大家还是会对社会学有一些误解和一些想象的状态在,我想问一下严飞老师,您从一个学生到一个老师,到渐渐成为一个社会学家,在长久的个人身份和社会学交织的过程中,有没有遭遇到什么误解或者自我调侃的部分,就是大家以为一个学社会学的人会不会天天想一些什么奇妙的事情?
严飞:还真的有误解,我记得我才上大学的时候,大家都不了解社会学,对社会学的一个基本认识,它就是研究社会的一门学问。社会太复杂了,我们怎么样可以通过一门学问就把社会了解或者研究得非常通透,会不会社会学什么都研究,但是什么东西都研究得不通透。到了大二、大三的时候慢慢根据学习的深度,把社会学等同于社会调查,又把社会调查等同于市场调查,最后把社会学学生毕业以后可以从事什么样的工作,等同于社会学的学生毕业以后只可以去做社会调查。所以在大学的时候大家对社会学还是挺失望的,这是第一个误解。
第二个误解是我最近才慢慢体会到,特别是在这本书《穿透:像社会学家一样思考》之后,我突然发现,因为书出来之后不同媒体都会来进行访谈,访谈的过程当中不同的媒体他们都不约而同提出很多很多社会现象,说严老师能不能对这样的社会现象提供一些解释的维度或者你对这些社会现象是怎么看的。这就产生了一种误解,觉得我们学习社会学就等同于我们对于社会非常了解、非常穿透,任何的社会现象都可以发表我们非常有专业水平的或者是专业深度的解答。但事实上我不知道,有些现象我都不知道,或者有些事件我都没有听说过,我觉得这就产生第二层误解,学了社会学就等同于我们可以回答任何的社会现象,变成了一个评论家。但实际上不是这样。
二、在中国,“官僚制”不等同于“科层制”
郝汉:之前我听严飞老师的一个节目,严飞老师讲到,有时候一些西方社会学理论,其实它嫁接到中国经验的时候,它可以让学生更好的理解这个理论表达的意思。但有时候它跟中国的实际情况又会有一些出入,这个部分是不是也是严飞老师在分享的时候、给学生们讲课的时候,会让他们尤其注意的?因为有时候,如果直接套用西方社会学理论去解读中国社会,实际上会造成某种误读,有没有一些具体的您在教学中的事例,可以给我们举一举。
严飞:有。比如韦伯对于社会的理性化,他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定义,就是我们对于科层制的定义。科层制是一个非人性化的、一套非常精密的科层体制,让人们在科层制当中按照文牍主义,按照精细化的分工,来有效的、高效率的进行投入和工作。
翻译到国内,科层制会被译成官僚体系或者是官僚制,在很多层面上,学生读到官僚制,他会把中国情境意义说的官僚制和韦伯的科层制划上等号,同时把中国情境的官僚制代入到韦伯的分析体系当中,但这两者是完全不相同的。
我们对中国的官僚体系印象就是:这些体制人员基本上不干活,不停地贪污,不停地寻租,不停地颐指气使,小小的官僚觉得自己掌有特权就可以不为大家服务的心态,而是不断使坏,不断让大家增加很多怨气等等。这是我们大家对官僚制一个天然印象。但是韦伯的科层制反而是朝向官僚制的对立面,在科层制下,因为分工的不同,所有人都在非常勤勉工作,不会出现这样一个寻租的主意,而且也不会出现颐指气使的状态,因为人人都是非常理性的在科层的每一个位置上,在高效的完成一体化的工作。所以在这里面,因为翻译的不同会产生很多误读。
三、“打工人”最需要心灵鸡汤
郝汉:现代世界不过两三百年,对现代社会的种种机制,在不同的社会学家那里都找到一些解释,那种解释我去看它的时候会觉得它是陌生的,我感到陌生,我才会感到我是清醒的。现代社会这件事情本身变成一个很显然的事实,但从前我们都忽视它,我们反而没有意识到现代社会这件事情。我们没有意识到,才会被卷入其中,随波逐流的去做选择、去过生活,我想跟您讨论这样一个问题。
严飞:我自己有一个体会,所谓的现代世界、现代生活,这样的词好大,到底什么是Modernity,到底什么是现代。还有一些人提出前现代、后现代(Postmodernity)、后后现代(Post Postmodernity)。所以我觉得“现代”这个词特别宏大,对于宏大的词我就特别害怕。我反而把这样的现代性通过一些我们现实当中的案例进行展现。
我举两个场景,一个场景是早高峰的北京西二旗地铁站,浩浩荡荡全是人,特别是很多住在天通苑的一些工程师、程序员,他们早上挤在西二旗地铁站,排队进入西二旗地铁站。他们不断地在外面绕弯进入地铁站,很多时候你是麻木地往前行走,甚至很多时候你不是在往前行走,你是被后面的人推着往前走。这样一种生活状态,麻木的、被后面的人推着,就好像在一个社会的、世界的浪潮之下,你是无力的,你是被后面的人推着往前走的生活状态。
还有一个场景就是,每天晚上十点、十一点,北京的国贸桥下很多人排队等待一辆开往通州的公交车,这辆车要开很长的时间才可以回到通州,他们基本上会花两个小时时间在路上,单程的通勤,每天就要四到五个小时。所以很多住在通州、燕郊的城市白领,有些还不是白领,他只是城市的打工,他们早上五点半就要去挤公交车,他们的父母很心疼这些孩子在大城市里漂泊,他们就会五点钟去帮孩子排队,为了让他们的孩子上班的时候可以不用这么辛苦,可以多睡15分钟时间,这些人他们有自己的爱恨情愁,有他们的欢乐,有他们的喜悦。
我还想再给另外一个场景。我特别喜欢问同学们一个问题,让大家去猜最流行的或者最受欢迎的微信公众号是什么,同学们会想到很多很多,之前是想到咪蒙,之后会想到其他的一些微信号,但实际上最受欢迎的微信号是这些官方媒体的微信号,比如说新华社、《人民日报》。
我们之前和《人民日报》微信号做过一个交流,《人民日报》当中最受欢迎的是每天晚上十点钟有一个夜读栏目,每天晚上到了特定的时间段,如果这一档栏目还没有按期发出来一篇心灵鸡汤的文章,《人民日报》的小编说后台会涌入大量的读者留言说:小编小编我现在正躺在床上,我现在正在回家的下班的路上我特别需要这一篇心灵鸡汤的文章给予我动力,给予我每天继续早起的动力。
大家把这三个场景可以连在一起,想象现代世界每个人的生活状态,特别是大城市里这样一种精神状态、生活状态:堵在路上、挤在公交车、挤在通往地铁的浪潮人潮当中,非常疲倦,非常没有目的,非常迷惘,回到家倒在床上,倒在沙发上,等待一篇心灵鸡汤的文章来给自己继续打气。这样的场景特别有趣,特别值得用社会学的思维方式去好好地和他们进行对话。
四、利益当先、精于计算的都市人格
郝汉:刚才讲的三个场景,具体化地理解现代性的时候,齐美尔也出现在您这本书里。您认为在这三个场景里,齐美尔有哪些非常深刻的洞见可以给大家一些启示?
严飞:对于大都市的精神状态,齐美尔有一篇非常重要的文章,叫做《大城市与精神生活》。在《大城市与精神生活》当中齐美尔提出非常经典的、具有深度共鸣的问题,就是一个现代人在城市当中生活,如何保持独立的个性,并且可以好好的生活下去。
对于这一问题,他是从大城市如何塑造人的精神世界的层面进行解读,一方面我们可以看到大城市对于年轻的,特别是不安于现状的年轻人来讲有极大的诱惑力,如果第一次来到大都市,站到天桥上面,灯火通明、车流穿梭,人们的穿着打扮非常时髦、时尚,有很多的机遇发展,对于居于其间的人来讲它具有无限的可能性。我记得我2000年上大学,到上海的时候,我当时是第一次对于上海有过如此亲密的、紧密的接触,看到上海的高楼大厦,在上海的外滩看到浦东的发展,非常受到震撼,觉得自己真的是深深陷入到大都市的或者上海的十里洋场的五光十色、意乱情迷当中。
但另外一方面,大都市也有大都市的不便利性,或者大都市的冷漠、人情的冷漠、交通的拥挤、环境的污染,大家都挤在西二旗地铁站,都挤在北京国贸天桥下,等待一辆通往通州、燕郊的巴士。我记得我在大一、大二的时候,做社会调查,跑到浦西非常偏远的上海街道社区里面,筒子楼里面,进行入户访谈。
在入户的过程当中,因为我们是外地人,不会讲上海话,自然会被上海的本地人,特别是上海的一些老婆婆歧视,即便我们掏出复旦大学的学生证,他们也不相信,也觉得你是外地人,用不是特别好的语言对待外地人。这样的一种排挤、冷落,实际上意味着大都市里面,在人际交往上有一种精于计算、利益当先的冷漠关系。
这样一种非常冷漠的利益当先、精于计算的人情氛围会让人非常沮丧,就会导致产生所谓的都市人格。都市人格就是人和人之间没有这么信任,大家比较谨慎,比较矜持,精神高度的紧张,理智会压倒情感,等等。特别是在异乡漂泊的人来讲,他们会觉得大都市这种精确性、准确性是它的便利,但同时又会过于精密、过于算计、过于对于自我个性的牺牲。所以齐美尔在这篇文章里面讨论了大都市对于人的影响。
五、拆拆拆,行业和市场没了,人就会走?
郝汉:我想给老师补充一下我的经验,您之前在美国、英国上学,我之前也在英国上学,在国外那种真实的生活,你与人打交道,哪怕是在都市里,你需要去买菜,你需要去超市,需要跟理发店的人聊天,跟肉铺也很熟,但这种生活在中国的大城市,哪怕是二三线城市甚至都消失了。在北京做任何事情,我手机上移动互联网下一个单一切都完成了,但如果在英国的一个中部城市,我需要这件事情变成我第二天真实的活动轨迹,变成我一个需要去跟人打交道才能做的事。这可能也是中国对现代性极度的挥洒之后带来的更严重的问题,可能是我们之后要面对和要处理的大都市的人的精神生活和真实的生活逐渐远去,肯定会对心理上造成很大的冲击,这是我想到的一些。
严飞:对,我也想再补充一点。对于现代性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我们之前也做了一项学术研究,现在也有两篇英文论文发表。我们做的是对于北京菜市场的拆迁,有段时间北京是说推出“以业控人”的政策,觉得北京要有首都功能,如何保证首都功能,就是要把这样一些社会边缘群体或者社会的弱势群体,不发挥首都功能的这些群体,让他们主动离开北京,他们当然不愿意主动离开北京,那就把他们所依附的这种行业、这个市场拆掉,行业和市场没了,人就会走,这是一个基本的逻辑。
所以当时有一个叫做太阳宫的菜市场,就是在北京的太阳宫地区,2013年的时候把它拆掉了,太阳宫菜市场是一个非常非常巨大的菜市场,把菜市场拆了以后,希望这些菜贩离开北京。我们做了三年的长期追踪调查,发现这些菜贩实际上并没有离开北京,95%的人都选择继续留守北京,但是同时他们赖以生存的菜市场被拆迁了,很多人必须要转行不再做菜贩,他们平均薪资收入下降20%-25%。同时我们又做了菜市场周围的街坊邻居的社会调查,就问菜市场拆迁以后对他们生活产生什么样的影响。特别惊讶,我们以为菜市场最主要的功能就是买菜,菜市场被拆迁他们没有办法买菜,这是他们最大的痛点。
我们的社会调查最后显示出,对于街坊邻居来讲买菜的需求是他们排在倒数第二位的需求,排在第一位的需求是交际的需求,社会交往的需求,这个菜市场是很多老人家互相交流的一个场所,有些老人家是跳完广场舞回来去菜市场买菜,一边买菜一边交流,街坊邻居之间交流。还有一些老人家,爷爷辈的、姥姥辈的,他们是接孙子、孙女放学,放学路上大家一起在菜市场相见,大家就互动交流。所以它不仅仅只是买菜的单一的功能性场所,更多的是一个社会交往的场所。
我讲的是街坊邻居之间的交流,同时街坊邻居和菜贩之间也会有交流,大家都有这样的体会,不知道你现在是不是去菜场买菜,我经常会去菜场买菜,因为我住在清华校园里面,我们有菜市场的。在买菜的过程当中,你会不断的跟他们交流,久而久之你就会在固定的一个菜摊买橘子、买香蕉、买水果,在另外一个菜摊买肉、买鱼,慢慢就会和他有长期的交流。就好像我们用58同城到家,请阿姨上门来打扫卫生,一开始用58到家APP平台,用多了你会认识一位阿姨,说我们要不要不用58同城到家,我们加一个微信,加一个手机号,我们有需要的时候就和阿姨打电话,她直接就来了,这样阿姨不用付平台费,我们也不用付平台费,而且用熟不用生,用熟悉的阿姨总是比较放心,久而久之你就和阿姨产生了感情,你和她不断的交流:阿姨你的孩子在什么地方、阿姨你的孩子上大学了特别了不起、阿姨我这个衣服不穿了送给你之类交流。这就是人和人之间的交流,这也是为什么要学社会学,社会学会观察到这样一些有趣的社会现象。
六、那些平淡无奇的日常琐事,是重要的课题
郝汉:我之前看到项飙老师的一个概念,叫做重建一种真实的附近,我觉得这个挺重要的,菜市场是一个附近。我从英国回来之后,在北京真的丧失了很多真实的生活,就是这种买菜几乎没有了,都是外卖,都是很简单的一键下单。我唯一能够感受到的是,我会在我们周边小区一个理发店,很固定的去那理发,我会感觉到一种安定的感觉。
严飞:对,你会找到自己固定的理发师。
郝汉:这个真的也是社会学学到后面你会去反思的一个东西,像严飞老师讲的,并不是很宏大的概念,宏大概念背后还是要具体到你怎么面对这个时代的巨变,怎么样找到那个真的能重建你心灵的那个工作的部分,也是社会学去完成的。
严飞老师在这本书的结语《社会学的想象力:批判理解世界的钥匙》里引用了美国社会学家彼得·伯格的书,叫做《与社会学同游》。这本书对我的影响也特别大,可以说我对社会学整体上的把握是由这本书完成的,我也像严飞老师一样,很想给大家推荐。严飞老师能不能借这个机会说一说,你为什么特别提到这本社会学启蒙读物?在全书里作为社会学启蒙读物,有中国经验结合的,您好像也只是特别提到这一本。
严飞:我特别推荐这本书是因为它的视角和我的视角有很多接近的地方,这本书的视角会把普通人的社会、普通人的世界、普通人的言行举止、悲伤欢乐、辉煌痛苦作为一个研究的主体,来进行深度的描绘,换句话说就是去研究社会和人的一个存在。我现在正在打开这本书,它的几章,叫“社会学视角,人在社会、社会在人、社会如戏”,其实描绘的是人和人之间的一种社会的关系。
这样一种关系,其实作者彼得伯格也在这本书里提出说,社会学研究当中最有兴趣的一个点,或者是最有价值的一个点,是叫做平民化的焦点。很多学者认为一些平淡无奇不值得作为科学研究对象的事情,我们就不要去研究它,不要去关心它。但是对于彼得伯格来讲,他觉得这些平淡无奇的日常生活当中的琐事,或者是所谓平民化的焦点,实际上应该成为社会学研究的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课题,无论这样的现象是多么的平淡无奇。
就像我刚才提到说,我们发现有固定的理发师,有固定的阿姨帮我们打扫卫生,我们去固定的地方买菜,去固定的一家兰州拉面店吃拉面,这些固定的生活形态每天都在发生,很多人往往忽视,或者很多学者说这些有用吗?这些值得去研究吗?我觉得很重要,这样的一种社会史,或者是在现代性下的个体生活的日常实践,它背后有非常丰富的文化的含义。
我前面也解释了,现代性下人的焦虑、人的一种依赖,或者人的社会关系、依赖的关系正在被潜移默化地被社会转型的洪流(改变),大家要是觉得这些东西不重要,就会去破坏它,就会把这样平民化的焦点,这些平淡无奇的人和人之间的依赖去打破。把这些小店拆了,你的理发店就没了,要重新去找一家理发店,甚至要跑到非常奢侈的、豪华的大型商场里面,去花很贵的钱享受这样的理发服务,一边理发的时候一边没有任何交流。
所以这些平淡无奇的事情,它背后有很多很多值得我们去深度讨论的结构性的动因,或者是深度讨论的一个社会发展变迁背后的一套机制和逻辑,这也是为什么我觉得这本书很有趣。
七、保持价值中立,变得特别麻木?
郝汉:社会学家如果试图从理性和科学的角度去理解和总结人性和秩序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究竟该不该保持价值中立呢?如果保持价值中立,会不会导致缺乏情感关怀,反而丧失了所谓的人文主义的视角,变得特别旁观、特别麻木?
严飞:对这一问题,其实在社会学里也是有过非常激烈的争论,迄今为止都没有一个非常标准的答案。这样的问题就是,到底应该是保持一个价值的中立,还是同感共情。特别是很多时候我们带着学生做田野调查、社会实践,我们都会问这样的问题,到底是应该用同感共情的方式去接近我们的被访者,接近整个社会,还是保持社会学的中立,保持一种抽离的态度。
有些学者觉得社会学提供了介入社会及政治行动的一种科学的基础,为了让社会学有它的学术幸运,必须要保持采取一种超然和价值中立的立场。还有一些学者,比如彼得·伯格说社会学更加接近人文学科,所以叫人文主义的视角,它不是自然科学,人文主义的视角当中必然有人的主观的想象力、一种描绘社会的能力,这样一种知识体系没有办法完全做到全然的中立与超然,必须要带有自我的情感。
对于我来讲,我是这样想的,我觉得还是要针对研究对象的不同,采用不同的观察视角或者是采用不同的切入视角。我们常常说在田野当中有三种不同的境界:第一种境界,我们要找到田野对象,找到我们的被访者;第二种境界,如何去接近这些被访者;第三种境界,如何走进他们的内心,走得非常近。
对于第一层境界如何找到,有很多种不同方法找到这些潜在的被访者,无论是路边的偶遇,或者是滚雪球,或者是街道大妈、亲戚朋友、好朋友带着我们进入到田野,总是能找到我们的被访对象,所以第一层相对来讲比较容易解决。
第二层如何去接近这些被访者,这非常好玩。我之前有带着一批来到清华大学做交流的香港浸会大学的学生在北京做社会调查,这些香港来的学生在北京,他们选择去做北京公厕的社会调查,他们是讲粤语,普通话不是特别好,他们想到胡同里采访这些街坊邻居、大妈、大伯,他们对于北京公厕的使用体会,一个基本的看法。对于这样的一个被访者,我们要怎么样去接近他们?我们没有办法去公厕里一边上洗手间一边做访谈,也没有办法让学生们堵在公厕外面等他们出来以后追上去说,大伯你觉得公厕使用怎么样。
怎么接近他们?其实很简单,就是在胡同里面找到一家小卖部,然后我们在小卖部去买东西,和小卖部的店主拉拉杂杂的聊天、闲聊,会有很多街坊邻居、大妈、大伯也会到小卖部去买东西,打酱油,在买菜的过程当中,买酱油、买零食的过程当中,你就可以和这些大妈、大伯一起聊天,有的没的都聊,比如阿姨今天天气很好,你吃了什么,为什么要买酱油,酱油多贵啊,慢慢扯出一句,我看到这边有一家公厕,里面好臭,怎么这么臭。慢慢把话题带出来,这样的话他会不断的和你进入到一种谈话的状态当中去,慢慢的就接近他们,可以找到很多东西,可以挖掘出很多有用的潜在的信息。对于这样的一些被访者,我们当然是保持学者或者调查者的价值中立、客观、抽离,我们不需要走入他们的内心,我们只是在做一个社会调查。
但是对于另外一些被访者,我们需要走入他们的内心,比如说性工作者,人民大学的黄盈盈老师和潘绥铭老师,和他们的整个团队,做了大量的珠三角地区的性工作者的访谈。在访谈过程当中,你不可避免的会陷入到性工作者固有的逻辑思维或者固有的话语术当中,基本所有的性工作者都会说我是第一次做,或者我才入行不久。所有人都会说我是家庭里面遇到巨大的打击、事故,家里面有人生病、住院,特别缺钱,所以不得已才做,等等,这样非常相似的话语术或者套话。如果我们不走入他们的内心,没有办法做到共情、共景、共述的“三共”状态,没有办法走入他们的内心,就没有办法获得真实的被访者信息。
再比如说,我的同事郭于华老师在过去三年时间里,一直在做尘肺病患者的口述史访谈,她上上礼拜发了一条朋友圈,说2018年做访谈的有三位尘肺病患者刚刚过世。对于这样一个人群,如果你不走入他们的内心,他们就会从这个世界上消失,再也没有办法去记录他们的遭遇、他们的伤痛。
所以针对不同的人群,我们是采用不同的方式,采用不同的到底是应该价值中立,还是我们要有自己特定的价值偏好。
八、社会学家是说故事的人
郝汉:文学艺术的重要性有时候是社会科学或者人文学科无法替代到的,您个人遭遇、个人经历中,社会学是一部分,文学艺术方面是不是也给你非常大的安慰?对社会学的东西也是有一些补充吧?
严飞:对于文学和艺术我特别喜欢,我也特别喜欢把文学和艺术和社会学进行紧密的结合。我们发现社会学,在过去二十年时间里,确实出现一个社会科学量化的趋势。这样的量化趋势,当然我自己也会做大量的量化的论文,量化的趋势之下,大家往往会忽略有血有肉、非常丰满、饱满的社会学故事。我特别喜欢的一位学者叫做叶启政,他是台湾的社会学家,他曾经写了一篇文章说社会学家作为说故事的人,他是一个story teller,我们有必要把社会的故事呈现出来,在故事的发展进程当中会呈现出很多,不是通过公式,不是通过模型可以计算出来的期然结果,没有预测到的社会现象和结果,我觉得非常有趣。
在文学和艺术领域,我觉得很有必要和社会学进行结合。比如我在清华大学教授一门课,本科生的课,叫做历史社会学。在这门历史社会学的课上,期中和平常的作业让同学们认真读社会学相关的理论,比如说现代性的兴起、国家的诞生、资本主义的兴起、革命的爆发、暴力的产生等等,通过不同的学术论文的阅读来掌握背后的理论脉络。最后的期末作业会让同学们读一本中国题材的历史小说,这些小说包含了陈忠实的《白鹿原》、张炜的《古船》、葛亮的《北鸢》,甚至梁鸿老师的《出梁庄记》等现当代的小说和纪实作品。历史题材的作品如果我们只是按照小说去读,酣畅淋漓,读完以后觉得这些非虚构故事和真实生活、和当代生活、和我们的日常生活、和我们的历史相去甚远,它只是小说。
但如果让同学们把相似题材的小说放在一起,再结合我们学习到的历史社会学的理论,我们发现这些不再仅仅只是小说,而是它描绘的是历史发展进程当中出现的种种记忆的裂痕、时代的暴力、时代的伤痛、人们的呼喊、人还有记忆的颠覆、性别的张力、城市的欲望等等。在小说的阅读当中不自觉的会从非虚构文本跳出来,和过去的历史现象结合,同时再加上社会学的理论维度,三者结合在一起就会非常有它的穿透性。这样的话,艺术、文学和社会学理论就紧密的结合在一起,社会学就增加了它的一个历史的阐释性,增加了一个文学向度的张力,这一点来讲的话,特别是对本科生来讲非常有必要。
所以这也是我慢慢在尝试的,让我们的本科生,让我们的学生,无论是来自任何专业,还是很多不一定是来自社会科学专业的学生,他们很喜欢读小说,把小说和历史、和理论结合在一起,我觉得非常有必要。
推荐书目

《江村经济》费孝通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9.04

《穿透:像社会学家一样思考》严飞 著
理想国丨上海三联书店 2020.1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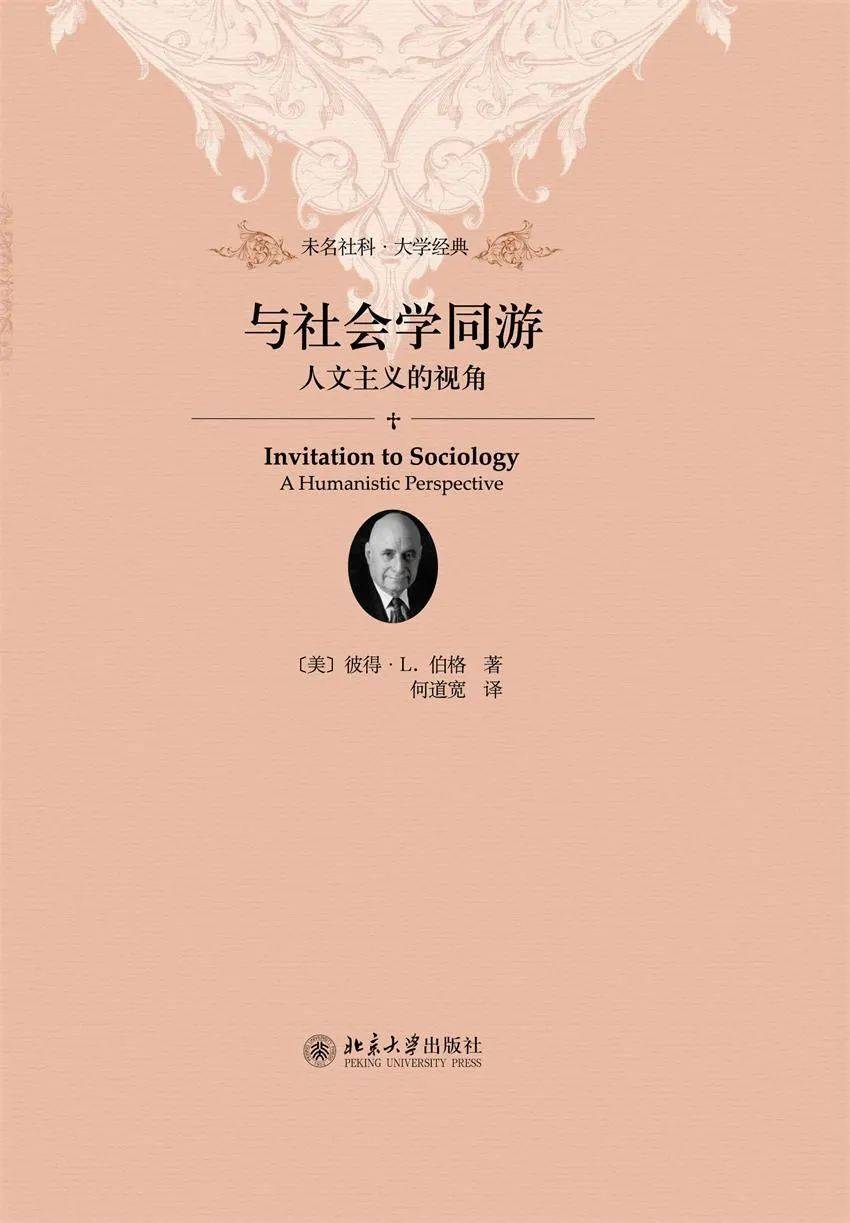
《与社会学同游》[美] 彼得·伯格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4.10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理想国imaginast(ID:lixiangguo2013),内容来自播客Naive咖啡馆第23期《像社会学家一样思考,做清醒的普通人》,嘉宾:严飞(社会学者、清华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主持:郝汉(利兹大学社会学硕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