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扫码打开虎嗅APP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看风景的局外人(ID:juwairen_neweekly),作者:花瓢白,视频:夏军青,出品:局外人,头图来自:视频截图

很多年前,人们会用“淘金地”和“混乱”定义深圳华强北,因为它诞生过“一米柜台的亿万富豪”,也造就过野蛮生长的山寨天堂。
但如今,在华强北步行街中摆放的免费钢琴,形成了一个更奇特的存在:它容纳了每一个需要慰藉的打工人、失意的艺术家和从现实出逃的流浪者。
贴膜男孩和修手机的大神已经换了几代,但华强北的传奇还在续写。而这8台街头钢琴,连接的或许就是一个真实版的“遍地都是六便士,但人们仍愿意抬头看月亮”的故事。
再见,琴友
2022年的春天,一场小小的追悼会在华强北的角落悄然进行。十来个陌生人用啤酒和小圆蜡烛围起了一块空地,在冷风中清唱起《感恩的心》。
他们正在纪念一位叫卢雪峰的琴友,她刚因脑溢血意外离世。不远处,就是他们常聚在一起弹奏的8台街头钢琴,卢雪峰曾在那里度过无数个春风沉醉的夜晚。
卢雪峰走的时候才59岁。她看起来年轻、优雅,从前总喜欢穿五彩斑斓的碎花裙和高跟鞋来弹钢琴,亮眼的大耳环会随着她跳跃的指尖闪动。

卢雪峰旧照。图/受访者提供
她几乎每晚都会出现在华强北。最初,她只是想借着免费钢琴弹给深夜下班的打工人听,慢慢竟汇聚起了一个小社群——她一弹奏,大家就簇拥在她身边唱歌,像过节一样。
为了在弹琴的同时也照顾家人,人们还常常看到她把患阿尔茨海默症的父亲和母亲带到华强北来遛弯,一起听街头的音乐会。
春去秋来,人们都习惯了华强北这一抹浪漫的剪影。
因此,她骤然离去的那天,很多人都难以置信,一个叫“华强北浪漫钢琴夜”的300多人的群组炸了锅,琴友们都想到追悼会上送别她,但是疫情不允许。
小杨是卢雪峰的女儿。直到母亲走后,她才知道有这么多人也爱着母亲。长长的问候像雪花一样飘向她,她也在群里看到了那个小小的追思会,十分触动,但当时她的小区因疫情被封了,她出不去。
她还看到有琴友根据母亲每日的必经之路,手绘了两张小画纪念她。


琴友为卢雪峰画的“日常照”。图/受访者提供
在小杨看来,母亲为了家庭放弃过很多梦想,钢琴就是其中一个。在最劳碌的几年,母亲只能在生活的缝隙间自学,夜晚还自荐到一些咖啡厅弹琴——从20点到23点,接受顾客的随性点曲,不要钱也可以。
卢雪峰还很爱摄影,退休后还曾到非洲埃塞俄比亚的原始部落采风,到孟加拉国的贫民窟和孩子们待在一起。在她家的钢琴上,摆满了卢浮宫的画、俄罗斯的套娃、土耳其的碗碟……
但近年来,母亲越发无暇出游,因为外公外婆的身体越来越差,母亲不忍心把老人家送到养老院,一直带在身边照顾。
因此,华强北的钢琴成了她生活中最大的慰藉。但小杨发现,自从母亲加入了华强北这个大家庭,每晚连吃饭的时间都是挤出来的,“她总是急着走,晚饭不能超过8点,因为华强北的歌友会8:30要开始了”。

从前,卢雪峰常常带父母一起来华强北弹琴。图/受访者提供
一开始,小杨也困惑不解,她觉得这像“街头卖艺”。后来她才知道,妈妈在默默做一些照亮别人的事——她不仅帮一位双目失明的琴友找到了工作,还认了一位小提琴手做“干儿子”。
这个男孩正处于叛逆的年纪,时常会跟父母吵架,卢雪峰就耐心开导他,有时候还会上他家里调解。
在卢雪峰离开前约一个月,她还马不停蹄地为琴友组织K歌大赛,帮忙搭建舞台,邀请演唱嘉宾、摄影师、化妆师,结束后又熬夜把图片和文稿编辑好才肯上床睡觉,像一台不知疲倦的永动机。
“自从妈妈认识了他们之后,每年的生日连着一周都过不完的,琴友们要分批给她过。”小杨说。
就这样,这些本该在路上擦肩而过的陌生人,因为8台钢琴逐渐联结成一个数百人的活跃社群。
它就像是一个万花筒,在深圳被“高效、物质、冷漠”等刻板词汇野蛮折叠时,又重新旋转出人们对这个城市的想象。
不再失语的老年人
深圳的华强北,本来就是一条充满传奇的街道。
从机器轰鸣的厂房到通往全球的大卖场,华强北创造了无数的草根创富梦,是一天销售额可超1亿元的“中国电子第一街”,马化腾当年也是在这里创立了腾讯。
但华强北大概没想过会有与钢琴共存的一天。
尖锐的拉车声在每个角落蔓延,做核酸的广播和商场的音响360度环绕播放,店铺里混杂着各地方言,拉货的人、推销的人、找工作的人、无所事事的人,都在这条街上游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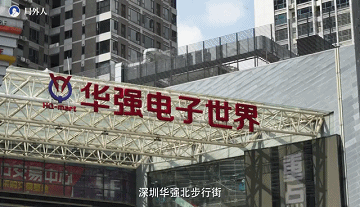
高峰时期,华强北日均人流量可达50万人次。图/局外人视频
但恰恰是钢琴这个格格不入的存在,让很多意想不到的人聚在了一起。
老年人是街头钢琴联结到的最有意思的一群人。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深圳好像是一个没有老人的城市,遍地都是脚下生风的年轻人,老年人是失语的、被隐没的。
但在华强北,可以看到各式各样的老年人在这里游走。
老苏是一位61岁的流浪汉,早年做木工出身。他屡次想转行“搞艺术”,学过根雕和绘画,参加过声乐大赛,还当过临时演员,什么都小有成就,但又一直被命运生硬拦截。

流连在钢琴边的流浪汉老苏。图/局外人视频
他离演艺梦最近的一次,是2003年电影《生死界线》在深圳开机,老苏几经艰辛终于入围,但还没等到正式开拍,他就被一块意外飞来的瓦片插中了胸口,差点丢了命。
后来,他当过保安,做过苦力,打过零工,其中一只眼睛还因工伤失明。有一段时间他专职喷广告牌,当天的喷漆有哪几种颜色,次日起来的痰里全都看得见,“医生告诉我肺部上有厚厚一层,像老茧一样”。
如今,老苏已经到了退休的年纪,但晚年没有任何着落,也习惯了风餐露宿,华强北就成为了他最爱落脚的地方——因为弹琴可以让他心情平和,血压稳定。
医生说他的血压已经到了“极高危”的阶段。“头两天我才真正醒悟了,什么都不要想太多,忘记过去,尽量让记忆消失。”老苏说。
他喜欢弹一首自己反复修改过的曲子,叫《为了那个梦》。这是他为第一部准备参演的电视剧写的。二十多年过去了,这个电视剧在网上都难寻踪迹,但他那个“梦”还像一棵不甘枯萎的仙人掌,一直扎在荒漠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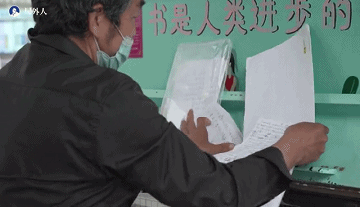
老苏演唱自创的《为了那个梦》。图/局外人视频
也有与钢琴相伴了大半生的人,把晚年生活寄托于此。
72岁的陈云昌是华强北年纪最大的常客,自从三年前得知这里有钢琴后,他几乎每晚坐一个多小时的地铁过来,风雨无阻。
陈云昌说自己是走了几十年弯路的人。在上世纪50年代初,新中国还没正规的钢琴教学,但陈云昌已经开始学琴了,他的老师是从基督教教会“偷师”回来教他的。
13岁那年,陈云昌如愿考上了音乐学院,但最终却没上成——彼时是1963年,主考官跟他说,中国在提倡民族化,学校主要开设二胡、笛子、琵琶、古筝、唢呐等民乐班,钢琴、小提琴、萨克斯这些属于洋乐器,暂不开班。
陈云昌不能接受转专业,只能遗憾离开。但在之后的几十年,他没有放弃钢琴,也一直在旁观中国钢琴行业的变迁。

陈云昌被街坊亲切地称为“钢琴爷爷”。图/局外人视频
他不认同当下的考级制度,觉得很多考生对钢琴的美一无所知。“钢琴不是舞蹈,不用整个身体乱动。一些年轻人在夏天弹得满头大汗,弹琴比种田还辛苦是干吗?”
他以《献给爱丽丝》作为例子:“很多人喜欢这首曲子,但你知道贝多芬跟爱丽丝是什么关系吗?爱丽丝是贝多芬的学生,也是他的情人。在那个年代,老师跟学生谈恋爱是不允许的,写封信都不行,但给首曲子可以。”
陈云昌边说边开始弹琴。第一段,他弹得谨小慎微:“这是贝多芬在谈情说爱,像说悄悄话一样。很多人弹得很响,就没有这个感觉了。”
中间一段,他弹得甜蜜欢快:“这是贝多芬回忆起他们相处得很开心的日子。”
结尾一段,他琴键上的情绪明显焦躁了起来。“听起来是不是很烦?这是爱丽丝知道贝多芬心里很难受,大家没办法在一起,难受得就像捶胸口一样。”陈云昌边说边用拳头大力捶自己,“像这样砰砰砰砰。”
但凡逮着一个对钢琴有探讨精神的人,陈云昌就会展开这种细致的表达。这也是他喜欢华强北的原因,在这里,他自成一派,不受任何学院理论的约束。

陈云昌在“街头学院”现场教学。图/局外人视频
还有一些老年人,把街头钢琴当作他们融入年轻城市的桥梁。
李伯是一位定居在深圳的北京大爷,头发花白但精神爽朗,穿着一件白T恤、背着一个双肩包就来了。
十多年前,他刚从一个上市公司退休,身体落下了不少毛病,还患上了恼人的帕金森,整个人有点萎靡不振。
但自从他知道华强北可以练琴之后,“就跟年轻人一样朝气蓬勃地来了”。每天早上8点,他骑一辆共享单车雄赳赳地出发,后来发现跟上班族有点“抢路”,就自觉推迟到9点出门,一直练到中午12点才回家。
尽管60多岁才开始学弹琴,但这让李伯找回了读书时代的精气神。“要是按照帕金森这个病的趋势,人就颓废了,最后吞咽困难、活动困难、摔倒骨折,躺在床上得褥疮慢慢就死去了。我不能说跟疾病作斗争,但我要自娱自乐。”
他喜欢深圳这个充满创造力的城市,思想也变得相当超前,会主动学习“躺平”“内卷”这些新词,前不久还申请了遗体捐献,家人相当震惊。

穿着年轻的李伯,每天都来打卡。图/局外人视频
在过去的共识里,钢琴意味着西方审美,甚至是贵族气质。但在华强北这里,它们就这样被路人随意弹着,不需要华贵的地毯和高级的舞台,固有的印象被逐一消解。
不管是世俗意义上的精英阶层还是loser,是失意的老人还是需要自我治愈的人,都可以在这些钢琴面前忘却蹒跚的岁月。
寻求出口的打工人
在“华强北浪漫钢琴夜”这个群里,还会看到另一种奇妙的冲突感:有一些昵称带着“手机配件批发”“蓝牙音箱耳机爆款”“5G新零售”字眼的人,会在群里一本正经地讨论钢琴的话题。
这些带着“华强北属性”的打工人,是除了老年人之外另一批来弹钢琴的常客。
自上世纪80年代市场经济以最惊人的魄力驱动这个城市,华强北就成为了远近闻名的打工天堂,最火热的时候“一铺难求”。
任何时候走在这条街上,都会看到成千上万的小电动车和快递车,附近都是热气腾腾的快餐店,有卖肠粉的,卖麻辣烫的,卖烧烤的,来自全国各地的“深漂”都不担心会饿着肚子。
但打工人需要的不仅仅是这些。他们的快乐与哀愁,也需要一个宣泄口。

华强北随处可见的拉货工人。图/局外人视频
王齐和是常年在华强北找活的装修工人。在深圳疫情严峻时期,很多商场都封了,他几乎没活干,心情郁闷,但幸好还有钢琴陪着他。
如果不是命运让他飘落在华强北,王齐和大概这辈子都不会学钢琴。在湖北老家时,王齐和是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终日埋头于种满棉花、西瓜和水稻的田间。因为收入微薄,2002年哥哥把他带到深圳搞装修,一做就是二十年。
但王齐和与身边的工友不太玩得来,因为他们只喜欢打牌和喝酒。偶尔发现的街头钢琴,刚好给了他一个跳脱庸常的出口。
如今,王齐和已经在华强北自学了三年,那一双常年劳作后黝黑粗糙的手,也开始在琴键上行云流水。“要弹得看不见五指”,他说。
他还把清洁保养的活儿揽了下来,每个星期都会提着消毒水去擦每一个琴键。

每天一待就几个小时的王齐和。图/局外人视频
不是只有“闲人”需要钢琴。小尹是在附近上班的一位眼科医生,常常会顶着正午的烈日出来弹上几首。
做近视眼手术的工作压力很大,小尹每天忙得焦头烂额,晚上回家还要照顾小孩,因此他只有午休时间能喘口气,可以把标着“临床数值”的手机暂且搁在一边。
但他每一首都弹得很急,像是2.0倍速的演奏,因为一有病人来了,他就要赶回去。
尽管从小在深圳长大,但他也清晰感到这个城市的节奏越来越快,“只能用自己的方式平衡,不接受就会被社会淘汰”。
回想起来,小尹有点感谢父母小时候逼着他学琴,至少能让他偶尔停下脚步,回溯内心。

小尹医生的经典标识。图/局外人视频
还有一位失恋小哥,在一个角落默默弹奏《月亮代表我的心》。他说自己是一个“不太懂谈恋爱”的IT男,老是说错话,最终错过了一段真挚的感情。
他之前一直想练好这首歌,在时机成熟的时候跟女孩求婚。但最后曲子还没练成,感情却已经走到了尽头。
“我之前想成为她的依靠、她的港湾,但最后却变成了她成长路上的障碍,变成了一堵没办法绕过去的墙。然后我又想,那我宁愿变成你垫脚的石头,也不愿变成你前进路上的墙。”他说。
片刻,他觉得自己又开始话痨,腼腆地笑:“所以我觉得男生要学会沉默,以后还是多练琴少说话。”
华强北的钢琴,很好地容纳了这些需要慰藉的人们。近两年,原本快速运转的城市不时像被上了卡顿的发条,身处其中的人,更能感受到自身在面对意外时的平庸。
而街头的钢琴,忠实地记录着这个城市人民的心声,并与他们一起对抗现实的棱角和繁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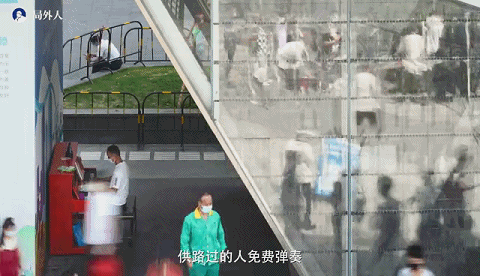
华强北的钢琴,接纳了无数疲惫的人。图/局外人视频
“街头”的甜蜜与烦恼
这个街头钢琴的灵感,最初来自英国艺术家Luke Jerram。自2008年起,Luke和团队在全球70多个城市放置了2000多架街头钢琴,并赋予它们一句浪漫的宣言:“Play me, I'm yours.”
之所以发起这个项目,是因为Luke某天在自助洗衣店发现,很多人每周都去同一家洗衣店,遇到同样的人,但从来不会主动交谈。他希望通过某种有趣的介质,打破这个固化的沉默空间。

国外街头钢琴一角。图/网络
这个想法就像一串充满生命力的种子,在全球很多大城市漂流起来,但有长期坚持的,深圳是极少见的一个。
孙永红是华强北公益钢琴的运营负责人,2018年接到这个任务时,她正在管理深圳乐器城的钢琴博物馆。街道办希望她参照国外的创意,收集一些旧钢琴涂鸦展示,没想到吸引了许多外来务工者来弹。
然而,要持续运营这个项目并不容易,因为钢琴属于昂贵的精密乐器,而且木制品也不适宜长期放在户外。
孙永红首先要解决的是人的难题。一个新事物如何被市民对待,决定了它的存活空间。被摆放在街头的钢琴,时不时就会遭遇恶意,琴键被人烧过,凳子也会隔三差五地被人偷。她只能装监控,给凳子上链条。
同时,在深圳这种南方城市,裸露在外的钢琴免不了被风吹日晒,特别容易受潮,涂鸦也反复被侵蚀。孙永红只能又上漆又镀膜,还在每一台钢琴上贴上她的电话,就是为了钢琴损坏后能第一时间被她知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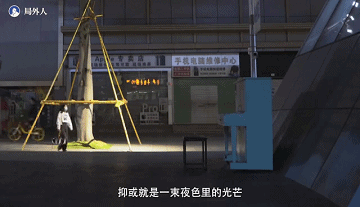
每一台钢琴,细看都有运营者用心的小细节。图/局外人视频
幸好孙永红在乐器城时认识很多能工巧匠,调音的、维修的、卖配件的,孙永红一个电话就能找到人。
最容易引起纠纷的是扰民问题。孙永红长期会收到派出所转过来的噪音投诉,说琴声过于刺耳。于是街道办定下规则,钢琴每天只在9点到13点、14点到22点开放。
但有些琴友仍是不遵守,矛盾升级后就有附近的居民来砸钢琴。“有人说家里有高考生,也有人说他每天失眠。我们只能两面协调,最后只好给琴上锁,或者把钢琴搬走。”
这些管理上的琐事孙永红几乎每天都会遇到,但她仍然很热爱华强北这个地方。自1986年毕业被分配到深圳后,她就在这里度过了将近36年,看着各类电子数码市场像雨后春笋一样填满了这条老街。
她也目睹华强北一度成为深圳的代名词,代表着一夜崛起的经济、前沿科技的集中地和不知疲倦的生意人。
而华强北的钢琴,就是当中最温暖的一个项目,充满人情味儿。在这里,弹得好会有人喝彩,弹得不好无人嘲笑,环卫工人会跑去跟钢琴合照,中老年人会开始精心打扮,就为了来参加这里的平民音乐会。
并非所有人的家里都没琴,只是在这里会形成一个神奇的场域,陌生人之间会流通和交互,也能强烈地感应到钢琴上的那句“I'm yours”。
也许是耳濡目染,孙永红后来也买了一台钢琴回家,但因为太忙一直没学成。如今她想着还是要学起来,这样在退休之后,也能来这里弹上一曲。

华强北的其中一台钢琴上,写着“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这句话跟钢琴没什么关系,但却显露出公共钢琴跟图书馆相似的社会职能:接纳、包容所有人,免费提供通往学识的阶梯,让再普通的人也可以争取艺术上的平权,解救一段可能始终平庸的人生。
它是一个流动的载体,在每个人身上留下的印记也不尽相同。
一位叫张旦旦的盲人琴友在这里练琴后,被大众赏识,应邀到一些商场、音乐酒吧表演。这或许是他职业生涯的一次转机。
王齐和找到了人生的另一种精神寄托。他不为了能开班赚钱或成为音乐家,因为弹琴本身已是一种享受,不必承担“苦练才能成才”的枷锁。
它与身份、地位、阶级、利益无关,就像抬头即可见的皎洁月光一样,免费又宝贵。
而对于卢雪峰的女儿而言,华强北的钢琴让她更了解生前的母亲。看到它们,她就仿佛能听见母亲遗留的声响——特别是儿时家里逼仄,钢琴只能摆放在卫生间旁边,所以每当她洗澡时,就会指定妈妈弹她最爱听的《美女与野兽》和《梦中的婚礼》。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看风景的局外人(ID:juwairen_neweekly),作者:花瓢白,视频:夏军青,出品:局外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