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扫码打开虎嗅APP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看理想(ID:ikanlixiang),作者:阿郎,头图来源:《一一》
6月29日是台湾著名导演杨德昌的逝世纪念日。
距离2007年已经过去了十余个年头,杨德昌依然是电影界最常被提及,也最受尊重的名字之一。他影响了无数东亚电影人,是华语电影当之无愧的代表人物。
今年五月也是杨德昌代表作《一一》的戛纳首映20周年。
贾樟柯在《贾想II》中曾写道:中国有一句话是“天妒英才”,或许就是因为《一一》说清楚了我们生活里的一切,他为我们揭开了生活的谜底,完成了它的使命,所以也就离开了我们。
我们怀念杨德昌,更怀念他看待社会人情的目光。在失去他的日子里,重温《一一》,去感受其中跨越时间维度的触动,或许就是与这位伟大的导演隔空对话的最佳途径。
一个台北家庭
《一一》是一个关于台北家庭的故事。
男主人公简南俊,人到中年,是一个事业小成的生意人。他和太太敏敏、女儿婷婷、儿子洋洋以及外婆,生活在一起。
和很多中国家庭一样,简家也过着平平淡淡的日子,生活中能算得上大事儿的,也就是小舅子的婚礼了。
电影最开始的场景就是小舅子阿弟的婚礼,而婚礼的走向也在意料之中——小舅子的旧情人大闹了婚礼现场。
这仅仅是故事的开始。紧接着在婚礼的同一天,外婆下楼倒垃圾时中风昏迷,被送去医院,这个平淡的家庭顿时陷入了混乱。

女儿婷婷深感内疚,她觉得是因为自己忘记了倒垃圾,才导致外婆中了风。简太太敏敏,在照顾外婆的过程中,发现自己的生活每天都在重复,“我觉得我好像白活了”,最后上山住进了寺庙。
七岁的儿子洋洋每天都在追问各种为什么,后来在简南俊的建议下,他学会了用相机拍摄人的后脑勺。
简南俊自己也偶然遇到了当年的初恋情人,趁到日本出差时,他们见了面,也叙了叙旧。
影片结束于外婆的葬礼。葬礼上,洋洋念了一段写给外婆的话:
婆婆,对不起,不是我不喜欢跟你讲话,只是我觉得我能跟你讲的,你一定老早就知道了。不然,你就不会每次都叫我“听话”。就像他们都说你走了,你也没有告诉我你去了哪里,所以,我觉得,那一定是我们都知道的地方。
婆婆,我不知道的事情太多了,所以,你知道我以后想做什么吗?我要去告诉别人他们不知道的事情,给别人看他们看不到的东西。我想,这样一定天天都很好玩。说不定,有一天,我会发现你到底去了哪里。到时候,我可不可以跟大家讲,找大家一起过来看你呢?
婆婆,我好想你,尤其是我看到那个还没有名字的小表弟,就会想起,你常跟我说,你老了。我很想跟他说,我也觉得,我老了。

《一一》拍出了生活的无意义
影片名字《一一》历来议论颇多。
一种说法是,杨德昌参考了《老子》里“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那么《一一》讲的就是一种人物和事件之间的因果关系。
但另外一种说法是,在中文里,“一”还可以表示 “每一” 或者是 “全部”,所谓《一一》指的就是所有:它讲出了生活中那种让人哀伤的相似,你以为你是独特的,其实只不过是全部中的每一个。所以有人看完了这部电影之后说,“像活完了一辈子”。
另一方面,《一一》的英文名《A One and a Two》似乎通俗了些,却也饱沾着一份禅意。
在世界电影的序列里,《一一》一直以来都是一部重要的作品。
2000年在法国上映后,法国的《巴黎世界报》认为:影片以敏锐而温热的镜头,进行了社会心理分析,为社会百态及人性的枷锁做出了见证。
《纽约时报》更是献上了罕见的感性评价:这部电影是一位大师完全掌握并支配了他的艺术资源的杰作,我泪眼模糊地看着片尾字幕,挣扎着去形容那股深深感动我又扯碎我的力量。是哀伤?喜悦?欢乐?是的,我想都是。不过最大的感受是感激。
美国的《时代》周刊更是将《一一》列入了2000年度的十佳电影行列。
对于华语电影而言,《一一》的重要性更是毋庸置疑,它是那种无数电影人羡慕,却无法拍摄出来的电影。
贾樟柯就曾经这样感叹:杨德昌的这部杰作平实地写出了生之压力,甚至让我感觉到了疲惫的喘息。
而对于广大观众来说,《一一》这部电影里什么都有,有如水一般平淡的日常,有如利石一般坚硬的生活,有偶尔的小欣喜,也有经常性的茫然无措,它拍出了人生拥挤深处的空旷、繁忙过后的空落和盛大之下的无聊。

很多年后,李安也说了类似的话:老师教育我们,觉得人生没有意义,所以我们要找到意义,意义是一个很大的概念,很人为的一个概念。其实这是一个安慰人的东西。所以我们拍电影,就是在寻找意义,寻找意义的本质是它没有意义。
《一一》因为拍出了生活的无意义,而变得有意义。
跳开一个距离,像写论文一样拍电影
对于导演杨德昌而言,《一一》也是他个人最成熟的一部作品。杨德昌的好友,导演陈国富曾说,他“是一个永远在思考却苦于表达的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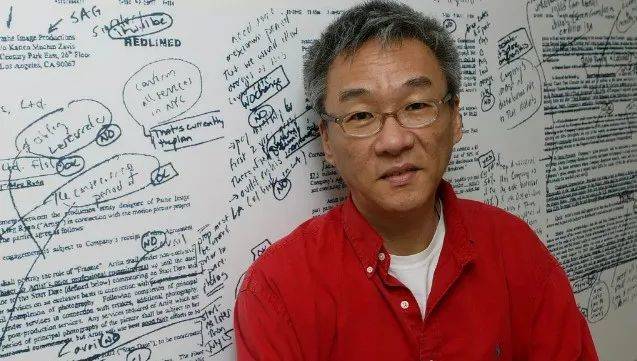
在杨德昌之前的电影作品里,《麻将》怒气太重,就像影片里的那句台词:现在的世界没有人真正知道自己想要什么,而是要别人来告诉他该怎么做。
《恐怖分子》则飘荡着一股戾气,整部电影都像李立群饰演的李立中说的那样:我也想一枪崩了那狗男女,狗领导,可是什么都做不了。
在这里,戾气不是力量,而是一种深深的无力感。
就连和《一一》双峰并峙的《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也会偶尔闪现出杨德昌意气用事的火苗,进而造成主题上的片刻失焦,比如,影片中冗长的小猫王部分。
《一一》则更像是杨德昌——1983年的《海滩的一天》、1985年的《青梅竹马》、1986年的《恐怖分子》、1991年的《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1994年的《独立时代》和1996年的《麻将》——这七部以往作品的集大成之作。
在《一一》中,我们能看到,杨德昌仍然是台湾社会的手术刀,但他已经学会了“跳开一个距离,观察、理解整体社会状态之后,做出综合评述。先创造出一种理念,再填入细节。他是在写论文,而非描述。”
于是,无论对于台湾电影还是杨德昌本人,《一一》都变成了一部完全不一样的电影,仿佛它一夜之间茅塞顿开,有了四通八达的通透和笃定。
可惜的是,台湾电影并没有因为受到《一一》的照明作用,而获得创作上的启发。《一一》之后,台湾电影仍然凭借着本能在横冲直撞。

也许能制作出超越《一一》的作品的人,只能是导演杨德昌本人了。
但2007年6月29日,导演杨德昌逝世,《一一》彻底成为一闪的灵光,唯有光芒闪耀,而再无超越光芒的可能了。
城市电影
在我看来,对《一一》进行各种角度、各种力度的赞美,都不为过。但在那么多的赞美中,它更深刻的意义并没有被提及——《一一》是21世纪华语电影中罕见的城市电影。
21世纪,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由乡村向城镇转变的过渡期。
相应地,21世纪的很多华语电影杰作,也都因为捕捉到了这种乡村与城镇之间的冲撞而永载电影史册,比如贾樟柯的《站台》和侯孝贤的《风柜来的人》。
也正是因为处于这个过渡期,中国的城市电影,更像是被简单地替换为故事发生在城市里的电影,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城市电影。
对于一个国家的电影工业和电影文化来说,城市电影意味着无限的可能。如果我们能够简单粗暴地认为,美国的西部片就是美国的农村电影的话,那么后来的黑帮片就是美国城市电影的雏形。
农村电影因为与自然的亲密关系,不具备裂变的可能,这也是美国电影西部片时代,只有西部片一家独大的原因。
而城市电影因为城市的丰富性,可以同时寄居无数种关系,黑帮片很快就裂变为爱情片、警匪片等等。也就是说,一个国家的电影,只有进入城市化阶段,才有可能迎来产业上的无限可能。
可惜的是,《一一》之后,中国的城市电影一闪即逝。
一方面,中国电影的城市化进程远远跟不上现实中国的城镇化进程;另一方面,在现实的中国城市里,人们也没有建立起真正意义上的城市文明,仍然顽强地保留着乡村的生活习惯。
这样一来,城市电影的体系就很难成型。于是我们经常看到,那些以城市为主要生活场景的电影,仍然采取非城市的逻辑来推进叙事。这也是目前很多以城市为背景的电影,一直弥漫着一层土腥味儿的原因。
城市空间重塑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城市电影是以城市为事发地,但更是以城市聚合为故事发展的逻辑,进而重新剪辑了人物关系,重新架构了故事形态。
《一一》的力量,源发于城市这个空间。
故事仍然是中国人的家长里短、生老病死,出现了婚礼、满月和葬礼,这三个仪式感最强的人生节点。但在城市这个空间里,人物关系、故事走向已经有了新的秩序。

乡村是空旷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没有那么局促,关系的折射物大都来自于自然,如星辰对方向的指引、四季轮转对时间的提示,人类的双脚还踩在土地上,对万物的感知是由下而上的,更接近本能。
城市最大的特点,则是一切的人工化,空间被人为改造重组后,时间随之发生扭曲,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出现了溶解、失效和某一部分的刺激性生长。这种变化导致人和人之间产生隔阂,无论是居住在楼房,还是为道路铺上柏油,都泄露着潜藏的信任危机。
但杨德昌似乎持有不同的观点,他曾说:
常常有人会感觉到现代社会是非常疏离的,我最近领悟到,这样的感觉是和农业社会比较得来的。过去的生活形态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较为单纯友善。
我一直在思考,现代社会中是否可能发展出早期农业社会那种人际关系,然后我发现这并不是不可能的,相反的,都市可以是一个发展更好、更亲密的人际关系的地方。
城市的疏离
在《一一》里,杨德昌通过对空间的塑造完成了电影的城市化。
杨德昌一直对建筑设计感兴趣,这使得他对空间更敏感,塑造特定空间的时候也更自如。
他曾谈及建筑设计对他写作剧本的影响:
我很早就对建筑有兴趣,后来也了解到,设计就是要满足一种需要,或者是去创造一个功能,创造一个空间。
这个道理同样可以用在编剧上。我们有时候会觉得戏剧张力弱,就是因为有个功能没有被满足,或是编剧没有看到那个功能是必要的。
张力断了之后,即使很短的事情都会让观众觉得很长。这其实跟建筑、跟设计师设计一座桥非常类似。
《一一》之所以是一部真正意义上的城市电影,就在于导演塑造了一个属于城市的空间。
杨德昌对城市空间的理解,首先是一种疏离感。
因此,《一一》的镜头大都采用中远景,制造出一种旁观的效果。但导演没有就此罢手,在中远景镜头之外,他还采用了隔着物品拍摄的方式。

比如,婷婷和外婆走进公寓的画面,是通过公寓的监控画面呈现的。而小舅子和前女友谈判时,镜头则放在作为谈判地点的餐厅的窗外:隔着一道玻璃,两人谈话的细节,被距离处理掉了,只剩下谈话的姿势。
后来,小舅子的孩子出生,他也是隔着玻璃望着那个小小的新生命,像隔着一代人的时间。
但距离之远不是城市的空间要点,杨德昌懂得城市的心理距离和物理距离之间的关系。他在塑造距离之远的同时,也塑造了距离之近。
距离之远,他用镜头和城市里无处不在的物体共同完成;距离之近,靠的则是对声音的重塑。比如简南俊坐在远处的车里和别人说话一幕,车窗紧闭,但声音却如在耳畔般清晰。
杨德昌没有遵循已知的物理定律,他重新发现的定律是他对城市的感受:耳边都是清晰的人的说话声,说的都是彼此能听得懂的语言,但抬眼望去都是陌生人,说的都是不知道从何而起、也不知道去向何方的零碎符号。

后脑勺
在影片里,7岁的洋洋问爸爸:我们是不是只能知道一半的事情?我们只能看到前面,看不到后面,这样不就有一半的事情看不到了吗?
后来洋洋只拍人的后脑勺,就连《一一》的影片海报也只是简洋洋的一个背影,后脑勺占据了大半。
镜头外的杨德昌就是镜头里的洋洋:在电影里,洋洋拍摄人的后脑勺,帮助人们看到那一半看不到的事情;杨德昌通过《一一》这部电影,也让人看到了自己的后脑勺。

贾樟柯就说,杨德昌在《一一》里找到了观察中国社会非常重要的钥匙,通过中国人特有的侵入他人生活的亲密的人际连接,呈现了在运动着的、发着热的人际关系中,原来埋藏着感情上的冰冷。
尤其奇妙的是,杨德昌为人工的城市节奏,找到了自然的韵律,这种韵律感通过片名《一一》,通过片中人物的名字——敏敏、婷婷、洋洋——渗透出来。以致于影片在法国上映时,片名直接就使用了拼音 “YiYi”。

尾声
在结束这篇文章之前,让我们回到1977年。那一年杨德昌30岁,他在华盛顿大学当一名电脑工程师。
杨德昌在下班回家的路上,被沃纳·赫尔佐格的《阿基尔:上帝的愤怒》的电影海报吸引,就进去电影院渡过了改变他人生的两个小时。
从电影院出来,他决定放弃当时的电脑工程师职业,去拍摄一部像《阿基尔:上帝的愤怒》一样,“电影该有的样子”的电影。
自此,华语影坛多了一位大师,华语电影史里,也出现了一部真正意义上的城市电影《一一》。
杨德昌拍出的是一部“已经跨越了地域和时间的藩篱,成为无论从哪一面攀登顶峰的登山者都要依赖的指向标”。

“拍完《一一》,他整个人都改变了,比以前沉静了很多。”
七年后,杨德昌病逝。这中间他再也没拍电影。《一一》,成为他的最后一部作品。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看理想(ID:ikanlixiang),作者:阿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