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扫码打开虎嗅APP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神经现实(ID:neureality),作者:Catherine Offord,译者:航迹云,审校/编辑:Orange Soda,原文标题:《造梦工程》,头图来自:《盗梦空间》剧照截图
亚当·哈尔·霍沃兹(Adam Haar Horowitz)觉得对即将入睡的陌生人耳语似乎真的有些诡异——他是第一个这么承认的人。早在几年前,他就在思考如何影响人入睡前夕所看到的类似梦境的画面,这种类梦境状态叫做临睡幻境(hypnagogia),他当时和在麻省理工学院读硕士的一名叫做伊斯汗·格鲁弗式(Ishaan Grover)的学生一直琢磨着这个想法。
这对搭档想知道,如果对处于临睡幻境的人低声耳语一些字句,这样做是否会影响他们入睡前脑海里的想法和画面。这种研究方式可以用于探究人类的认知,最终还可以帮助人们掌控自己大脑的梦境。
哈尔·霍沃兹并没有真的去对陌生人耳语;他和格鲁弗式还有他们的合作团队采用了一个更实际的办法来实现他们的核心想法:用一个能放进人手心的设备来监测人体心率变化、肌肉张力和皮肤电导率(这些设备可以帮助研究员确定佩戴者即将入睡的时刻),再将这些数据和电脑或智能手机的软件配对,让它们自动播放语音提示并记录人声反应。
哈尔·霍沃兹说道:“这个软件会在检测到佩戴者临睡幻境结束之际,在他们进入更深的睡眠之前,对佩戴者耳语。”研究者要求那些佩戴者报告完自己当时在想什么,接着他们重新开始准备入睡,重复这整个过程。
在哈尔·霍沃兹的硕士论文和今年初发表的科学论文中,他描述了这个实验的具体细节:在实验中,人们可以轻松地和这个名为多米欧(Dormio)的设备进行交互。尽管毫无意义,人们和多米欧聊着他们在清醒状态边缘游走时能看到和感受到的东西。
根据哈尔·霍沃兹的论文,一名被多米欧暗示去想象叉子的志愿者,描述他梦到了一个家庭,“这个家庭因看到叉子而感到高兴,然后他们把这个叉子放进了一个南瓜里”。另一名被暗示去想象树的参与者描述道“一棵来自我童年的、后院的树,它从没要求过任何事”。
和《科学家》期刊交流过的梦研究者们说,这个领域曾因科学家不能和被试者交互而受限,多米欧让这个领域跨出了令人兴奋的一步。很多专家认为睡眠时人类的任何主观感受都可以定义为梦——虽然大部分的研究课题都依赖于将被试从快速眼动(rapid-eye movement,REM)睡眠中唤醒,然后收集他们对梦的描述。
在REM睡眠期间的睡眠里,人们多半正经历着感性的、有故事的梦(虽然这并不是唯一一个能产生梦境的睡眠阶段,请见下文“梦的几个阶段”)。这个耗时的方法一直阻碍着想要操控梦的研究者——操控梦是研究梦的重要一环,现MIT媒体实验室的流体界面研究组研究助理哈尔·霍沃兹如此认为。他说,“毕竟,如果不能控制梦,你就无法用可控的实验来研究梦了。”

和亚当·哈尔·霍沃兹(左)一起开发多米欧的(左起)伊斯汗·格鲁弗式、奥斯卡·罗塞罗(Oscar Rosello)及佩德罗·雷诺兹·奎利亚尔(Pedro Reynolds-Cuéllar)。其他队员有艾比楠丹·贾恩(Abhinandan Jain),托马斯·维嘉·加维斯(Tomas Vega Galvez),艾亚勒·佩里(Eyal Perry),马修·哈(Matthew Ha),凯瑟琳·伊斯法罕(Kathleen Esfahany),克里斯蒂娜·陈(Christina Chen)
哈尔·霍沃兹是一群规模小但正在壮大的研究者里的一员,这些人称自己为梦工程师,他们探索各种能影响人们在睡眠前夕以及睡梦中的思想的方法。一些技术像多米欧一样使用听觉刺激,另一些则利用视觉或嗅觉,或是运用更复杂的科技,例如非侵入式脑刺激。
靠着近期研究中此类技术所展现出的前景,神经科学家和心理学家们或许不仅能更深入地了解产生梦的机理和原因,还能推进梦境控制带来健康和认知方面的应用。这样的技术能帮助赋予梦研究者们想要的控制力,哈尔·霍沃兹的导师及合作人,哈佛医学院的梦研究者罗伯特·斯蒂格尔德(Robert Stickgold)这样说道,通过这些方法,“我们就能用科学方法了。”
清醒梦和其他梦境体验
试图影响梦境绝不是什么新鲜事。人们认为早在古埃及,就有人能快速引导生动的梦,但与此同时,科学家、哲学家和艺术家们花了几百年,一直通过印度大麻、鸦片和其他药物来催生入睡和睡醒时的梦境。
许多文化还相信某些特定的食物有改变梦的效果——一些西方社会的民谣认为奶酪能引导生动的梦,虽然并没有太多科学研究对这方面问题进行探讨。而且在过去几年里,对清醒梦引导课程的需求在大大提升,这类课程是为帮助人们控制自己梦境而设计的,这样的需求是拜克里斯多弗·诺兰(Christopher Nolan)轰动2010年的、关于梦境意识扭曲的电影《盗梦空间》所赐。
梦工程师的兴趣在于找到可靠的、由研究者控制的办法来引导清醒梦,这是一种做梦者知道自己身处梦境的状态:在这个状态里,做梦者有可能可以掌控他们的行为和周遭的环境,以及其他感觉(例如飞翔)。
梦工程师希望通过引导清醒梦来研究这些感觉的产生机理以及它们对做梦者来说是否存在用处。非侵入式脑刺激就是其中一种备受关注的操控梦境感知的方法,它利用磁力圈或在头皮上安装电极来影响做梦者大脑的电活动。
2013年的一项小研究里,研究者对处于REM睡眠期的被试者们进行了10分钟的经颅直流脑刺激(transcranial direct current stimulation,tDCS),基于被试者从REM睡眠里被叫醒后的描述,结果表明该脑刺激相对于对照组的虚假实验,能增强梦境的清醒度。
接着在后一年一个相似的实验里,被试者接受虚假的实验处理*或是经颅交流电脑刺激(tACS)——一个被认为比tDCS能更好影响脑振波的技术——得到的结论是,在REM睡眠期用40HZ的交流电刺激大脑也能让做梦者在梦里变得更有自我意识。
然而,两个研究的效应都较弱,而且2013年的那个研究还只征集了本来就说自己经常经历清醒梦的被试群体。这样的群体很难代表普遍群体,因为据研究者估算,50%的普通群体也许从不会有清醒梦的经历。(译者注:接受虚假的实验处理的被试作为对照组,佩戴与实验组相同的仪器但实际上并没有接受脑刺激,这样能排除因实验程序不同而影响实验结果的因素。)
在蒙特利尔大学睡眠医疗高级研究中心(The University of Montreal’s Tore Nielsen),指导梦与噩梦实验室的托尔·尼尔森(Tore Nielsen),并不相信非侵入式脑刺激能引导清醒梦。尼尔森说自己和许多梦研究者一样,经历过很多清醒梦和非同寻常的梦。
他和他的同事们最近在非常严格的实验条件下实行了他们的tACS实验:为了让研究者能确认做梦者有如实汇报自己的清醒梦,做梦者必须在开始做清醒梦时给出信号——快速地从左到右闭着眼皮动弹眼睛三下——而且是在REM睡眠阶段下动弹,脑电图会通过脑活动判定他们是否处于REM睡眠期。
“非常遗憾的是我们并没能重复之前研究的结果”,尼尔森说道。尽管一些被试者能在REM睡眠期给出眼动信号,并在那之后能描述做过的生动的梦,但是接受过tACS的被试者并没有比接受虚假实验更容易做清醒梦。

非侵入式脑刺激在操控梦方面也许有着其他作用,尤其可以帮助我们研究不同脑区在产生常见梦境体验的时候,是如何作用的。例如来自伦敦王后玛丽大学的法尔达斯·诺瑞卡(Valdas Noreika)一行人,最近用一系列10分钟的tDCS实验区段,在10个志愿者的REM睡眠期里扰乱他们的感觉动作皮层的活动。
每个实验区段后,研究者都马上将志愿者从REM睡眠中唤醒,让他们填写问卷描述梦到的东西——尤其关注他们是否有举东西或是行走之类的动作。结果表明接受tDCS的志愿者在梦里比接受虚假实验的志愿者体验到了更少的动作,这说明正常的感知运动皮层的活动对这类梦的感知是必不可少的,诺瑞卡说。更确切地说,“我们发现感知运动皮层负责梦里的重复性动作,例如行走、跑步和游泳。”
一些更简单的科技也可能有操控梦境体验的功能。在尼尔森实验室完成了博士学业的米歇尔·卡尔(Michelle Carr),现在已是罗切菲特大学的一名博士后,他一直用科技在实验室尝试让做梦者在梦中产生自我意识。她发现了一种激发清醒梦的有效途径,那就是通过行为训练教导人将强化的自我意识和一些感觉刺激(可以是光或者是声音)联系起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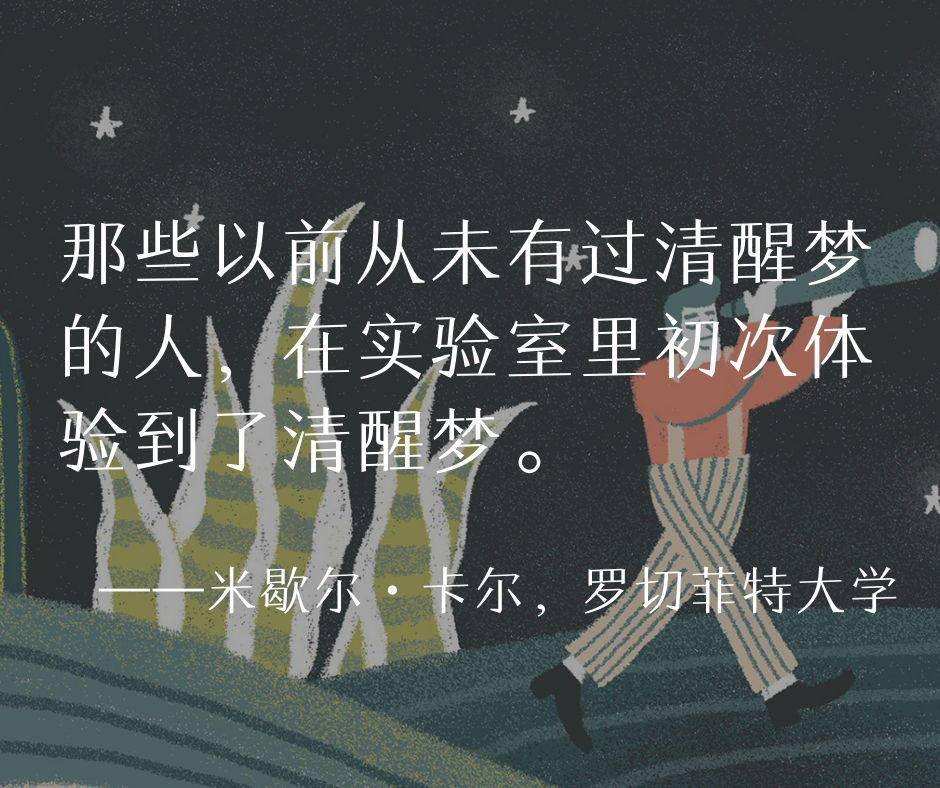
例如在近期一个研究里,卡尔等人训练清醒的志愿者们,在看到研究员给他们呈现的变化的闪烁的红LED光或是“哔”的一声噪音时,要格外地注意周围环境。参与者们在训练后,有90分钟的时间在实验室里睡着,与此同时,研究员们用脑电图和肌肉电活动等技术监测他们的睡眠阶段。
当参与者进入REM睡眠时,实验员就激发出和训练时同样变化规律的LED光和声音信号。研究者监测通用的眼动信号,将被试从短周期小睡中唤醒并记录他们的睡眠报告,并在被试的90分钟睡眠过后发放调查问卷;该研究团队发现,相对于在整个过程中没有接受光或声音刺激的17%的参与者而言,大约50%的实验组人员都经历了清醒梦。“有些参与者出现了8次被感觉信号激发的反应,实在是太酷了。”卡尔说,“有些从未有过清醒梦的人,在实验室里初次体验了清醒梦。”
虽然这个研究还处于早期阶段,卡尔希望他们的发现能够激励那些未来想要在梦里激发特定感官的研究,并更深入地挖掘其潜在益处。她和同事们最近分析了20个人在一周里记录的关于梦和心情的日记,他们发现清醒梦越强烈,第二天醒来后的心情越好。
卡尔说研究员们想用他们引导清醒梦的技术来探究这两者之间是否有因果关系,以及引导清醒梦是否有其他的应用,例如帮助被近期噩梦困扰的人——这是焦虑症和创伤后应激障碍等心理疾病中常见的病症。卡尔说,“如果我们能可靠地激发这些清醒梦,那我们就能将它们用在有益的地方。”
特定内容的梦境养成
对某些梦研究者而言,值得操控的并不只有做梦这个体验,还有梦里特定的内容。很多古老的人类文明也尝试实验过这个想法,例如有记载试图引导梦里遇见各种神明的故事。但对于来自哈佛的斯蒂格尔德来说,是1990年一趟去夫蒙特州的家庭旅行让他萌生了这个想法。
斯蒂格尔德在绿山区驼峰山徒步后的那天晚上睡着时,很惊讶地感到自己似乎在吃力地向山的一侧攀爬,就像他这天早些时候所经历的一样,他的手掌清晰地感受到那个石壁独特的触感。醒来后再次睡着时,他发现自己好几次都能在进入更深的睡眠前找回这种感受。斯蒂格尔德说,他被这种体验激发着,想知道如何能在实验里捕捉它。
斯蒂格尔面临的一个阻碍是:带着一群本科生去攀岩徒步,就为了观察他们是否会梦到攀岩的经历,这种理由很难通过伦理和审查机构的考核。没几年过后,另一种办法出现了。“我正在和一群学生开会,生气地抱怨着我永远不能实现这么好的实验”,斯蒂格尔德说,“其中一个在场的学生就说,‘那玩俄罗斯方块怎么样?’他们接下来告诉我刚开始玩俄罗斯方块的时候就是这样的:你会看到那些方块在你眼前一块块地落下。”
这段谈话成为了一颗种子,成就了之后的研究梦的一个著名实验。斯蒂格尔德一行人招募了27个人,其中10人是玩俄罗斯方块的高手,12人是新手,还有5个人因大脑损伤而有记忆缺陷——这些人在3天里玩了7小时的俄罗斯方块。
在每晚开始的一个小时里,在入睡和睡醒时,参与者(要么被实验员,要么被一个电子音提示)将自己当时所想记录到一个微型卡式录音机里,或是讲述给一个实验员。几乎2/3的参与者都汇报自己在入睡初期有看到类似梦一样的俄罗斯方块的画面,而且在5个有记忆缺陷的参与者里,3人说自己看到了俄罗斯方块的画面,尽管他们根本不记得自己有玩过这个游戏。
其中一人描述道“就像是小方块们从屏幕上掉下来一样,然后我尝试着把它们放到该放的地方”,另外的人则说他们会看到“翻转着的图像”。“我不知道它们从何而来,我希望我能想起来,但是它们看起来像是砖块”。几个高手玩家说他们不仅想到了他们在实验里玩的俄罗斯方块,还想到了他们以前玩过的一个老版本。
激发大脑去产生一些特定的内容——一种叫做梦境养成的伎俩——已被计算机和虚拟现实技术证明拥有惊人的可行性。依琳·沃姆斯利(Erin Wamsley)曾在斯蒂格尔德实验组做博士后,现在南加州的弗曼大学有了自己的实验室,他说很多研究者都默认梦更容易被比较激烈的经历影响。
“你可以给一个人看一些恐怖的图像或是令人不安的,有着激烈情感色彩的,观影者也承认是令人不安或是情感强烈的电影。”沃姆斯利说,“但这些并不一定是激发人们梦到这些经历的直接因素。另一方面,我们已有很多次成功地引导了参与者梦到他们新的学习经历。”现在,沃姆斯利正在研究是什么决定着被试将经历融入到梦里的方式。

2010年,斯蒂格尔德和沃姆斯利等人招募了43名志愿者来玩一个叫做阿尔卑斯竞速者的滑雪电玩游戏。在游戏结束后的第二晚,被从NREM睡眠里叫醒的被试者里,近1/3的梦境汇报都与这个游戏有关。
虽然梦的性质随着人们进入更深度的睡眠而改变着,从“我看到了那个游戏的闪回画面,那个虚拟现实的滑雪游戏”的典型汇报,到较为模糊的和滑雪有关的回忆,例如”这一次我在想象层层叠叠的树丛,我感觉自己好像在一个,似乎是5年前曾经去过的滑雪胜地滑雪。”
在过去的几年里,他们还通过让被试者在电脑里做一个简单的迷宫导航任务,来探索特定内容是怎样被植入到不同睡眠阶段的梦里的。例如有个刚入睡的人的梦境汇报里出现了关于在迷宫上方游泳的想法,另一个被从REM睡眠期叫醒的参与者汇报梦到自己走完了迷宫。从NREM睡眠中被唤醒后的一种典型汇报,是做梦者站在迷宫中心,等待着一个朋友去找到他。
包括上述研究在内的其他许多研究都表明,将任务内容植入梦境和睡醒后的任务执行表现之间有关系——这个发现进一步证明了一个较为盛行的观点:该观点认为睡眠,也许更特定地说,做梦,在记忆巩固上有着重要的作用。
基于当下的证据,还不清楚到底是做梦在起这个巩固作用,还是也许它只是这个巩固过程的一种映射或是副产品。斯蒂格尔德,和共同作者安托尼奥·扎德拉(Antonio Zadra)在一本名为《当大脑在做梦》的新书里探讨了做梦的各种理论,他们提出了一个假设,认为REM睡眠有利于巩固情感丰富的回忆,以及从近期经历里提取特征;而且也许临睡幻境里的似梦画面是大脑标注相关内容的方式,以便之后睡眠周期进行处理。其他的研究者认为做梦另有其用——一些科学家认为梦是在模拟做梦者现实生活中也许会遇到的潜在危险和社交情景——或者可以说梦根本没有任何功能,诺瑞卡就是这些人中的一员。
哈尔·霍沃兹指出,像多米欧这样能影响梦境的科技所探究的一个关键问题,就是梦的潜在功能以及梦境内容。他说道,相比于传统的对梦的研究来说,多米欧与做梦者实时交互的能力使研究者可以更为轻易地收集数据,尽管临睡幻境和REM睡眠并不能完全等同。他最近已经发起了几个合作,合作者不仅包括对改变梦境内容会如何改变记忆与学习好奇的睡眠科学家,还有对梦境养成会怎样提升他们的创造力感兴趣的艺术家和哲学家们。
让梦工程成为主流
卡尔,哈尔·霍沃兹等人去年在MIT的工程师和梦研究者间组织了一个研讨会,以探讨领域内可用的科技;该团队还于2020年暑假,在《意识与认知》期刊上写了一个关于梦工程的特别篇。“那个研讨会带来了很多合作。”负责管理特别篇特邀编辑嘉宾的卡尔说道,“我觉得这将开启一个新篇章。”
在这个势头下,梦研究者们有希望攻克睡眠科学里一个迟迟未解决的问题。就算是现在,“很多人还是认为梦研究是一个边缘话题,像是在研究超感(extrasensory percpetionp,ESP)或是离体体验一样。”沃姆斯利说,“当然了,依我看来,梦研究和那些完全不是一回事。在我们的梦研究里,我们把研究梦境看作是理解心智和大脑在睡眠里的作用的一种方法。”
不管怎样,自我描述的梦境的主观性仍然是一个问题,她承认道。她说,虽然试图用功能性核磁共振此类脑成像技术来预测梦境的神经科学家们,在过去几年里迈出了很大一步,但要让成像结果能与做梦者自己的描述细节匹配,研究者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一些研究梦工程的团队已经了解到了这个阻碍,他们正致力于证明将收集梦境汇报作为常规睡眠研究一部分的价值和可行性。

例如在近期一个研究里,来自弗里堡大学的毕约恩·拉什(Björn Rasch)实验组的研究员训练被试者做一个文字和图片的结合任务,然后在晚上叫醒他们让他们汇报梦境。这个团队发现,被试者第二天早上对于任务的记忆似乎并没有受前一晚被叫醒这一过程本身的影响。
研究者还表示在NREM睡眠期间梦到任务,和第二天早晨的记忆表现成正相关,但他们发现在REM睡眠期做梦就没有和记忆表现有关系——这个关于睡眠影响记忆的线索,要是没有梦境汇报的收集,就一定会被人忽视。
梦研究者们也还在期待着对于操控梦中人意识的一些非同凡响的解读。MIT媒体实验室流体界面组的领头人,同时是《意识与认知》里一篇该领域的综述的共同作者,计算机科学家帕蒂·梅斯(Pattie Maes)指出,有了像多米欧这样,能让人们与自己或他人的梦境交互的设备,伦理方面的考虑“才是重头戏”。
斯蒂格尔德同意这一观点并指出,即便解读半梦半醒的人的意识这一领域已被研究了数十年,仍有独特的甚至尚未盖棺定论的东西。“这简直细思恐极”,他说,“我们正在触及人们睡眠时的意识这一我们或他们自己都无法控制的领域。我们就像是偷窥者,窥视着他们的意识要做什么。”
原文:https://www.the-scientist.com/features/scientists-engineer-dreams-to-understand-the-sleeping-brain-68170,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神经现实(ID:neureality),作者:Catherine Offord,译者:航迹云,审校/编辑:Orange Sod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