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扫码打开虎嗅APP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信睿周报 (ID:TheThinker_CITIC),原载于《信睿周报》第80期,作者:黄剑波(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头图来自:《美丽人生》剧照
风险社会被认为是理解现代社会的一个关键特征,过去两年多的新冠疫情全球大流行无疑给这个论断提供了海量的论据。对很多人来说,疫情之所以被认为是一场巨大灾难,不仅因为它带来了病痛、死亡和与之相关的恐惧,还在于它打乱了人们的生活节奏和秩序,而这些都淋漓尽致地展现了现代社会的不确定性。
对人类学研究来说,风险不仅是一个现代性问题或一个可测量的客观事实,它也体现了人类对风险感知的长期需要。在玛丽 · 道格拉斯(Mary Douglas)看来,风险的存在和感知在根本上是人类的问题,它不仅是一种外在的客观实存,更是一种内在的主观感知,并在很大程度上来源于个人对于整全状态或正当秩序的类别性理解,而这种理解往往源于某些刻板的先入之见。
从风险的主观性向度出发来看今天这个充斥着病痛和恐惧的时代,我觉得有必要澄清这样一个事实:我们都是生活在残缺世界中的残缺个体。

风险的接受:社会科学的视角
玛丽·道格拉斯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薄荷实验,2022
当下的医学研究已经注意到,整全与残缺之间并非界限分明,个体和世界的整全状态本身就难以企及。残缺和痛苦不仅是切实存在的,更是需要被感知和理解的。然而当下的我们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感知和理解外界苦痛的能力,变得麻木了。
因此,理解个体和世界的残缺,关键在于找回痛感。同样地,只有尝试去感知和理解他者的苦难和痛感,人类学才有可能真正回应这一时代乃至所有世代的根本问题,做出有知识冲击力、有价值的研究。
作为普通人,我认为找回痛感是必要的。痛感的消失不是说人们没有痛苦了,恰恰相反,它意味着越来越多的个人或者地方性的痛苦无法被外面的世界所理解,无法被准确、清晰地传导和感知。
在很多文化中,麻风病曾被视为最恐怖的病痛,除了传染性,它最为恐怖的一点在于它会让人在麻木当中失去身体的一部分(感染者的皮肤、肌肉、骨骼会慢慢失去感觉,病情达到一定程度,手指甚至可能脱落),甚至是全部的生命。它意味着,身体的消失可能是毫无征兆和感觉的,人的苦难失去了被感知的可能。更可怕的是,人们对麻风病患者身体痛苦的忽略甚至遮蔽,造成了一种更加深刻的无助感。
不仅是麻风病,对他者任何身心苦难的忽略,都会带来更糟糕的结果:个体因为愈发孤立的境况而无法言说自身的苦痛。这种无法言说的痛苦才是最为深刻的,因为它意味着个人不仅面临着诸多苦难,而且这种个体性的痛苦还是被这个世界忽略甚至遮蔽的——这种忽略和遮蔽本身是一种对苦难者更深层的伤害。因此,只有找回痛感,我们才能更加清晰、准确地体察他者的痛苦,并且令人欣慰的是,通过此种努力,我们也将得以摆脱那些无法言说之痛,在同他人的联结中得到更多理解。
作为学者,我认为也需要找回痛感。它的意义在于,重新定位研究者的深度关怀,努力思索和寻找你真正关心和在意的问题,而不是为了成为某些话语的附属物,为了论证已有的结论或仅仅回应某个学术团体的问题。
一个重要的研究问题应该源于这个世界对你内心深处的触动,你想要去理解和感知这个世界面临的问题和苦难,想要通过更加准确、清晰地传导这个世界的残缺之处,为人们理解和感知他者带来更多可期的联结。找回痛感,找回你对这个世界的关怀和期待,这才是一个学者应有的问题意识。

Light in Dark Times: The Human Search for Meaning
Alisse Waterston
Illustrated by Charlotte Corden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2020
当下世界的痛感:焦虑、恐惧与倦怠
那么,今天这个残缺的世界又有哪些痛苦需要被感知和理解呢?
如果说“9 · 11”事件对于20年前的欧美世界影响深远,那么 2020年初暴发的新冠肺炎疫情对今天的全球而言更是如此。它给我们带来的首先是COVID-19病毒,它会对人类的身体造成冲击,加速基础疾病的暴发。这个病毒极强的传染性和致病能力使我们活在极大的焦虑和恐惧之中。而除了疾病本身,还有死亡的可能,尽管病毒的致死率并不高,但人们仍会感受到巨大的恐惧和不确定性,这些都加深了我们对于风险社会的判断和认识。
如果说风险社会是社会学家关于现代社会的精彩判断,那么人类学家为风险社会或者现代性问题作出的贡献或许在于提出了:疫情不仅带来了疾病和死亡,更重要的是,它还带来了对于疾病和死亡的恐惧,一种巨大的不确定性,这正是现代风险社会的一个基本特征。
不确定性不仅涉及对疾病和死亡的恐惧,还有关时间悬置(temporality)的感受。对密切接触者的7天、14天或21天隔离政策,打乱了很多人的时间安排,任何计划都变得非常脆弱。很多人都喜欢确定和稳定的生活,一旦计划被打乱,种种时间安排和规划就会被悬置,这会给人带来不安。
而除了不安,时间悬置还会破坏我们对于时间意义的确定感。若对自己两年之前与近两年的记忆做一个比较,很多人会发现一件很有意思的事:两年之前的记忆很可能要比这两年间的记忆更加深刻和清晰。现代人可能习惯于把时间看作是匀质、等分的:一天24小时,一周7天,一年365天。事实上,时间在很多时候都被赋予了不同的意义深度,而一种混乱和模糊的记忆往往意味着意义的确定性和深度的散失。记忆的差异告诉我们,疫情不仅打乱了我们的安排,也使我们丧失了诸多关乎生活的体验和意义感。
无论是疾病、死亡以及与之相关的恐惧,还是时间悬置带来的不安和意义散失,残缺的世界必然带来残缺的状态和苦难的蔓延。世界的残缺从来如此,昨天如此,今天如此,明天大概还是如此。
《信睿周报》曾刊发过一篇对弗吉尼亚理工大学的阿什利 · 修(Ashley Shew)教授的专访。修是一位身体有残障的哲学家,她在访谈中说过这样一句话,“我们的未来,很可能就是一个‘残疾’的未来。这是我们需要认识、需要接受的”,我深受触动。(《我们的未来,很可能是一个“残疾”的未来:对话弗吉尼亚理工大学阿什利·修教授》)

弗吉尼亚理工大学技术哲学教授阿什利·修,她从自身的残障经历出发,探究身体和技术的关系。
无论是小说、电影,还是诗歌类的文学作品,在种种形式的乌托邦当中,我们的未来都被想象成一个没有残缺的、完美的未来。就算过去不完美,现在不完美,未来也能够完美。修的这句话的动人之处在于:或许那个没有残疾的未来永远不会到来。
我们以为所有的行动,无论是科技的、社会的还是政治的,都会朝着一个预定的目标前进。事实上,这些朝向理想的努力如果不能经受现实的质询,即使出于高尚的目的,贸然前行也可能造成灾难性的后果。而现实往往告诉我们:至善至美的整全,难以达至。我们需要习惯和苦难同行,因为世界和我们都不可避免地保持着残缺。
从人类学的角度来看,残缺不是一个纯粹的病理学问题,它涉及生物属性之外的文化、社会等方面。我们并不完全是身体(physical)或逻辑(logical)意义上的残缺,而是社会(social)和文化(cultural)意义上的残缺。
例如我们在过去两年多和现在正在经历的,非常直接、深刻的恐惧、焦虑。恐惧、焦虑本身表明你有所虑,有所惧,表明你是有感知的人。虽然有人可能会告诉你,这是错误的感觉,但这种感觉本身表明:你作为人,是切实存在的生命事实。正如前文所说,恐惧和焦虑还不可怕,可怕的是无所感,没有痛感——麻木。可事实上,麻木还不是最棘手的,最棘手的是倦怠(Acedia)。

倦怠社会
韩炳哲
中信出版集团,2019
倦怠代表了一种绝望的状态:对任何事物都提不起兴趣,对任何事物都漠不关心,任由自己的生命缓慢地或者快速地结束。
中世纪基督教的修道士能够通过对个人的修行或者集体性的鼓励克服很多问题,比如七宗罪,但无法克服倦怠。倦怠最大的特点在于没有盼望,最极端的倦怠会让人对任何事物都丧失兴趣,就像“低欲望社会”一样,所有感官愉悦活动都不再能够激发你的兴趣,不愿意去爬山、看电影,甚至谈恋爱。倦怠意味着,我们什么都不做,也什么都不想做,没有能力也没有欲望——我想这是今天很多人面临的问题。
人类学议题如何理解人的残缺和痛感?
在今天这样一个时代,人类学的视角让我们认识到那些生物性之外的痛感——恐惧、焦虑,甚至倦怠。除此以外,人类学议题还能为我们理解人本身提供什么呢?我认为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对个人与身体的重新聚焦,二是将人置入更大的场景。
第一个方面是过去三四十年医学人类学作出的贡献,尤其是对人和身体的重新审视。早期的医学人类学主要研究社会学的问题,关注权力、公正这些结构性的问题,后期则更多地去处理一些更深刻的关于人的问题,尤其注意到身体(包括精神)的残缺并不能否认或减少人的性质。
在生物功能上,患病者和一个相对健康的人当然不能同日而语,但在作为人的性质的意义上并无不同。当然,仅仅聚焦身体的残缺还不够,这就涉及第二个方面,即将人置于更大的场景当中来理解。
我们要贯彻整体性的人,就要把人放到更大的、更具体的场景中去理解,而不是把人视为一些抽象的概念。
我们首先要在人与人的关系中去理解人,以历史学家安玛莉 · 摩尔(Annamarie Mol)的《照护的逻辑》一书为例,当她在讲照护逻辑(logical care)时,主要的批评对象是选择逻辑(logical choice)。选择逻辑认为个体是自主和先在的,这也是过去500年来欧美传统当中对人的基本理解:人是能做选择的人。
所谓的自由(freedom)就是指 free to make choices(自由选择)。摩尔在对思想史的反思中主张照护逻辑,其中care指关系,它要求把人理解成在关系中的人,而不是可以自觉、自主做选择和决定的个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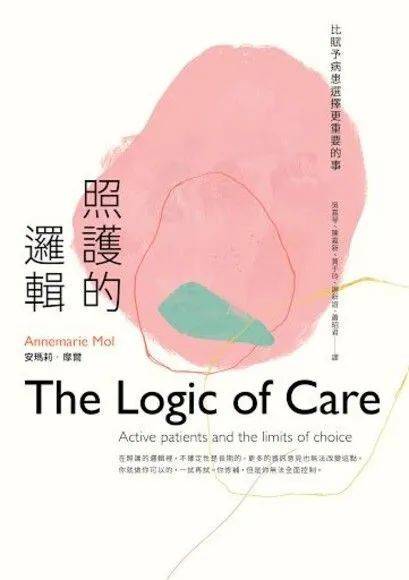
照護的邏輯:比賦予病患選擇更重要的事
安瑪莉·摩爾
左岸文化,2018
除了对人和人关系的理解,今天我们对物和非人、对“山水”的研究,都是在试图超越一个局限性的人观。乔尔 · 罗宾斯(Joel Robbins)曾发表过一篇题为Beyond the suffering subject: toward an anthropology of the good(《超越受苦主体:朝向一种关于良善的人类学》)的文章。
他认为,人类学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只关注黑暗的方面,通过“黑暗人类学”(dark anthropology)的激情来推进研究,但是现在应该更多去关注“美好生活”。其实罗宾斯想强调,人是在关系中的人,存在一种美好和良善的关系。并且,这种关系不仅仅存在于人与人的联结上,还存在于更广阔的宇宙意义上,它是一种人与人、人与物、人与非人、人与山水、人与宇宙的美好关系。
我想,人类学议题的这两个方面能够帮助我们在生活中、研究中更好地去找回这个时代的痛感。
墨西哥诗人奥克塔维奥 · 帕斯(Octavio Paz)有一首诗,我曾经和孩子一起读过,叫《诗人的墓志铭》。他写道:“他要歌唱,为了忘却,真实生活的虚伪,为了记住,虚伪生活的真实。”
好精彩!我们每个人至少都可以记录这个世界的苦难和痛苦,只要能够真诚地面对自己的写作,真诚地去与他人分享,我们就能够找回这个倦怠世界中的痛感,在感知和理解、探索和分享的过程中消除自身的苦痛和倦怠,重新找到生命的温度和力量。

墨西哥诗人奥克塔维奥 · 帕斯
如何寻找痛感:体验、附近和真实
作为学者,我们应当如何以研究来面对这个充斥着倦怠和缺乏痛感的时代呢?
第一,学者也是活生生的人,所有研究的展开都离不开自己的生活,只要是能够带给你痛感的研究,就是一项有意义的研究——或许不能保证这是一个好的研究,但它至少是有意义的。而对痛感的追寻,需要你去不断地提问:我真正关心的是什么?
今天我们很多时候过于强调一种知识层面的经验(Ergahrung),一种外部的、自然科学式的经验。但我认为,今天的人类学可以更多地去强调一种内在的体验(Erlebnis)。你到底“经历了什么” (what has been lived through), 这是德国思想家威廉 · 狄尔泰(Wilhelm Dilthey)以来的传统,即对主观内在感受的强调。体验,而非经验,是我们这个时代所缺乏的。
维特 · 特纳(Victor Turner)去世后,他生前的合作者爱德华 · 布鲁纳(Edward Bruner)帮他编了一本叫作《体验人类学》(The Anthropology of Experience)的书。在这本书的前言中,有这样一句话, “‘体验’指的不仅仅是感官数据、认知,也包括了感觉与期待”。
一个好的研究除了要有logos(逻各斯),还应当有 pathos(情感)和ethos(性情)。尽管今天的学术文本都是旁征博引,但并不能给你带来任何共鸣,这是为什么?就是因为缺乏性情以及情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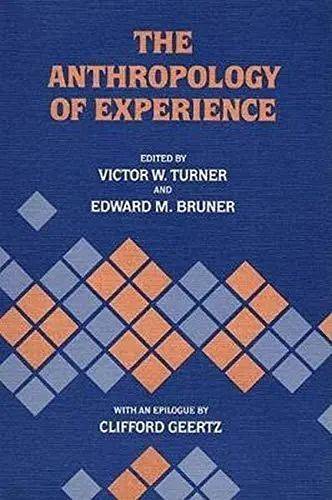
The Anthropology of Experience
Victor W Turner , Edward M Bruner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2001
正如项飙所说,“把自己作为方法”。如果说人类学和其他任何学科,尤其是与姊妹学科社会学相比,还存在某些特别之处,那就在于我们的根本方法是自己。你要把自己的感知和经历用语言传达出来,以自己的感知切入世界。长久以来,人类学过多强调对语言或文字的研究,而常常忘记更加重要的信息在文字之外,是声音、光线、气味、姿态,而未必是语言的和逻辑的。
我们要从自己全方位的感知出发,去关注更加具体的人,而不是作为类别的人类。海子说:“今夜我不关心人类,我只想你。”这也是我对人类学研究方法的理解,首先要去接近、触摸、感知一个或者一群具体的人,关注他们的哀哭、叹息和痛苦。通过真实的接触,可以达致对整体人群的感知。
第二,我们的研究应当从身边的生活开始,而不是想象的远方世界。海子还有一句有名的诗句,“从明天起做一个幸福的人,喂马、劈柴,周游世界,从明天起,关心粮食和蔬菜”。现在的我们每天都在讨论什么呢?伊拉克问题、伊朗问题、阿富汗问题,甚至美国大选问题。并不是说,这些事情我们不应当关注。
我想说的是,人类学的问题意识首先应当来自身边的生活,即使是对海外或者域外的研究,也是为了更好地理解自己身边的生活。通过理解一种不同的生活样式,我们至少能够意识到生活逻辑的另一种可能性,从而避免对自身文化、生活的习焉不察或麻木。
第三,我们的研究应当讨论真实的问题,而不是抽象的概念。我们的研究至少应该是一门真学问。我们可以发展或者讨论一些抽象的概念来更好地理解现实世界,可是如果我们的经验现实被这些概念所局限的话,就本末倒置了。理论是拿来使用的,概念是来帮助我们理解现实的,而不应成为研究和思索的限制甚至桎梏。我们的目标不是概念,而是理解和回应生活中的问题。
而在疫情之下,最大的问题不是恐惧和焦虑,而是彻底的倦怠,对自己、对人类、对未来、对所有都不再关心。“压伤的芦苇,它不折断;将残的灯火,它不熄灭”。既然我们和世界都不可避免地残缺,又何必为暂时的苦难而困扰呢?我们仍要对世界保持期待:总会有一条出路。
在这个残缺的世界中,我们要保持尊严地过活。因为只要活着,就还能够感知,只要还有痛感,就至少还是一个真实的人。做一个真实的人、一个有勇气诚实面对自己感受的研究者,去诚实地处理你觉得重要的问题,去分享和讨论你的感受。
生活并不美丽,我们身处的世界充满了痛苦,但在《美丽人生》这部电影里我们可以看到,当纳粹以公正、纯洁的名义来清理犹太人时,作为犹太人的男主依然努力地为自己的孩子保留一份对美好生活的想象。我想,这部电影是想告诉我们:即使在如此残缺的世界中,我们仍然要相信,生活不只有苦难。

电影《美丽人生》剧照,1997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信睿周报 (ID:TheThinker_CITIC),原载于《信睿周报》第80期,作者:黄剑波(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
